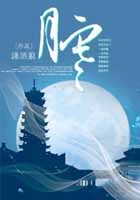祐骋往火里填了几块木头,整个房间陡然亮了许多,这是一间荒废的小庙,距源北村有三里左右,四周没有其他人家。熊熊火光,恍惚将他带到一个时辰以前。
沾衣被册封以后,祐骋仿佛丢了半条魂,白天常常独自发呆,晚上则整夜无眠,这天半夜索性独自一人从王府中偷偷跑出,策马在暴雨中狂奔,似乎想让雨水冲走所有的哀愁和烦闷。
漫无目的奔了一段路后,祐骋突然见到前方一片火光,慌忙勒马辨认了一下方位,发觉着火之处似乎是源北村,心头骤然一紧,慌忙飞奔到近前,不由瞠目握拳,只见火蛇吞噬着一片片房屋,尸横就地,惨不忍睹,全村竟无一个活口,也无一处完好的房舍,那些房屋定是被喷了火油,风大雨急,火势竟也如此猛烈,沾衣的家只剩一片断瓦残垣,他曾经住过的房间,也已面目全非。祐骋就在那里呆呆站了半晌,突然猛冲进去,在满是灰烬的屋里乱翻,他不敢相信慈祥善良的莫氏夫妇就这样命丧黄泉,他更不敢想像如果沾衣得知此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时的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焦灼和恐惧。
就在祐骋在灰烬中极力翻找时,一个身影从烧焦的窗前缓缓移过,他慌忙闪在一边定睛看去,顿时惊呆了。那人正是沾衣,只见她表情木然,双眼呆滞,身上衣服早已湿透,头发蓬湿散乱,横七竖八贴在苍白的脸上,肩头背着绳子,用力拖着一辆破旧的牛车,车上并排两具尸首,盖着席子。暴雨依旧哗哗地下着,一阵狂风刮过,席子滑落地上,露出莫氏夫妇的面容,沾衣慢慢停下,捡起席子,用袖子仔细擦了擦,小心翼翼盖回他们身上,仿佛是在给睡梦中的爹娘掖好被子,然后重新回到车前,奋力拉起绳子,牛车吱嘎吱嘎又开始在雨中前进。
祐骋再也看不下去,冲到沾衣面前,抓住她的肩膀,忍不住连连发问:“沾衣!这都是怎么回事?是谁干的?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在这里?”
沾衣慢慢抬头,依旧面无表情,呆呆望了他一眼,轻轻挣脱他的胳臂,默默拉起绳子,继续跌跌撞撞向前走。祐骋不再追问,刚失去至亲之人,怕是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巨大的悲痛控制她的一切,使她如同行尸走肉。他唯一能做的,是从她的背上取下绳子,背到自己背上,帮她拉着这辆沉重的车,在暴雨泥泞中挣扎前行。
沾衣对他的做法没有丝毫抗拒,一言不发走在前面,直到走上一片山坡才停下脚步。祐骋打量四周,心头又是一酸,他记得这个地方,这里长满杜鹃和各种花草,春夏期间乃是非常绚丽的一处风景,在沾衣家养伤之时,俩人常来此处散步,沾衣定是想教父母在这里安息。正嗟叹间,只见沾衣从车上取来一把钢刀,紧咬嘴唇,狠命挖掘起来,祐骋不及多想,也拔出佩剑掘土。
雨渐渐小了,淅淅沥沥,当最后一把土撒在莫三言夫妇的坟上后,沾衣像是被抽干了体力,昏倒在父母坟前。
祐骋又往火里填了几根柴,低头看着怀里仍不省人事的沾衣,只见她双眼紧闭,睫毛微微颤动,脸色依旧苍白得让人心疼。祐骋紧紧抱住她,将脸贴在她的脸上,泪水不由自主充盈眼眶,曾几何时,他们也这样贴近过,那时的沾衣笑语嫣然,似乎从不知痛苦为何物,与他软语相偎,一起憧憬美好的将来。
“为什么?为什么要她承受这些?”祐骋喃喃道,他的心阵阵剧痛,这痛楚比七夕那天沾衣无情拒绝他时带给他的痛苦更猛更深。他忽然觉得,那天在观止园的花园里发生的让他心碎的一幕,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宁肯倒退回那时,也不肯见到沾衣现在的这副样子,那时的沾衣虽然离弃了他,但至少还是能够快乐的;此刻的沾衣虽然安静躺在他的怀里,却不知将要忧郁悲痛到几时。
沾衣在昏迷中,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小的时候,爹娘笑眯眯站在院子里,自己大约三四岁的光景,走起路来还有些摇摇晃晃。有一天,爹请村口铁匠打了双小铁鞋,娘怕磨坏沾衣的小嫩脚丫,便花了一夜时间为鞋子做了厚厚的棉布衬里,鞋的口沿之处还缀了一圈兔绒。刚穿上小铁鞋的时候,自己一步都迈不得,急得直哭,爹和娘在院子的另一头,不住鼓励自己向前走,爹还说了很多自己当时似懂非懂的话,后来才知道那是练功的要诀。当自己终于蹒跚迈开第一步时,爹竟然欢喜得掉下眼泪,在自己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胡子茬扎得脸蛋生疼,娘则在一边笑着,用柔软的手抚摩自己的头发……
“爹……娘……”沾衣含糊不清唤道,慢慢睁开眼睛。
祐骋欣喜不已:“沾衣……你终于醒了!”
只见沾衣看看他,又愣愣望着四周,突然拼命挣扎着离开他的怀抱,踉踉跄跄后退几步,扶着供桌站定,身体如风中柳叶摇摇摆摆。祐骋一惊,欲上前扶她,沾衣却大叫道:“你不要碰我!”双眼满含悲怨和愤怒,仿佛眼前的祐骋就是她的仇人。
“沾衣……是我,是我啊!”祐骋轻轻唤道,慢慢走近她。沾衣似乎才看清眼前的人是祐骋,吃惊地怔在那里,祐骋慢慢揽住她的肩,把她的头靠在自己怀里。沾衣如梦初醒,下意识紧紧抱住祐骋,放声大哭,肩头剧烈上下抽动,祐骋自从认识她以来,从未见她这样过,他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惟有保持这个姿势不动,让她尽情哭个够。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沾衣哭声渐渐平息,逐渐恢复的理智迫使她推开祐骋,表情也恢复凝重和矜持:“三殿下,你怎会在这里?”
祐骋目不转睛望着她,百感交集,万语千言堵塞在喉头,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沾衣将目光从他脸上挪开,轻声道:“昨夜,是三殿下帮我办妥了家父家母的身后事罢?多谢你了……时候不早,我得赶在天亮之前回宫去,告辞。”说完转身慢慢向门口走去。
沾衣正欲迈出庙门,忽然听祐骋在身后低声清晰道:“沾衣,跟我走罢,我带你永远离开这里,我们重新开始!”沾衣身子一震,停下脚步,却没有回头,又听得祐骋道:“我刚才想了很多,已经想得很清楚,你绝非无情无义之人,是我错怪了你。这些日子虽然发生了太多我不明白的事,我不明白你怎会成为父皇的妃子,我不明白今夜你怎会出现在源北村,我不明白源北村怎会遭遇屠戮,但我明白自己的心,它对你一直没有变过。我不想再骗自己,你可明白?”
沾衣依旧没有回头,站在那里,似冰雕雪塑,声音也冷冷的:“走?我父母为奸人所害,这个仇我不可能不报!”
祐骋有些激动:“仇一定要报,但不是你一人,而是我们两个,我祐骋在此发誓,一定会助你亲手杀死仇人!之后我们便远离这里的一切,出世隐居,白头偕老!”
沾衣仰天大笑,转过身来,想是笑得太用力,说话有些气喘:“三殿下,你太过意气用事!我早已是你父皇的人,你与我私奔,就不怕世人唾你乱伦么?我现在已怀了你父皇的孩子,纵然我们能长相厮守,日后你将以何身份与我这孩儿相处?皇上对你一向慈爱有加,你也敬他爱他,一旦他钟爱的儿子拐了他宠爱的妃子逃跑,他必会大受打击,你就不感觉内疚么?你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立过赫赫战绩,也察过民间疾苦,心中定是早存了鸿鹄之志,如今却为一介女子,尽诸抛之脑后,你扪心问问自己,可甘心么?”
祐骋紧咬嘴唇,眼里闪着光,沉默良久,坚定道:“你与我父皇有过什么,我不在乎;世人如何看我,我亦不在乎!我的确曾梦想有番作为,但你不在我身边,我纵然得了江山社稷,那又如何?顶多在青史上多添几笔浮谀之言,最终还不是落个孤棺枯陵,此生复有何趣?我唯一愧对的,便是父皇,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他的孩儿……以求稍作补偿!”他顿了顿,热切望住沾衣:“沾衣,只要你愿意,我们从此就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做这民间最普通的一对夫妻,男耕女织,双宿双飞,好不好?”
沾衣猛然转过身去,泪流满面。男耕女织,双宿双飞,这是她原先思念祐骋之时无数遍在心里绘制的美丽景像,也是个离她越来越远的梦,她没想到祐骋对她用情之深,竟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为什么祐骋偏偏是皇子?而此时的她偏偏是皇妃?如果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俩必是幸福的一对璧人,天涯海角,她一定陪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可如今,一切都变了,就算祐骋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她也无法释怀,何况旧恨新仇接踵而至,此刻的她,心境已是大为迥异。
沾衣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待情绪平稳下来后,静静问祐骋道:“你当真什么都不在乎?是不是为了我,无论受多大委屈,你都心甘情愿?”
“是的!我心甘情愿!”
“那好,”沾衣偷偷擦去泪痕,转过身,对着祐骋绽开微笑,眼神含情脉脉:“你过来,抱着我……”
祐骋不由大喜过望,走上前去将她紧紧搂到怀里,突然觉得前心一麻,两臂垂下,身体僵立那里,丝毫动弹不得。
“沾衣!你……?”祐骋知是被沾衣点了穴,却不知她为何要这么做。
沾衣背着双手,踱到门前,冷冷道:“三殿下,你一人做梦倒也罢了,莫要将我拖下水,我如今在这世上已是孤苦无依,怎么可能放着皇妃的福不享,与你去浪迹天涯?”
祐骋只觉得胸口被人捅进一把烧红的钢刀,伤口又被塞进一把冰雪,彻骨的烙灼与冰冷在他体内起伏交织,刚刚燃起的希望顷刻便被无情击碎,他无法言明此刻心里的感觉——失望,伤心,愤怒,更多的是心寒。
“你……你终究还是放不下荣华富贵,是不是?”祐骋的嗓音和他的心在一起颤抖。
“你说得一点不错!”沾衣斩钉截铁答道:“以前是我太糊涂,所以才在你身上荒废了很多时光,自从跟了皇上,我才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若你还对我有情,就别再打扰我,让我开开心心过日子,算我求你了!”祐骋望着她的背影,眼里满是哀伤,一句话也说不出。
沾衣独自迈出庙门,似又想起来了什么,便停下来,回身轻轻一笑道:“一柱香之后,你那穴道便会自行解开,你自保重罢!”说完头也不回,向皇宫的方向飞奔而去。
暴雨过后,风依旧劲急,却怎么也吹不干沾衣脸上纵横流淌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