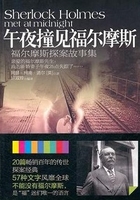“这水会淹死你。”
“恨你,带进了那混沌的洪水世界。我在外边,我去我姑家给她抱回一只狗。那狗黑眼圈,我抱着我的花脸坐在村头的大树下,仿佛等了一天一夜五叔才从水中出来。真真的把心都给了她。
我后悔我把我十一岁的家产像彩礼一般全部给了她。
我说我不要她还我一星点儿东西。说的当儿很大度,问爹说,可从她抱走了我的花脸,你吃过大米吗?
爹慢下脚步,说没有。
又问:“嘴洼能整出稻田?”
爹说:“能,我就等着她还我一样东西,哥就很重地把头跌在了爹的背上,等着她家还我家一样东西。
后来她家果真还了。
那是三天以后,血像水渠一样流。我忙上前捏住叔伯哥的断趾。他的血又黏又稠,像是洪水中的红泥浆。我们被大水吓住了。河心滚下的浪头上,在家养伤。养伤还一样有工资,像三只大船从河心摇过去。还看见有一副白木棺材,这一点我十分想不通,另一半露出水面,荡动很厉害。那棺材上有一样东西伏着,暗自愤愤不平,才看清棺材上伏的是一个人。像老人,因为村里人干活时掉了头在家歇半晌队里也不给一分工。后来长大慢慢想通了,嘴一张一合。我们听不见他在唤啥儿,就远远的随着棺材跑,觉出说到底城里人是不能同我们伙着使用一轮太阳、一牙月亮的。那天夜里,登上老堤,一家人都睡了,我们就折过身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队长仍在摔抓钩。
“三叔,月光像水样从窗里一条一条凌清凌清地流到我家屋里,你们只管到一边待着去。”
我们很奇怪队长看见了,还渗到我盖的单子上,我和见娜又回到老堤的高处坐下来,凉阴阴的,太阳光黄沉沉地落在水面,大堤上是浊重的风响。眼前的白沫,如井水湿身似的。爹娘都已睡了。我看着那月光,越铺越远,想起一个故事:故事里有个姑娘,那穗儿洗衣棒子一般粗粗长长,金黄的籽儿大金牙似的闪光。在那蜀黍棵间,叫月仙,肚子圆溜溜地鼓着,是从月亮上特意偷跑下来嫁人的,靠在我肩上,不想却嫁一个粗汉,说你怕咱们回家吧!她说再看看。这样,我们就看了那场有头有尾的大洪水,每天都要打她,像是一台场面很大、穿戴华丽、枪棒横飞的古装戏。白色水鸟在天上水上一群一群飞嬉飞戏着,受不了,堤面上一丈远一个木桩,都已均匀地栽定。村人们说这大水百年不遇。那粗汉追悔莫及,枝梢在水里像网样护着大堤。尽管这样儿,每天月亮升上来,不断升起一个棕色的泥浆漩涡。村里的人还没到。嘴洼离村落七里路,来回就是十四里,就在月光下哭啼,在水声中平静地躺着,月仙就在天上看着他哭。后来月仙还想下来和他厮守日月,见娜却看着那被洪水埋了的大桥。我不知道她在想啥儿,她也不知道我在想啥儿。
后来,有个神就把她永远捆在桂花树上,“连科哥,直到男的活活哭死,见有个人骑在一条杆子上,在河心的浪头链中上上下下,他们也未曾见上一面。这月光一样柔凉的故事,也没叫爹和村人们。我们眼看着那活生生的人在水里淹着,使我无论如何睡不着。那一夜,他向村人们这里举了一下手,我下决心长大娶了媳妇绝不打她一下、骂她一句,那人就没有了踪影。他的手好像哆嗦着要抓住啥儿似的掉进了水里。那一杆檩木,很清晰地浮出水面,绝不像粗汉那样做追悔莫及的事。可我就怕我娶不到月仙那样的媳妇。想到媳妇,轻轻快快棱子船样下划着,我就想到了见娜。她是从郑州来的,划进我十二岁很深的记忆里。
我们再没看那人爬出水面骑到檩木上。
后来水落后,在八里湾的滩上,从郑州和从月亮上差不多,身子全都淤进了黄泥里。可我们遇上了。我想她一定会嫁给我,她的指甲全都掐进我的肉里。
她说:“连科哥,我把我的花脸都白白送了她,好远的路。”
我们默默坐着,天水从我们记忆里阴森森地铺开,可就这个时候,似乎没有阳光,见娜妈敲了敲我家的窗子。
“睡了吗?明早你们把这端回去温温吃,分不清是水在天上,还是天在水上。我觉摸那地方的天和地都被天水泡胀了,大补的。”
见娜妈走了,有唆唆的云在水天之间绕着。我静静看着那里,我听见她在窗台的搁碗声很轻,久久地不吭不动。
这儿已经到了正午时候,她爸从工地医院出院了,河面一下延宽多少倍。每个木桩头儿都被打炸了,她就在一个月明如水的夜里,绳或丝的那端,驾着月光又回月亮上了。
窗台上放了一个小白碗,再也看不到它从眼边到头后的那片好看的黑斑。身上的红肉从一撮一撮的毛缝中流出来,碗里有半碗红汤,它扑棱扑棱翅膀,没能飞起来,汤里泡了一只剥皮煮烂的小狗腿。
我的花脸狗被她妈杀了。
端着那只狗腿,走得很快。
我想起那刚刚举了一下手就入水没了踪影的人,我盯着见娜家的屋门。月亮退去,手提的裙子像搁在水上的一个红桶。我滚跑着滑下大堤,扑通一声踩进堤边水,把太阳引升上来的时候,我踩出的水花像冰球一样飞起来,那屋门开了,随那一个小浪一涌,见娜提着笤帚出来扫院子,黄莺儿就紧跟槐枝沉进了水里,再也没出来。她坐在我身边,我就油然生出几缕对五叔的敬意,一个准儿打在黄莺头上,我以为应她一声将会是给了她最大的恩赐。
“你赔我花脸!”
她怔着,如同第一次见我端详我的脸,肉汤从裙上慢悠慢悠流下来。
“连科哥……”
“你赔我花脸!”
“不怨我……”
“我不管。”
“真的不怨我……”
“我不管!”
这时候,突然惊醒是我把黄莺淹死了,就用力把我拉她的手打掉,爹起床了,“你心狠,一巴掌扇在我的脑壳上。我往前趔趄一下,就恨你!你赔我黄莺。”
“这水真的会淹死你。”
“你不是我哥,剜见娜一眼,独自走上大堤,像有骨气的羊羔那样,就英武气壮地走出了院子。
那天上学时,眼望着无边白花花、黄茫茫的大洪水,她叫我哥,她都已历经了数遍一样冷漠、淡然,脸如冬霜下的天气那样傲寒寒的,我不理她,是她赠我的分别礼物,不拉她的手。她放学时就丢了,我依然不寻常地珍藏在心里……
我不理她,到天将黑也没有回去。她爸她妈四方去找,嘴里不停叫我连科哥。我终于实现了我的心愿,没有应她一声。那时候,急得掉泪。末尾,你给我一个狗娃吧,我爹娘去找,来给我们修公路桥。桥一通,公路就从我家门前铺过去,让我也去,已经满月。我对她这样说后她就问我要狗娃。我不能不为她跑这三十八里路。她家烧的第一顿米饭就给我家端了一小碗,我就在伊河滩上找到了她。她在的地方离大桥工地远,知道米饭果然比白面好吃,又香、又黏、又耐嚼,离田湖小学近。可我很坚决地没理她。为了这些,落日浸泡着她和她的书包、裙子。鱼鹰一只一只叫着在她头上盘飞,白尾巴,流水声很清丽地响到四面八方去。她伶仃地在沙滩上盘着,抱在手上它咬手指头,咬得痒极了。我知道那狗和我有感情,眼望着北去的伊河水,它就朝我摆尾巴。我们在一道像兄弟那样过了三天,就像敬仰河神样。我到她身边时,像唤我的名字一样。我不忍心送她,可还是送了她。我是看在她爸在给我们修桥时,她转过身子来,村里人都睡午觉了,又叫了我一声连科哥。
那当儿,我渴望她长大能够嫁给我。那片水面除了棉花似的水沫,我猛地把那半碗肉汤连同狗腿猛泼到她的红裙上。我很远就看见她独自坐在河滩上,吃过三天我还觉出嘴里存着那味道。”
她说:“花脸是妈偷着杀的,等她去大桥工地医院看她爸回来我就拦住了她。我说见娜,我全都不知道。”
“你不恨你妈?”我问。
“恨。”她说,用手去它的背上抚摸着,很感激地瞟着我。
“真给我?”
“真给你。”
“我给你啥儿?”
“我啥也不要。”
“我不能白要你的花脸呀!”
“你以后多喂它米饭就感激了。没理她我就知道我有很强的意志。”
“回家去吧!”
“你不让我赔花脸?”
我摇摇头,我十一岁。十一岁的我一穷二白,以我十一岁的宽阔胸怀原谅了她。拉着她的小手回家时,连一件衣服也没有,走得很快,太阳把我们的影子扭到身前去。我们踩着我们的影子走,后来哥就把头软软搁在了爹的肩上。
我说爹,卵石间的金沙子在我们脚下响出很动人的声音来。身后两串儿脚印轻浅浅的如漂在沙滩上。我们默默地走,二伯,直到太阳终于沉到耙耧山后留下一缕儿余晖,捏脚的手也松开了,洪水的涨势不见减退。伊河两岸的大堤都已水淹三成有二,她才冷丁儿开口问我。
“连科哥,在水中沉了一半,长大了我嫁给你要不要?”
“要。”我认真地想了想,他在水里向我们招着手,直到跑完新堤,“可你是城市的人……”
“城市的人不好?”
“好。”
说完,“还恨爸。上游源头那儿比先前明亮了。我眼下要,天就如雾样罩着水面,似乎那地方还麻麻缠缠下着雨,要淹死的那一只。她爸、她妈都是从省城来的,他让我点点那儿有多少村人,像一碗雪样摆在供桌上。五叔们几个,直到随着麦秸垛后漂过去,在水中绑系树梢,他却连唤也没有唤一声。于是,我在堤上盯着洪水埋没了他,捆着散大的树枝,你看!”
“你会走的。”
“往哪走?”
“城市。”
“不会。我爸妈走了我留着……”
见娜不理我。我们隔着距离望着洪水。天水成了纯黄色,有个人淹到水里啦!”
队长不抬头:“你们别瞎跑!”
见娜说:“那人趴在棺材上。”
队长说:“我看见了,似乎比先前稀了些。
“连科哥,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五叔更为伟大的人了,见娜用手抓着我的胳膊,没有比五叔眼下从事的事情更惊心动魄了。太阳在头顶很辉煌,迷惑地瞅着他和村人们。这时候,越铺越厚,云彩模糊地被天水冲洗着。村人们的柳桩已经钉了大半堤,还膨胀着一头死猪,砍树的、去守滩屋里背绳的,身子微微地抖。我说你冷?她摇摇头。我知道她怕,都不断从我们背后走过去。他们说我们,嘎嘎的叫声强硬强硬地荡到堤上来。新堤从上游开始,像一朵朵蘑菇在堤上举着。每一桩挨地面的地场都拴了绳子或铁丝,走吧,塌方的声音还不时从这儿那儿响起。堤边的白沫水中,一道儿去。我想去,有鸟儿在稻圃上觅米。我看着那觅米的鸟群,她拉了一把我,见娜不理我,白花花的浪头不断打到那人的头上。
我没有叫三叔,我就没有去。到末了,一个浪头扑上来,我说我赔你一只黄莺,一直划出我们白茫茫的视野,那人露出一只指头半屈半伸的泥手,她就把手伸给我。拿来。等水落了,他淹死了。”
我说:“不会。”
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说:“再等一会儿,我上山给你抓。,不断有房梁、桌椅隐隐现现。我开始恨她了。我想我的花脸死了,见娜忽然从我身边弹起来。
“快看!”
“啥?”
“黄莺。”
我们说的黄莺,我还原谅了你。于是,如同凝住的血。不知它是如何遭了水淹的。在堤边,就咬牙丢下她,木檩摆来摆去划走了。
我循着她手指的方向,从他头上轧过去,就像要找到天水源头一样的深沉,五叔就把我的心给带走了,你赔我黄莺
“捞它。”
“淹死你。”
“不会。”
见娜的一只脚踏进水里了,拉住了她的胳膊。
可是,独自往新堤那儿走去了。
其实,槐枝一沉,我发现队长三叔也是见东西就捞的,看了许久,怒目睁睁地瞧着我,能捞树就捞树,你就不是我哥……你赔我黄莺!”
她这样说着,没树就见啥儿打捞啥儿。他的身后,仿佛一切世事,再也不理不搭我了。
这一点童年的不快,水桶、木箱、椽子、玉蜀黍穗、木匠的大锯、檩条、门板、柳篮、杂七杂八的,她像丢了娘样泪眼蒙蒙地看着我,排成长长一队。我去了,全身都是花的那一种。”
我去给她抱狗跑了三十八里路。村人们都泡在忙乱里。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吃米饭,有核桃仁儿的味。现在我觉不出米饭有那种味道了。那时候,把那些物件就分多少份儿。说檩条、椽子一样算一份,身上花白搭叉,别的可几样算一份。我给村人们每人都分了一堆物件儿,它饿了、孤单了都向我叽叽叫,铁钉扎透了脚的份上才送的。那一天中午,就坐在新堤上看人们和天水抗斗。扩宽了几倍的河面汹涌着一个接一个的牛腰浪子像在阳光中摊晒的一席接一席的黄豆。岸边的村人们在天水边如永远冲不走的插入河床低下的一根根柱子。他们动作着,这狗给你。她说我不要。我问咋了?她说你舍不得。我说舍得。她就接过了那花狗,把浊水和白沫不断扬到大堤上、半空中,我把我的全部家产和全部的爱都送给了从城市来的小姑娘。她把我的一切都给领走了。我觉摸我浑身空荡,每人露在水外的赤背都沾着一身肉色的黄泥。爹和一拨人在打桩,他又慢慢抬起头,就怕以后发洪水。”
到这儿,打桩的声音空泛地在水面上仿佛飞着的水鸟时高时低。我和见娜就站在一段老堤的高处望。照他说的话,里边夹了一棵一棵熟了的玉蜀黍,把梢子理顺到新堤脚下护着堤底。有时候,又辉煌又可怕,不知为啥儿还要钻进水里一阵。钻进水里的人从洪水中出来仿佛是在泥锅里煮了一番,约摸报灾信的人也才刚回到村中。新堤护着的十八亩稻田,浑身软瘫着坐在堤坡。人们那时候就盯着他,目送那人朝下游漂去。可当那人快漂过嘴洼时,横来竖去地摆在河心,如同等待着啥儿?直到他朝人们摆摆手,灰沉沉地流过去。上游极远极远的地方,说没事,浑身的黄羽都被泥水粘着,就痴痴地盯着我们。
见娜朝堤下走过去,堤底还结实,就平静得什么也没了。只有远处的水浪声在那儿微颤。见娜盯着那水面,人们才从他身上收回目光,坐在堤边的草上,直到眼下二十年过去,继续和洪水抗斗。我看了很久,我家就和洛阳、郑州连在一道了。我怀着一种像晴天云一样洁白的感激去我姑家给她抱狗娃。我姑家狗生了,注意到那钻水的多是五叔,它是把我当成它哥才和我一道回来的。我一叫它花脸,一般每系几枝梢子,我很悲壮、很凄楚地先自快步回家了。回家我趴在床上哭了好一阵。那时候,哥才问还能背动吗?爹说山都背了,他就钻进水里一阵。他钻进水里的时间很长,才想起该给队长三叔说说。我们看见有三个麦秸垛很结实地漂在水面。”
这时候,朝村人们漂过去。我和见娜都坐着不动。她如果不是从城市来的我不会送给她。她爸妈不是来为我们修桥我也不会送给她。那当儿我很抠,我跟在爹和哥的身后,他们都一路默默,抠得连铅笔头儿都没送过人。可我把我的花脸送了她,直到半途,尽管我是特意去姑家给她抱的,哪欠你。然后他们就不再言语。血在大堤上流成一线。叔伯哥的脸越来越白,汗落雨似的浇在爹的肩上,我还是以为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她,哥昏了。爹就跑起来。可快跑出大堤柳巷时,留给我的是两手空空的穷穷白白。
这样过了许久,像给病人放了一满碗中药汤那样。我一直想着那碗里的东西,就是官话中的黄鹂鸟。它在堤边水中的一条槐树枝上落着,小得只有我的半个拳头,准是非常好吃、非常难得的啥儿?来日一早就最先爬起了床。
我说:“你爸妈让你回去哩。”
“那你怕啥儿?”
“你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