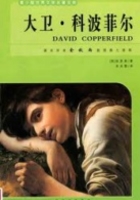“小少爷?”扎嬷喊道,我没有理会她便独自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一个人来到厨房。母亲坐在灶台前面,我像一个疲惫不堪的游子倒进母亲的怀抱。灶膛里的火烤得我脊背发热,让我感觉昏昏欲睡。我将脑袋贴到母亲胸前,她抚摸着我的头,我们久久不语。锅里的水在翻腾,我闻到了煮白菜的清香。过了一会儿扎嬷进来,手里端着一盘酥肉。空气依然沉闷,扎嬷好歹说道:
“太太,今天怎么说也是过年,看在孩子的分上……”
我不理解扎嬷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但是母亲显然被她打动,流下两滴眼泪,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扎嬷端着酥肉盘子,母亲从火塘里掏出炭火将肉烤在上面。扎嬷从锅里盛出菜汤,又从衣兜里掏出几个青辣椒递给母亲。母亲看着扎嬷,破涕为笑了。我们在厨房里,将酥肉裹着烤熟的辣椒,就着白菜汤,下着白米饭,将它们吃了个精光。
吃完饭,扎嬷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我:“小少爷,你在找什么?”
我可不要告诉扎嬷我在找猪骨头。
“小少爷?”
我打住了,见她走了过来,我赶紧将两块刚刚找到的肋骨藏到身后,不料已被她看见。
“我……”干脆直说了吧,我心里想到,“我要去喂狗,只有狗了。”
“什么只有狗了?”母亲问。母亲正在纠正我词不达意的毛病,每当我说出这种含糊的言语,她就会马上纠正,直到我说明白了为止。
“我没有马,没有伙伴,什么都没有,只有狗了。”我说。
看看吧,儿子在无形中伤了母亲的心。其实我并不想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到了现在我的心里仍然空虚得厉害,那种被亲人抛弃,那种一无所有,那种与快乐失之交臂,那种不被理解,那种委屈,所有这些感觉,都会使我无所适从。除了门口的狗,还有谁是我的朋友?厨房里惊人的沉闷让人感到痛苦,我独自一人朝外面走去。广场上觥筹交错,人们在欢笑,在庆祝,在高呼,唯有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承担着一个孩子不该有的痛苦。我穿过仓房,从马厩的后面绕到碉楼。狗们依旧摇着尾巴,但是它们已经餍足,面前早已骨积如山。我将手里的骨头扔到地上,拍了拍狗脑袋,轮番拥抱它们,继而转身上了碉楼,那里的黑暗吸引了我。
碉楼作为官寨的重要防御工事,自然坚若堡垒易守难攻。里面共有四层,每层之间只由一根独木梯上下连接,上去之后可将木梯收起,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每个夹层里又都备有石块和沙子,起到御敌、防火的作用。我钻进碉楼,上了两次独木梯来到第三层,在外窄内宽的箭孔里看到了官寨外面的风景。从高处俯察你原本熟悉的世界你会感到陌生,许多本来如此的事情在瞬间就会变得与众不同。零散的炮声从汉人聚居的八块田方向传来,循声望去远处的街道升起一阵青烟,我仿佛已经闻到了火药的香味,看到了人们正围着鞭炮跳舞。孩子们在田坎上奔跑,电光闪处泛起一阵烟雾,我的耳朵里便响起一记鞭炮爆破的声音。听见他们的欢笑,我自己也跟着欢笑,仿佛自己就是他们的玩伴,只是他们在田坎上,而我在远处不被他们注意的碉楼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我又看见一个孩子正往冬水田里扔炮仗,炸起的泥浆溅了他一身,他一边咒骂一边又往水里扔鞭炮,当泥浆再次跳起来时他很快地躲了过去,动作难看却身手敏捷,仅就这样的玩法,已给他带来无尽的快乐和刺激。不远处的一棵紫油树下,一个黑影睡在地上,想必是谁家酒醉的老头正做着美梦。说到美梦,我便朝昔佐部家的地头上望去,一群孩子结了绳在梨树下荡起秋千。他们的笑声惊起竹林里栖息的鸟群,那绿豆般大小的鸟群在天空中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朝着远山飞去,渐渐消失在苍茫的群山中。
当我回过神来,一阵铃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换了一个窗口,正看见哥哥们的骑兵队从广场上出发。一百多匹马呼啦啦冲出官寨,沿着大街奔向山上,在三岔路口分成三列,沿着不同的路线冲刺,最后吆喝着汇聚在一起朝官寨奔来,气势十分壮观。没有从高处俯视,你不会看见他们的全貌,如今爬上碉楼我才知道哥哥们每天为之冲刺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还一直乐此不疲,重复了又重复,就跟往水里扔鞭炮的孩子一样,从中寻找快乐获得满足。马队回到官寨,刘教头将骑兵队集结在广场上。头人们欢呼起来,他们看到了土司家强大的骑兵,看到了骑兵队迅猛作战的能力,看到了这背后土司家雄厚的实力,这对他们来说无疑起到了震慑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却更像一群有组织的蚂蚁,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跑了回来,仅此而已。过了很久,头人们带着自己的人马回家,土司的骑兵队也就解散了。午后的阳光晒在大地上,温暖的风吹进碉楼里,我只觉得自己睁不开眼睛,全身都感觉沉重,竟然在碉楼里睡着了。
“舅舅?”舅舅将我唤醒,我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个熟悉的地方。
“孩子。”舅舅抚摸我的头。
“我很难过。”我说。
“因为你没有马儿?”舅舅问道。
“我想要有自己的坐骑。”我说。
“你会有的,以后。”
“可是我现在就想得到。”
“你还小,”舅舅解释道,“你还不懂得照顾自己。”
“那么……”我想到三姐,可她毕竟大我一岁,而且她有一个年长的奴婢和一个随时供使唤的丫鬟,我却什么都没有,那么老扎嬷呢?算了吧,她不是。想到这里我就不说话了。
“你不高兴?”
“没有。”我想了想,还是说说狗的故事吧。我喜欢狗,我对舅舅说:“舅舅,阿妈给我讲过彝家天狗的故事。”
“所以你喜欢狗。”舅舅说。
“是的。”不过现在,我更想要一匹马,虽然我口中不说。
“你到底还是想要一匹马。”舅舅洞彻了我的心思,说出了我的愿望。
“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你要先学会照顾自己。”舅舅说。我懂他的意思,彝族人在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不配拥有自己的坐骑的。
“我们讲故事吧,”我说,不要去想那些自己没有的东西。“我给您讲摩梭人和狗换岁的故事,好吗?”
“好吧!”舅舅欣然同意。我将扎嬷给我讲过的故事从头到尾给舅舅复述一遍。“很好,”舅舅抚摸着我的头,“所以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爱护自己的伙伴。”
我说:“那是,如果我也有自己的猎犬的话。”
“即使不是自己的,”舅舅认真地嘱咐道,“你也应当爱护。尔比有言:‘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马是人类最牢靠的朋友。’”
我点点头,舅舅的嘴角泛出笑容。
“既然你给舅舅讲了一个摩梭人‘天狗换岁’的故事,那么舅舅也给你讲一个彝族人‘机敏的青蛙’的故事。”说到这里,舅舅竟也飞起眉毛,一脸轻松愉快的样子,他说:“小孩子要在故事中学会成长!”
我认真地望着舅舅,舅舅于是说道:“故事是这样的,一天老虎与青蛙在森林里相遇。老虎便对青蛙说:‘我要吃掉你。’青蛙说:‘请稍等一下,你说你要吃我?哈哈哈!’青蛙笑了起来,它似乎不把老虎放在眼里。老虎感到奇怪,那么一只小小的青蛙竟敢嘲笑它,于是很好奇地看着青蛙。青蛙说:‘既然你感到奇怪,我且问你,你平常都吃些什么,胆敢与我这样说话?’”
我问道:“那么,老虎都吃些什么呢?”
舅舅说:“不要着急,听我慢慢往下讲。老虎回答道:‘我平日里只吃牛、羊、猪、狗等大型动物,全把它们咽到肚子里,像你这样的小家伙,还不足以塞满我的牙缝。’”
“然后呢?”我问。
“然后,青蛙说:‘光是口舌之争有什么意思,大话不足以为凭据,不如我们各自吐出肚子里的东西,看看谁更厉害。’老虎当然不信小小的青蛙能有什么作为,于是将肚子里的牛羊全吐了出来。青蛙一看果然无所不具,各种动物都成了老虎的腹中之物。青蛙灵机一动,趁着老虎躬身狂吐之际,喷出自己的舌头,粘下许多虎毛和别的动物的骨头储藏在口中。等老虎倾吐完毕,青蛙说:‘你刚才已经吐完,现在轮到我了。’接着,青蛙将虎毛和骨头混在一起吐了出来,说:‘我呢,平常只吃老虎,而且专吃老虎,别的什么都不想吃,现在我的肚子里只剩这点虎皮和虎骨了,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所以才变得有些矮小。’老虎一看,果然是虎毛和虎骨,竟被吓了一跳。青蛙的计谋得逞,又说:‘吃几只老虎有什么奇怪,我想和你打赌。’”
“打赌?”我感到不可思议,青蛙竟然要和老虎打赌。
“是的,”舅舅继续讲道,“青蛙说它要和老虎打赌,老虎马上答应了,它才不信自己会输给这个小东西。老虎说:‘你想怎么个赌法?’”
“怎么个赌法呢?”我用手抓住舅舅的衣襟,着急地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