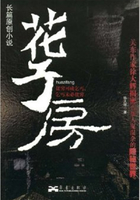接着,又颂起《升火辞》:“火塘是房子的心脏,今后一年三百六十天,火永远不会熄灭,水永远不会用完。盖一座房子,要两根大柱,五根大梁,九十二根原木,五百块椽子,七百块黄板。门后有装财宝的柜子,门左边有一只牦牛,门右边有一只老虎,门上边有一只孔雀,门下边有一只狮子。水槽里有一只金铸的青蛙,外圈房里放着一个银磨。上火塘边的柱子是男人,下火塘边的柱子是女人,男人和女人撑起了一个家庭。”
最后,兰波许愿道:“地下的地母娘娘,请你不要扭动,保佑土司老爷家人丁兴旺,六畜平安,五谷丰登,百姓安宁!”
神将篝火点燃,篝火将热水烧开,热水煮开第一壶酥油茶,香茶首先献给祖先和神灵,接着分给长辈和客人,最后是土司的家眷,这样升火的仪式才告一段落。
兰波从火塘里取出燃得正旺的炭火装进香炉,焚着柏香绕着家里的每个人转了三圈供到神龛上去。土司一家围着火塘坐下,孩子们分靠在屋内的两根柱子旁边。我们管右边的母柱叫“木杜牧”,左边的公柱叫“若杜牧”,它们撑起了摩梭人的整个正屋。母柱和公柱是向阳的山上同一棵大树在属猴的那天被砍成两段的,上边的那段为公柱,下边的那段为母柱,象征着女性是家庭的根。然而对于砍伐木材,我们也有很多规矩,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拿着斧头上山。根据祖先的规定,每年的四月初一至八月十五是禁山的季节,在此期间不允许任何人砍伐木材,以免得罪山神降下罪责,人们就会遭受雷电、冰雹和泥石流的袭击,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在禁山期间进行祭山,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梭赅”。每年的“梭赅”由村里的烟火户轮流承担,每十户人家形成一个祭山的小组,每个小组分给一个木刻,每一户人家代表木刻上的一个缺口,挨家挨户传递着木刻,传到谁家就由谁家去“梭赅”。祭山的早晨,人们来到山上,选一个宽敞明亮的山头,埋一段树干代表山神,在下面点燃松枝和柏香,摆出各种祭品,向山神敬酒献食,等到开山的季节,人们才可以进山砍伐木料和竹子。尽管如此,我们在砍树之前还是杀了一只大白公鸡以敬山神,祈求屋基稳固安定。就在立柱当天,兰波装了两斗粮食,煮了一壶酒,牵着一只大红公鸡绕着柱子转了三圈,把鸡冠刺破将鸡血滴在粮食和酒里,放生的公鸡朝东边飞了出去,这是一个好兆头,表示土司家将会兴旺发达;然而要是朝西,就是不好的兆头,就得重新选树择日,不得有丝毫马虎,以免家运多舛,人员遭殃。立好男女柱后,就在上边架好房梁,梁和柱都被漆成红色,在房梁的正中包上一块装着五谷和银钱的红布,象征着家庭衣食富足。今天这些柱子都系上了麻绳,插满了柏枝和松枝,装饰得非常漂亮。
土司一家坐在正屋里,听着两个达巴白天黑夜地念经,我只好一个人爬到广场上去和自己玩耍。搬家时我并没有想到带上自己的小凳,等我想到已经为时已晚,我一个人没法独自去取,索性放弃。我四处寻找可以代替小凳的东西,可是找遍了整个新官寨也没能找到。失落、沮丧、孤独,这些本不该属于孩子的东西,第一次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而且茁壮成长,我竟然开始怀念自己过去住在老屋里的那些快乐时光了。每天吃饭时扎嬷总是满院子找我,端着饭碗的她倒像是兔子在追赶野狼。直到有一天我在马厩里发现了一个新的蚁群,虽然没有空心柳树下的那样庞大,但是这里的蚂蚁却长得更加油亮好看。从此马厩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就算里面关满了马我也照去不误,几次吓得母亲昏厥过去。后来还是师爷想出了办法,他让扎嬷把我抱到广场上,自己捉了一只蚂蚁捏在手里。扎嬷把我放到地上,我又朝马厩爬去,这时师爷来到我跟前,把蚂蚁放到地上,惊惶失措的蚂蚁在地上拼命逃跑,师爷便放了一个小石子在蚂蚁面前,巨大的石子挡住了蚂蚁的去路,它赶紧掉头朝另一个方向逃跑;跑着跑着,师爷用另一块石子挡住它;蚂蚁往回跑,结果还有一颗石子挡在那里;蚂蚁于是不停地变换方向逃窜,然而师爷都会用石子挡住它的去路。就这样,三块石子变成三座大山挡住了蚂蚁的去路,蚂蚁不停地掉头在三个石子之间跑来跑去。我匍匐在地上,尽量贴近地面,蚂蚁变得像牦牛一般庞大。三座大山来回变换位置,在它意想不到的地方挡住它前进的方向。有的蚂蚁从不越过挡着自己的大山,只要前面一有东西出现它就马上躲开,我像阿依冉巴拉神一样主宰着它们的命运。不过,偶尔也有蚂蚁爬上大山,但是爬完一座又来一座,有的山还会飞,无论它爬了多远翻了多久,最终还会回到原点,依然在三座大山之间来回奔波。
离九月初九越近,来土司家的客人就越多。大家无不为这座雄伟的宫殿赞叹,它结合了摩梭人传统的木螺子结构和汉人美观实用的土木结构。所有客人中最先到达的自然是左所土司,年轻的左所土司永远那么朝气蓬勃,还没到达官寨就已听见他召唤大妈的歌声。卦祖老爷爷说过,在美丽的泸沽湖畔是歌的海洋、舞的天堂。的确,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大家用歌声说话用舞蹈走路。年轻的左所土司还没有抵达瓜别,山谷里就传来左所的小伙子们和瓜别的姑娘们对唱的山歌。歌声在群山之间飘荡,这是一个野蛮而又浪漫的时代,所有能歌善舞的姑娘早已备好了美酒等待客人们到来。铃声叮叮哐哐响彻山谷,快到瓜别的时候左所土司赶起了跑马,在山坡上唱道:
阿哈巴拉,
山隔着山,
河隔着河。
只有歌声,
飞得过高山,
飘得过河流。
亲人啊,
你可曾听见?玛达米!
真是一个善于唱歌的能者!歌声才出,就连埋头地边的老奶奶也不忘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泛出笑容,露出光秃秃的牙龈朝山坡上望去。我的大妈已经站上碉楼,盼望弟弟能够早些出现。听见弟弟亲切的歌声,大妈回道:
阿哈巴拉,
山也不是山,
河也不是河。
哪里有歌声,
带得走思念,
背得走家乡。
亲人啊,
你可曾听见?玛达米!
又是一个美于歌唱的天才!嗓子才开,那些聚集在一起喝酒咂烟的老爷爷无不探出头来,睁大眼睛,张着嘴,忘记了调侃,屏着呼吸,侧耳倾听。
左所土司又唱道:
阿哈巴拉,
山还是山,
河还是河。
马儿哟马儿,
快跑过高山,
快踏过河流。
亲人啊,
就要来相见!玛达米。
山歌从山的这边唱来山的那边回,山的那边回来山的这边汇。大家都静了下来,沉浸在优美动听的歌声里。大妈唱道:
阿哈巴拉,
山也不算山,
河也不算河。
马儿呀马儿,
快跑过高山,
快踏过河流。
亲人啊,
快点来相见!玛达米。
短短几天的日子,远远近近的客人陆陆续续到齐,土司府上上下下的客房全部挤满了客人。从九月初九开始,狂欢持续了一个多月。杀了几十头牛,几百只羊,难以计数的猪和鸡。老土司说:“只要有溜菇山在,就有杀不尽的牛羊;只要有龙洞河在,就有喝不完的美酒。”跑马场上白天尘土飞扬,骏马追赶着骏马;跑马场下晚上载歌载舞,篝火一堆邻着一堆。村子里每户人家的花楼下面都有两三个小伙子通夜通夜地唱着情歌,吵得老妈妈们半夜里起来咒骂:“蚊子都晓得春夏秋冬,耗子也晓得白天黑夜,谁家打圈的牙猪没有关好,一天到晚叫个不停。”然而刚走了一个,又来了一群,整整一个月,没有消停的时候。
我依旧在广场上玩着蚂蚁的游戏,谁能抵挡这样的诱惑:牦牛般粗壮的蚂蚁在空旷的大地上喘着粗气奔驰,一座大山从天而降挡住它们的去路。蚂蚁掉头就跑,谁知又有另一座大山恰好落在它前进的方向,它并不知道这座大山其实就是刚才那座。蚂蚁转过头来换了一个方向,可没跑多远又有一座大山凭空而降……无论怎样努力,刚才还空空如也的大地上偏偏就会出现一座大山径直挡住它的去路。蚂蚁仍然不知道这座大山一直都是刚才那座。它没有停下歇息,依旧忙忙碌碌,然而大山却是那样如影随形,不折不扣地出现在它前进的路上。凭着恒心与毅力,蚂蚁翻越群山不停地前进,可它竟没有发现自己走了这么久仍是在原地。不曾仰望,不曾遥视,脚踏大地,勇敢向前,没有停下来的一刻。蚂蚁埋着头,坚信自己的力量,一步接着一步朝着前方走去。蚂蚁或许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闹剧,但是它没有力量去改变一切,它唯一的做法就是不停向前,向前了又向前,因为主宰游戏的不是它而是我。这就是蚂蚁,这就是人和蚂蚁的游戏。
长大后,我觉得人跟蚂蚁实在没有多大区别。一个未知的超然的存在把握着人的命运,人看不见它就像蚂蚁看不见人;它主宰着人,就像人主宰着蚂蚁。一座座大山,一次次坎坷就这么凭空出现在人前进的路上。人和蚂蚁一样只争朝夕,埋头赶路,勇敢前进,生怕太阳落了下去就不会再升起。不曾仰望星空,或许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模模糊糊看不清的光迹;不曾遥视远方,或许希望渺茫,只有自欺欺人的彼岸;没有停下来的一刻,只看见一望无际的原野和一座连着一座的大山。人生有走不完的路,命运有翻不完的山;人看不见玩弄着人的那个玩家,就像蚂蚁看不见人这个玩家。然而游戏还在继续,今天这只蚂蚁并不比昨天那只聪明,现在这个人也不见得比过去那个智慧。蚂蚁终究是蚂蚁,人也终究是人。蚂蚁逃脱不了属于所有蚂蚁相同的命运,人也避免不了属于所有人类共通的结局。一天天重复,一年年重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永无休止。只要定义时间的人还存在,只要让人存在的那个东西还存在,只要让存在还存在的那个存在还存在,游戏就得继续。除非蚂蚁不再是蚂蚁,人不再是人,存在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