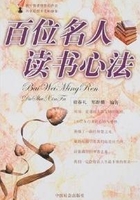爷爷照师爷的安排做了。果然,派出去的信使回来说,画的确是县太爷作的。县太爷收到谢礼后非常高兴,当众奖赏了送礼过去的小伙子。“说我们瓜别人杰地灵,夸我们师爷的字写得好来着……”师爷一听非常高兴,好长时间都神采飞扬。一年后大妈嫁到瓜别,先后有了大姐布耳姆、大哥镇藩、二姐优妹和三姐伊姆,再加上二妈家的二哥镇疆和我这个三太太家的小阿龙佐,土司家一共有了六个孩子。每天早上我在被窝里听得最多的就是大妈的笑声和姐姐们的争执,我的母亲要等到所有人吃完才能去将就一些残羹冷炙。好在奶奶一直对我母亲很好,所以这些年来她也并不吃亏。
谁都不知道每年秋天的第一片叶子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有这么一个早晨,窗外吹着凉凉的风,一片干脆发黄的核桃叶被卷进天窗飘落在我的床前。通常在早晨的这个时候,母亲是不会来我房间的。我还小,也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用人,然而姐姐们可就不一样了,天还没亮这些小鸟儿们便在土司府里飞来飞去。不是找那红色的丝带,就是寻那绿色的头绳;不是偷了大妈的胭脂,就是拿了二妈的香粉。有一次,我的两位姐姐竟为一根漂亮的丝线发生很大争执,我们姑且称之为“丝线之争”。
我还记得那是一根绕着银色毛绒的丝线,是县太太托马帮给她的干女儿——土司家的大太太带来的。大妈还没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年方十二的姑娘。那年她父亲左所土司从木里返回左所,路过盐源时顺道拜访了县大人。他们两家之前就有过交情,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县太太见土司的女儿长得大大方方、端庄秀丽,谈吐聪明、举止得体,自己很是喜欢。又知土司是为她的婚事而来,便自己做主收了她做干女儿。干爹给干女儿招婿就是分内的事了,左所土司当然求之不得,立马在县府里大张旗鼓打起亲家来。县大人见夫人很喜欢这女儿,自己膝下又尚无儿女,此举还可以团结地方,也就欣然同意成人之美。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巧结连理之合。县太太给大妈带来的丝线都是成都蜀绣坊的精品,用精选的蚕丝、上等的兔毛经能工巧匠精心编织纺制而成,最后还在上面撒了金粉,扎在头上可谓金光灿烂、摇曳生辉。大妈将这难得的宝贝藏在衣柜底层,从没拿出来用过。先是大姐发现了它,她看母亲不在房内,又委实抵挡不住美丽的诱惑,便悄悄剪去一截私自藏了起来。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二姐发现大姐天天躲在屋里不出来,也不让人进去,不知道在干啥,搞得神神秘秘,便趴在门缝里偷看,结果发现了姐姐的秘密:她竟然戴着一根美丽的头绳在闺房内孤芳自赏。
妹妹不干了,可是姐姐也舍不得,她不愿意在自己仅有的这段头绳上再剪下一截分给妹妹,也不愿意与之分享这稀罕之物;此事僵持很久,最后姐妹俩终于商量着一个在门口把哨,另一个进去再剪一段出来。进去之前她们还定了协议:妹妹的头绳要比姐姐的短,太长了可不行,一则怕母亲发现,二则妹妹就是妹妹,必须低姐姐一等。看着姐姐漂亮的头绳,妹妹也就爽快答应。于是,姐姐让妹妹守在门口,自己进去偷偷剪了一截。结果姊妹俩又好长一段时间窝在自己房里不出来,相互鉴赏对方的美丽。
那这个秘密是怎么公开的呢?有一天,我们的厨房总管扎嬷路过小姐们的房间,发现里面正窃窃私语。原本无心琐事的她,突然听到姐妹俩谈到大太太的首饰盒,而且口气极为隐秘,便马上警惕起来,把耳朵贴在门壁上偷听。原来姐姐也留了一手,她不让妹妹去翻母亲的首饰盒是怕妹妹也像她那样发现许多宝贝,到时可就洪水泛滥不可收拾了。但姊妹俩在一起嬉戏打闹难免说漏了嘴,妹妹紧紧跟上,姐姐也就开了口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大妈所有的宝贝全都抖搂出来,结果全被扎嬷给听了去。一辈子在府里操劳、事事为主子着想的老家奴果然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将姊妹俩的秘密当着大家伙的面报告给了老太太。终于,姊妹俩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人赃并获。
出于女人的心思,母亲不仅没有惩罚女儿,反而将更多的东西赏给了她们。扎嬷虽然也得到了好处,可姊妹俩却从此与扎嬷结仇,处处给她下绊子使她在土司老爷面前难堪。她们经常在爷爷的酒碗里放一根头发,然后说这是扎嬷的。老土司传来扎嬷对质,然而这也确实是她的。上了点年纪的扎嬷经常掉头发,这便成了孩子们的武器。扎嬷受到了老土司的责罚,诚心忏悔自己的过失,凡事小心谨慎以免再出差错。然而没过多久,她的头发更多地出现在土司的汤碗里、土司的饭菜里、土司的卧室里,简直到了无处不有无所不在不可思议的地步。起先,扎嬷老老实实认账,甘愿接受一切惩罚,深自检讨过失。可时间长了,处处当心、时时留意的扎嬷还是屡屡碰壁,搞得全家人的神经都有点紧张。这时老土司和老太太才发觉事情古怪:为什么扎嬷明明在老太太身旁伺候着,她的头发却偏偏出现在客厅里老爷正在会客的酒碗里呢?难道扎嬷的头发长了脚自己会跑,或者生了翅膀自己会飞?最后,大家终于发现,一切都是这姊妹俩在捣鬼。从此老爷不再处罚扎嬷,姊妹俩闹得无趣,也就渐渐收手各自消停了。
时间并不能冲淡小姐们对曾经出卖自己的家奴的怨恨,尤其是心直口快忠心耿耿的扎嬷,不得不在一些小事上得罪二位小主子。所以,每当我躺在被窝里还没有起床的时候,经常可以听见她们之间激烈的战斗。然而大妈总是偏向自己的女儿,表面上她似乎公正无私,实际上扎嬷讨不到半点好处。好在奶奶虽然是大妈的姑妈,但她毕竟走过人生的道路,凡事大而化小小而化了,成了我们家庭的调和剂。二妈在家里从不参与任何一方,她的存在似乎就是一直围在老太太周围任劳任怨,待在家里你简直听不到她半点声音。与此相反,扎嬷的嗓门那确实是大,大到让人难以忍受,我相信这也是扎嬷不受我的姐姐们喜欢最主要的原因。然而,我却是很喜欢扎嬷,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亲切地叫她一声:“嗨,娘娘扎嬷!”
据说扎嬷就是遗传了她母亲的大嗓门说话才那么大声的。她母亲在年轻的时候是我们当地出了名的大喇叭,长得虎背熊腰、身长八尺、热情奔放、力大如牛。所有人都预言,这姑娘长大以后肯定嫁不出去,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她,更没有哪个男人敢娶她。刚开始的时候她不这么认为,谁要是说她嫁不出去,她就会把谁放倒在地,掐着人家的脖子质问:“谁说我嫁不出去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嫁不出去了?”每当这种时候,围观的人们无不退避三舍吓得赶紧逃跑。领教过她锁喉功夫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不敢在她面前说三道四,全部改为背后议论指指点点。这么一来,她虽听不着人家的议论,可心里却更加痛苦,因为她总是觉得别人在背后谈论她,说她坏话对她冷嘲热讽。每次上街,她都觉得背后有无数眼睛在窥探她,等她出点什么洋相的时候暗地里发出老鼠一般嘶嘶的笑声作为对她的报复。因此她的神经变得敏感,性格变得急躁,脾气变得莫测,最后发展到有些癫狂的地步,甚至别人说的不是她,而是十八里坡外一个哑巴的女儿,她都会认为这是在取笑她,她的癫狂便会再次发作,无辜的人们就会再次遭殃。时间一长,以至周围的人都不敢在瓜别的大街上谈婚论嫁,唯恐从身后跳出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上来熊抱把自己放倒,然后骑在自己身上疯狂质问,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还是不要沾惹的好。
可是老天,事情总有急转直下的时候。谁知道有那么一天,一个汉子站了出来,破天荒地宣布自己就是要娶扎嬷她妈为妻,这话很快传到了扎嬷她妈的耳朵里,气得她暴跳如雷,提着裙子,卷着头发,风风火火出了家门。我们摩梭人有一句谚语:“只有剩饭剩菜,没有剩男剩女。”按理说这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现在有人肯娶她,而且这人还不错,是村里村外出了名的老实人,她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她一点都不高兴,反而正是因为人家太老实,所以说出的话才让她难以接受,仿佛是在骗她,侮辱她,玩弄她。扎嬷她妈像一头发了疯的牛一样冲到大街上,声称要干死那个玷污她名誉的家伙。她径直朝那男人抱了上去,大家竟没能拦住,直到两军交战大家才舒了口气。奇迹终于发生,这回她真遇上了对手,只见她冲上前去,用一如既往的手法抱那汉子的腰,想要把他甩翻在地。结果摔了几下,挣得自己满脸通红,对方都稳若磐石纹丝不动。她不甘心,又要去掐那男子的喉咙,却反被对方轻松拿下,她便束手就擒了。
原来这男子是本村出了名的石匠,几百斤重的大石头他能一口气抱起;别人推不动的东西他只需鼓一鼓力,那东西马上就乖乖地滚动起来。只因常年在山里干活,所以大家只知道村里有这么个能人存在,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唯有那些在他家买过磨子的人才清楚这个人姓陈,叫陈娃子。看来陈娃子小的时候,父亲并没有给他取名,长大后别人也都这么叫他,他便一直叫陈娃子了。话说陈娃子从小就力猛如虎、资质禀异,一顿比一家人吃得都多。他母亲虽然不忍、父亲也没有别的用心,就是实在没有办法看着别的孩子挨饿而让这个孩子吃饱,或者成全了别的孩子吃饱而让这个孩子挨饿。父母几经商量终于决定让陈娃子外出学艺,打发了他二十张大饼,让他别再回来了。结果这孩子一去就是二十年,父亲猜他早已迷失在山野树林,母亲则以为他准是饿死在荒郊野地。谁知二十年后他竟然活着回来了,还学了一身打石匠的本领。全家人都很高兴,尤其陈娃子打出的磨那是绝对的漂亮,购买的人络绎不绝,一时间声名在外。除了打磨之外,他还偶尔打点猪槽、石板,技术也就仅止于此了。曾有汉人问他会不会立碑刻墓,可惜这孩子没有识字的命。师傅在教他打石的这些年里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可惜字他是半个也刻不出来,磨子倒是闭着眼睛都能打得圆圆滚滚。师傅觉得这孩子的造诣不足以继承自己的衣钵,便给了他一些银子算是这些年的工钱,做了二十张大饼让他背着,告诉他学艺已到尽头他可以回家了。
陈娃子回到村里干起打磨的行当已有好些年,没磨可打的时候就帮家里干活,从不下山惹是生非。母亲心想儿子已是三十好几的人,同龄人的孩子都能下地干活了,便说合着给他讨个老婆。陈娃子也觉得是该给自己找老婆的时候了,便依着母亲的要求去邻里有合适姑娘的人家帮忙。可这活儿是干了,而且他一个人的工足以顶人家五六个人的工,但人家就是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好几户人家都这样。眼看陈娃子就要帮全村的人干完所有农活,很快就要没有人家可去,母亲实在搞不明白这是为何,就去挨家挨户地问,这才发现她那打石匠儿子除了能吃以外还有一项特殊的本领,便是那双能干活能打磨的手有一种破坏一切的能力,简直邪恶透顶让人无所适从。譬如吃饭的时候,放在他手里的碗就会不明不白地破裂,一顿饭换好几次碗都是这样。起初人家以为这是自家的碗用久了偶尔是容易碎的,但是一顿饭换了好几次碗都会莫名其妙地碎掉。本来碎三四个也就够了吧,可陈娃子饭量大,人又老实,没有吃饱那就是没有吃饱,丝毫也不晓得什么叫客气。主人家看他干活时那勤勤恳恳的样儿,吃饭的时候也就实实在在地让他吃。结果一顿饭下来,家里所有的碗基本上全泡汤了,就算是剩下的也已拿不出台面,都是非伤即残。以前陈家人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陈娃子在家历来使用盆子,所以母亲倒也没有发觉儿子这潜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被拒绝多次以后,实在没有人家可去,失落的陈娃子第一次走上瓜别的街头。他听人家说喝酒可以解愁,便到瓜别最好的酒楼“通衢之家”要了一桌好菜一壶好酒。掌柜的怕他拿不出酒钱,迟迟不肯备酒上菜。直到陈娃子往桌子上拍出两锭银子,掌柜的才赶紧到地下室抬出一坛“龙头玉液”,很快又将菜饭端了上来。美酒佳肴上齐之后,陈娃子端起酒碗就是一口,没喝过酒的他自然是被呛得涕泪俱下哇哇大哭。老板娘见状很是不忍,知道他是个老实汉子,便走上前去安慰。一番善意的劝解终于解开了汉子的心结,陈娃子像孩子一般哭诉着将自己坎坷的身世和离奇的遭遇全给老板娘说了。
老板娘听完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个中规中矩的媳妇儿,包你一百个满意!”陈娃子一听,乐开了,无比信任老板娘,不管她说啥都照做。第二天陈娃子又去酒楼喝酒,瓜别街上便传开了他非要娶扎嬷她妈的流言。扎嬷她妈浩浩荡荡杀将过去,使尽浑身解数却反被陈娃子制住,眼看拿他没办法就卸下气来想要寻死,说是陈娃子侮辱了她。那陈娃子喝过好酒吃过好肉,精力充沛,正在兴头上,被她弄了那么几下,倒也觉得这个女子还不错,有点力气,配得上他陈家打石匠的巨擘,确实是个持家的料,趁着酒劲儿哪由分说,只听他大喊一声:“你这个黄昏牛!”便将女子扛在肩上大摇大摆地回去了,任由她在背上撕抓乱扯。街上的行人无比惊异,也都跟着看热闹,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有人竟能将大名鼎鼎的扎嬷她妈降服。到得家里陈娃子已酒醒三分,霎时间觉得不对,自己似乎做得有些过分,可又不好意思退还,便将女人放下置在一边,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倒头便睡,呼噜声排山倒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