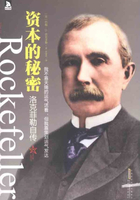在这篇文章中,陶行知还对中国教科书进行了“总批评”。他说:
“三十年来,中国的教科书在枝节上虽有好些进步,但是在根本上是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翻开小学常识和初中自然教科书,就会发现这些教科书并没有教学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与此同时,他对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也做了无情的揭露,说这种教育只能让我们回到义和团时代。此外,他还详细解释了生活教育教科书的编写标准和编写内容。在陶行知的带动和影响下,浙江、湖南等地也大力推行乡村教育,并取得很大成效。
这种留美博士致力于乡村教育的现象,在陶行知去世之后好像已成绝响,至今尚未出现。
九 讨论恋爱问题
晓庄师范成立后,曾经发生一起“桃色新闻”,引起广泛的关注。大约是1928年,该校一对热恋中的学生结伴去游玄武湖。由于天色已晚,路程又远,他们在返校时雇了一头小毛驴,一同骑着回去。现在看来,这种事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周围的群众议论纷纷,说他们伤风败俗,而且在学校也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些同学甚至说此事影响了学校声誉,应该严肃处理。
有意思的是,这一事件居然传到教育部部长蒋梦麟那里。蒋梦麟与陶行知是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又都是杜威的学生。蒋问陶:“听说你的学校里,男女关系有些浪漫。男女同学合骑一匹驴子,招摇过市,这倒有碍校誉。”陶行知回答说:“对,两人合骑一匹驴子,的确不太好。但他们骑在驴子背上,上见得天,下见得地,中间还可以见人。比那些大人先生坐在汽车里,偷偷摸摸,上见不得天,下见不得地,中间见不得人,不是好多了么?”
按照晓庄师范的规定,每周要开一次人生问题的讨论会。为此,校长陶行知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关于“人生问题”的笔记本,任何人有问题都可以写在上面,供大家讨论。上述两位当事人非常苦恼,因此他们在那本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问题:“难道青年男女讲恋爱就错了吗?难道男女同骑一头毛驴就有伤风化了吗?恳请陶师给予我们正确的指导。”
陶行知认为,凡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面包问题、恋爱问题在内,都是教育的内容。这就是生活即教育的真谛。为此,他引导大家就此事展开讨论。经过两周的热烈讨论,似乎仍然没有理想的结论。于是陶行知也参加进来,并发表讲话。他说,生和死,事业和恋爱是人一生要面临的四件大事。前两件事自己不能控制,后两件事自己却可以控制。许多人讳言恋爱,这是错误的。古人所谓“食色性也”,所谓“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说明他们对这个问题已有正确的认识。今天我讲这个题目,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向大家报告一下人类恋爱可能发生的三种现象:第一,恋爱的人忘记一切,只知道爱他所爱的人;第二,恋爱的人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所爱的人;第三,如果恋爱遇上外界的阻力,就会转入地下或者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成败乃恋爱之常事”,“压迫恋爱的人是天下最愚笨的人”。
接下来,陶行知还以徐志摩为例,进一步说:“三年前我到浙江观潮,同行者有汪精卫先生,徐志摩先生,任鸿隽先生及其夫人。当时有人同徐志摩先生开玩笑,向志摩先生贺喜。精卫先生以为志摩先生得了公子。志摩先生自己解释说:’生子不如成婚,成婚不如订婚,订婚不如求婚,求婚不如求不成。‘这是诗人的态度,将失恋的情感,在诗中(或艺术中)表示出来,使他的诗更能动人。”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正在热恋之中。从“贺喜”之说以及汪精卫的反应、徐志摩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二人对人生的理解和态度。
在这次讲话中陶行知还谈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三角恋爱。他说,在西方,如果两个男子同爱一个女子,他们的处理办法是尊重女性,“让女子自己选择,女子爱谁就是谁,失败的人决不应多言。倘若女子自己也决不定要爱谁,他们也有痛快的办法,以决斗解决之。决斗的事,我虽不希望发生于现代,但他们这种态度是很高尚的。”二是恋爱的目的有两种。
一种是为了家庭,为了传宗接代;一种是为了个人,与传宗接代无关。三是恋爱有“专一和独占”的特性,因此一夫多妻的家庭往往不能和睦相处。
四是对于离婚,应该视为“世界上最伤心的事。”如果“夫妇不能相爱,也应平心静气研究不能相爱的原因”;如果无法挽回,是可以离婚的。
此外,他还希望恋爱中的人要学会爱护情人的名誉。他指出,在恋爱问题上,艺术家和诗人偏重感情,科学家偏重理智。这两种态度都是对的。因此每一个人要本着自己的天性,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陶行知还告诉我们:“恋爱本是一件极平庸而极重要的事,我们应该公开地诚实地讨论,才不致走入歧途。中国习俗,家庭间、学校都不敢谈这个问题。全国学校中,师生坐在一堂来谈论它,晓庄恐怕是数一不能数二的。”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当时情况,陶行知是鼓励男女同学自由恋爱后共同去穷乡僻壤办学的。为此,他还写过一首题为《村魂歌》的诗。诗中写道:
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
哪儿做先生?
东村或西村。
同去造新村。
旧村魂,新村魂,一个夫妻一个魂。
据说赵元任看到这首诗后,还为它谱了曲,在同学中间传唱。有的同学因此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消息传出,引起《申报》的关注。记者在报道该校招生时说:“以夫妻办理乡村小学,为陶知行夙所主张。此次挈其未婚妻来考者,有武进于某,一对小夫妻感情异常浓洽,鹣鹣鲽鲽,寸步不离。旁观者或啧啧羡彼等幸福不置也。”
十 反对会考杀人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会考制度。该制度规定中学生在毕业考试合格后,还必须通过省、市主管部门组织的统一命题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这种统一命题考试被称为“会考”。
有感于这一制度造成的恶劣影响,陶行知在1934年6月1日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为题,对它进行严厉的抨击。文章一开始就说,自从会考令下达之后,中国教育界就出现了一幕幕“滑稽的悲剧”。这种“滑稽的悲剧”首先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由于会考是关系到能否毕业和升学的大事,因此它势必成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会考要考的内容,老师就教;会考不考的内容,老师就不教。这正如陶行知所说:“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 这样一来,“教育就等于读书,读书就等于赶考”,学生学会考,教员教会考,学校也成了“会考筹备处”。其次,这种“滑稽的悲剧”还表现为中学生不堪重负。为了应付会考,同学们只好加班加点,推迟熄灯,减少睡眠。有些“会考呆子”
在“茅厕里开夜车”之后,还不无幽默地说:“不闻臭中臭,难为人上人。”这种状况与如今的高考大同小异。
陶行知说,由于毕业考试以后是会考,会考以后是升学考,因此中学生只能是“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他还说:“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正因为如此,陶行知指责这种会考是变相的科举,变相地杀人,是大规模消灭民族的活力。
令人奇怪的是,当陶行知与主考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主考官没有一个相信会考”。也就是说,“他们是不相信会考而举行会考”。有感于此,陶行知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杀人的、“毁灭生活力”的考试,建立能够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
同年11月11日,陶行知又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中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两种吃人的手段。第一种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所谓自己吃自己,是指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如果只会读死书,死读书,十几年下来,就“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就叫读书死”,是自己吃自己。第二种是“教学生吃别人”。所谓吃别人,是指如果一个人求学的目的是升官发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当他学成以后,就会“发农人、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人、工人血汗”,就是在“吃人”。
陶行知说,他所谓生活教育有两大特点:第一,生活教育是教人生活、教人做人、不教人赶考的教育,是一种“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
的教育。第二,生活教育不教人升官发财,只教民众“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这就是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
用陶行知的观点反思当今教育,应该会有所启发。
十一 提倡科学创造
1932年5月,陶行知在杭州师范学校参观,就儿童科学教育问题发表演讲。他指出,20世纪是科学昌明的时代,这个时代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中国;要建成科学的中国,就需要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教育。在这方面,小学教师负有重大的责任。他认为,要对孩子进行科学教育,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玩科学的把戏”,让孩子在自由的游戏和玩耍中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为此,每个教师一方面要“变成小孩子,加入小孩子队里玩把戏”,一方面要以“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众生皆同学,书本不在兹”的精神,把学校与社会、学校与自然联系起来,去探索科学的奥秘。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提醒大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杀人,也可以造福于人类。因此在进行科学教育的时候,要让孩子们做大众的天使,不要做少数人的奴隶;要让科学养生,不要用科学杀人。
第二年3月,陶行知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创造的教育》。他说,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关门的教育。它的主要表现是“教师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因此这种教育也是“死的教育”。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大家都以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社会是行动的地方,好像学校与社会是漠不相关的,以致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书呆子”。他指出,王阳明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代表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的教育思想,“现在我要把他的话翻半个筋斗”,变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让大家在行动中得到知识,然后用知识进行创造,这才是正确的教育观念。陶行知年轻时因为崇拜王阳明而取名陶知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又要改名为陶行知。
在这次演讲中,陶行知还对什么是创造教育以及创造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创造教育是行动的教育,“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所以我们主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或者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还说:“假使我们给小孩子自由行动,我相信千百孩子之中,一定有一个小孩是天才,是一个创造者,发明者。”他强调,只有以生活为内容的教育,才是创造的教育。如今的孩子,在应试教育束缚下,为了考上重点学校,考上大学,每天就知道死记硬背课本知识,几乎没有行动的自由。这显然是我们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缺乏创造力的主要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3年10月,为了调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他向大家宣读自己所写的《创造宣言》。宣言说:
“教育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这种人应该是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的活人”。此外,他在批判了懒惰者和懦弱者的各种遁词之后,还热情洋溢地指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1944年9月,陶行知在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题目是《创造的儿童教育》。他首先指出,儿童的创造力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只不过是“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罢了。为此,他提出教育工作者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加入到儿童队伍里去,成为孩子当中的一员。要打破成见,去发现和认识孩子本身具有的创造力。他认为,要解放孩子的创造力,就必须解放他们的头脑、解放他们的双手、解放他们的嘴巴、解放他们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多动脑,多动手,多发问,多接触大自然。在这次演讲中,他特别提到为了把时间还给孩子,就要改变“现在中学校有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的状况。否则,就会“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到成人时,即使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他还说:“专制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不能培养人民做主人”,因此“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陶行知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应试教育的弊病,进一步指出了我们为什么长期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的原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根据形势需要,把他主编的《战时教育》改名为《民主教育》。为此,他在《民主教育》一文中首先指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以教育为公器,教人做主人的教育。但是“党化教育”
却不是这样。他表示:“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是把国家的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
他还说,要培养创造力,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就必须“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解放双手,剪去指甲,摔掉无形的手套,使大家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动手向前开辟。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摆龙门阵,谈天,谈心,谈出真理来。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有了这六点大解放,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
在这篇文章中,陶行知还说:“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这种生活“是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织成之和谐的生活”,因此民主教育也是“和谐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