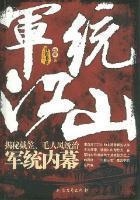哪里都是大吃小、强欺弱,监狱里的犯人是这样,学校里的小孩是这样,军队里的娃儿还是这样!王亨渐渐把敌意集中在邵杰身上,反倒发现了别人的好处:以前总觉得战友都是一群剃光头的傻瓜,现在认真一体会,觉得他们还不错,说说笑笑的挺容易相处;以前觉得连里的干部从连长指导员到实习排长都废话连篇,现在觉得他们肯在自己身上下工夫做思想工作也挺难得。变化就是这样开始了,起初是被迫,后来是真的放弃了最初的偏执。他想到过逃跑,但像王排说的,他能逃到哪里去呢?又能逃多久呢?一辈子吗?“逃”的日子必是可怖的,不然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邵杰何以会逃到部队里来?好几次他路过连长或指导员的房间,都想推门进去举报,甚至吃饭时他很想站起来大喊一声:“我们中间有逃犯!”最终还是抑制住了这股激情。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忍辱负重的修行者,一个怀揣利器却要韬光养晦的江湖高人,一个承受着重大秘密的地下党员……
听到这里,王远已经坐不住,一下子站起来,腮帮子的一块肌肉收缩表明他正咬了咬牙。意识到他想法的王亨连忙说:“那都是以前!以前!现在我和邵杰是哥们儿,真的,我已经不怕站岗了,我们站岗都一起聊天,他还教我武功呢……”
他的话音未散,实习排长王远已经走远了,他径直去找到肖遥,把他拖到不影响两人自由进行语言表达的地方。还是在那棵樱桃树下,肖遥拖着有气无力的声调——“听我说,是这样的……”
他们都知道如果不治住王亨,指不定这家伙会出什么乱子,而王远在领导那里也无法交代。肖遥也知道凭王远那一身傲气,要动点歪点子肯定是行不通的,他只有悄悄找几个有经验的老兵,讨了个主意——找个厉害点的新兵治治不听话的人(武功高手、杀人犯什么的当然出自肖遥的想象,也只能骗骗王亨,本科毕业的王远当然不会上当)。
“我知道你是不会同意拿邵杰去吓唬王亨,”肖遥说,“但是你看这样不是效果很好吗?我们是在基层连队,切切实实的部队,它有它的现实逻辑!”
由于王远一直沉默不语,肖遥自作聪明地以为终于说服了这个倔强的死党,至少触动了他的基本观念,为了乘胜追击,他继续宣扬: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利于生存的种族,哪怕再有梦想的翅膀,一撞上现实的墙壁他就头破血流了,飞不了了。王亨的转变也告诉我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跟着指导员混什么混啊?他也就是一空谈家!
听到“指导员”三个字,王远敏感地追问肖遥是什么意思,肖遥涨红了脸索性把话挑明:“你不是指导员的人吗?全连都知道!”王远恶狠狠地逼近肖遥问:“那你是谁的人?连长吗?”被逼问的人只梗着脖子、紧咬牙关不作回答,王远冷冷哼一声:“你要拉帮结派就忙乎去吧,我他妈谁的人都不是!”
9
全连都当他王远是指导员的人了。也难怪连长后来对他反倒小心一些了,尽量对他的工作不做否定性评价——以免指导员多心。但王远知道他和指导员并没有走到很铁的一步,最多也就是谈得到一起而已。世俗之人到一个新地方总是急着找靠山,但他王远不是俗人,至少自认为不是。
接下来的日子,王远多多少少有些故意疏远指导员,但指导员却热情地找上他,一进房门王远就发现对方面若桃花,“春天来了”的感觉。满面春风的指导员确实迎来了他的春天——“我要离开这儿了,到政治处当保卫股股长,命令刚刚宣布。”
那天晚上唯一没去参加指导员饯行酒宴的就是连长。他没去参加酒宴,并不意味着他没喝酒。从酒宴回来的人经过连长房门时都蹑手蹑脚,只有王远“借着酒兴”在那个门前停下了脚步,抬手敲门。门里传出粗哑的询问声,回答说我是王远,里面又问干什么,回答是:“找酒喝。”
门打开时,一股浓重酒味像夏季气浪一样直冲过来,气味裹挟中的连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颓唐,他一脸粗壮的胡茬,皮肤过早松弛,目光里弥漫着寻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他把王远瞅了瞅,转身走了,这是允许来客进屋的表示。王远进去后关上了门,把不良影响减少到最小,同时一眼扫到桌上两个竖立的空啤酒瓶,椅子旁边放着一箱啤酒,空了两格。
连长解释自己的酒量远不止两瓶,只是没人陪,喝闷酒太没意思,现在王远来得正好。王远抓住话头问他为什么不去和大家一起喝,连长脸上闪烁出了苦笑,说像自己这种粗人去了会破坏气氛。“自当了连长,陪了三个指导员,现在第三个都走了,老子还在这里!烂在这里!”随话音落下的是说话人随手抓起的一个空酒瓶,它脱离主人大手之后没能来得及划个漂亮的抛物线就重重撞在对面的墙上,哗啦一下粉身碎骨。沉寂片刻,王远麻利地从箱子里提出两瓶啤酒,用牙咯啦一下咬开一瓶递给连长,又咯啦一瓶归了自己。
酒是男人最好的沟通良药。重新握着酒瓶的连长面对比自己年轻一大截的实习学员,哭的心都有了。
“多大了,今年?”
“二十三。”
连长啪啪地拍打着自己胸膛,悲怆地说:“我,马上三十了!三十了!”
一个带着审视意味的年龄。一个逼着你回望来路并规划未来的年龄。一个对中国人而言具有宿命色彩的年龄。大多数人从“而立”二字中感觉到安身立命的紧迫感,但对穿了军装的人来说,安身、立命都是不可预期的。连长海灌一口啤酒,泡沫被他生生咽下又从胃里泛出个畅快的嗝,他用潮湿的语气问王远知道自己过去的故事吗,王远点点头说知道个大概。
“他们叫我们光头连,嘿嘿,”连长笑得带出了眼泪,像搞了个成功的恶作剧,“他们都晓得我喜欢给人剃光头,可他们晓得我为啥喜欢吗?”
完全是上次指导员所讲故事的续集。张参谋从毫无知觉的漫长混沌中逐渐恢复意识,第一个感觉是来自头皮。一种木木的、切肤的触动——细腻、轻柔的刀片刮过,头上一点点失去保护与伪装,一点点地裸露与发凉,透过皮肤传来恐怕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嚓嚓嚓的声音。再细腻轻柔,那也总是刀片啊,他刚试着挣扎了一下,头部上方响起一声甜美的普通话:“别动!在剃头发呢!看你的头伤得……”素色的环境、浓烈的药水味儿、人的话音和器械触碰产生的低微却清晰的声响,通通围绕着他,使他明白这是医院了。锋利的刀片剃着受伤的头脑上阻碍治疗的毛发,也许握刀片的女护士年轻且美丽,笑起来唇红齿白,她听上去轻松愉快,熟门熟路地进行着日常工作——给伤员剃一个完美的光头。
恢复意识后难以避免的是:思想启动了。这悲剧性的大脑内部活动正是伴随着女护士手下单薄却锐利的刀片、伴随着无情剃发的外部活动同时展开的。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摆脱这个噩梦般的场景,赌酒、开车、出车祸都因为酒精参与而包裹着一层模糊,唯有醒来后的第一感觉清晰得可怕,那么冷静而冰凉的刀片。
基本伤愈后他回到部队,接受了团里的处分,也接受了被“发配”到修理连的命令。刚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的目光一一触及浸淫在暮色中的颜色黯败的营房、弃置在路边无法修理也无法拉走的报废车辆、散发着墓地一般幽冷气息的连属菜地以及大门口等候着迎他进门的表情木讷的兵,医院里带回的恶劣感觉又幽灵般出现了,他的头皮一阵阵地发凉、发紧、发麻。他曾经怀揣的雄心壮志、为理想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对曼妙青春寄寓过的奢求与幻想,都被那个说一口甜美普通话的小护士一点点地剃掉了,现在他一无所有,狰狞不堪。
剃。
他迷上了这个动作。他让自己保持着硕大的光头走来走去,别人因为他受过伤,不便指责他的特殊发型,更增强了他自由的个性。渐渐的他不再满足于此,开始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把这一个性扩大化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右手握着一把理发专用推子,左手抚摸着一块毛发旺盛的头皮,心里缓缓滋长起一丝战栗。他把左边的头发削了削,右边的显得太长了;又把右边的削了削,左边的又太长了……反复多次之后,两边的头发都短得失去了比赛资格,却依然参差不齐,于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借口——剃。让这块头皮寸草不留。剃。他就这样让手下的娃儿们一个个变成了光头。剃的时候有种摧毁的痛快,像把什么东西打翻了打垮了,压倒一切又砸得稀烂……他不可以助长心里的恶念去破坏任何一个人的命运,但他可以剃光他的头发。怪异的癖好纠缠着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剃两个光头会让他发泄怨气,当修整出一个光滑亮洁的光头时,他会长长舒一口气,疲劳不堪,心境则在蓦然间恢复平静。
先前的确是生手,只会剃光头,但事实上,几年的积累,已经让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准专业的理发师了,他早就会几款不算落伍的基本男式发型了,分头、平头、大背、三面光,都不错,回到家里,儿子和邻里的老人都是找他理发的。但一到连队,面对同样穿军装的“娃儿”,他就像瘾君子见了毒品似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了,推子一递过来,非要把它用到极致,除了剃光,还是剃光、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