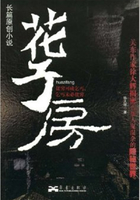水芬可真是个好女子。
在农村里,这样的“好”是“好”得很具体、很实在的,像磨得细细的玉米面,可以调成糊,可以团成饼,可以蒸、煮、烤、炸,随着人口味来的。
人们私下里议论屠广福家三个女儿的时候,以前都把重心放在一心要读大学的水英和长得漂亮的水芹身上,水芬倒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很长时间没有引起旁人关注。看起来这个老二是两不搭边:既没有大姐水英读书的脑子与劲头,又没有妹妹水芹的脸蛋与身段,她的存在本身就很中庸,很平凡。平凡是不怕的,只要你甘于平凡。这个水芬,真把平凡发挥到极致了,她和杨家湾大多女子一样,早早退了学,又和大多女子一样,劳动,持家,等着嫁人。收割时她可以一口气挑上一百三十来斤的稻子稳稳当当走在硬实的田埂上;在大清早她和男人们一起赶着把新鲜的时令蔬菜装进筐子里挑到镇上去卖;傍晚她伙在姑娘姨婶堆里纳鞋垫、听笑话。笑话都是风过无痕,纳在鞋垫上的针脚却是密密匀匀,一针一线、一板一眼的。没结婚也没对象,所以不和男人们笑骂调情,眉眼顺着,山高水长的,让人一看就舒坦,忽然就觉得应该把她娶来移到自己家中的院落里。这样,水芬终于脱颖而出,被发现了。她的被发现也是情理之中的。每个村子都有许多个水芬,每个水芬都有一份大致相同的心思,她们后来嫁的也都是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却又差不多的男人。
水芬本来可以把她平凡的命运进行到底的。已经有一两家的女长辈借着磕闲话的机会探听过水芬妈的口气了;还有,三组杨才康的妈妈只要一出现,动不动就把眼珠盯在水芬身上,带着相当程度的考察意味。这几户人家还在权衡,还在考虑,等到时机成熟了就会委派一个中间人身份的婆子媳妇前来提亲。过不了多久,水芬后半生的情形也就大致定下来了:她那爱吃酱肉就白干的丈夫,她那天天相互拌嘴怄气的公公婆婆,她那拖着长鼻涕要糖吃的男娃或女子……都会从模糊中一点一点走到青天白日下。谁不是这么过过来的?
水芬是认命的。
有一年外出打工的屠广福为省路费没回家过年,托人带回了几斤孔雀蓝的毛线——也真是会动心思,自家三个女儿,直接送衣服吧,只送一件的话,送谁呢?比着任何一个的身材买都会让另两个有想法,送三件又花费大了点,干脆送毛线,囫囫囵囵的,好像每个人都沾点情分似的。屠广福的女人倒是利索,拿这毛线毫不含糊地给大女儿打了件毛衣。倒不是她格外心疼水英,而是家里的传统历来如此,大的穿了二的穿,二的穿了三的穿,这样才算物尽其用,丝毫不浪费。还剩一点毛线,她给男人织了双毛线袜子,又给强烈抗议的水芹织了双手套。织手套已经很勉强了,左手有三个手指头是拿另一种颜色的旧线补上去的,看上去非常显眼。水芹很生气,把手套扔给水英:“你戴!你戴!家里啥玩艺儿不是你先用?”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纠纷。
风波过去以后,有一天水芬打扫屋子,扫出角落里扔下的一双手套,带三个另类的手指头的。她捡起来,就着昏暗的光线看了又看,忽然有种别样的亲切,那三根手指头像伸出来,挠她的心。她把手套掸掸灰,戴上了。水芬看看戴上手套的手,这双手好像文雅了许多,没有那么粗糙了。她把手捂在脸上,感觉到毛线特有的痒痒的温暖。她只有躲在这里悄悄地珍爱自己一下。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拥有一样崭新的东西。
别人可能不注意,但是大姐水英注意到了。水英发现大妹把手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晾晒之后收进大妹自己的衣服箱子里,她就明白水芬的心了。
那天晚上,水英和水芬闲聊——这是难得的,一般有空闲时间水英都是看书。说到村里谁家说上了亲事,又有谁家应承了亲事,水英忽然起身,从箱子里捧出了那件孔雀蓝的毛衣送到水芬手里,恳恳切切地说:“芬女子。”
话到这里就顿下了。这么一来,它变得郑重其事,像一个嘱托,像一个任命。
“芬女子,”水英已经有点伤感了,“我们屠家没有儿子,就三个女子,如果我读书读不出头,家里就没啥靠的了。没办法,我只得把书读到底,考大学,找个城里的工作,以后你们才算有条门路。女子家迟早是要散到别家去的,婚事么,我这几年想都不要想了,你不一样,你会是我们家第一个嫁出去的……嫁了,也要想着点娘家的好,多帮衬着家里,水芹那丫头是没指望的。”水英觉得头绪乱乱的,那些话说出来,像个走夜路的人,哪里都是路,却不知哪里可以走出去。
水芬已经淌出泪了。水英还要说,这毛衣我没穿过,你穿,你穿,你从小到大没穿过新的,别记挂娘家的这些委屈,啊。
水英反反复复地叮嘱,直到水芬把脸埋进毛衣里,肩膀一耸一耸,哭厉害了,可是头却一下一下地磕着,表示点头了。
偏偏屠广荣家来了个杜孃孃。
怎么会来个杜孃孃呢?简直是从水芬的命里硬闯进来的一颗石子。水芬是水,弱水,涓涓细流,随便一颗小石子往那儿一扔,水就分流了,改道了。
杜孃孃这样的女人,活得才叫精神十足,四十多岁的人了穿得比杨家湾待嫁的女子还艳气,大花大朵的衣服一身地披盖下来,看得人眼珠都发了岔;人又热情,嘴甜手快,一来就把你家婶婶的胳膊挽住了,七倒八拐地攀上亲,要你答应哪天农闲了去她家坐坐——她家哪是随便坐得成的呢?人家住在老远的大城市,火车也要坐上三两天的。可是难得这番热情,大伙嘴里也都答应着,想着万一哪天去了那个大城市打工呢,总也有条路吧。杜孃孃是令人愉快的,她喜欢和上了年纪的大娘拉家常,中途常常瞅着大娘某个年轻的女儿,心疼地看上半天,末了向大娘说,这女子长得像“年轻时的我”。这么一来,女子也和她亲了,近了,仿佛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未来。杜孃孃还会打开一个大大的皮包,拿出一串珍珠手链呀玉石胸坠之类的,一把抓住那女子的手往她手心里塞。女子的手就像受惊的小兔子挣呀逃呀,总还是带了些留恋意思的。杜孃孃那手,这时候就像个男人的手,孔武有力,不容挣扎,嘴里说:“缘分!缘分!孃孃没女儿,只当收个干女儿吧!哪有见了干女儿不给见面礼的!”话既然说到这份儿上,连大娘也会腼腆地示意女儿收下来。收下来,这干女儿就算是认了。杜孃孃来的时日不长,干女儿倒认了三四个。那几个被认了干女儿的,一个个跟捧上了天似的,说话都带点“飘”。女伴们传看着那几样见面礼,神情都是羡慕的,眼睛都红了。那一阵动不动就有人私下里互相打探:“杜孃孃认你当干女儿了没?”好像是种身份,是种荣耀。
原本这一切都和水芬没有关系。她长得不够好看,身材又是体力型的结实蛮壮,哪会像年轻时的杜孃孃呢?怎么会被杜孃孃收为干女儿呢?怎么配得上那么好看的手链和胸坠呢?可是她和屠广荣的女儿屠丽娜要好,这就使她具有了某种契机。屠丽娜也是水字辈,本来该叫屠水丽或屠水娜,可她前面有三个哥哥,生到她才终于生成了小凤凰,父母乐坏了,当成宝贝疙瘩,执意要给她取个洋气的名字,以示与众不同。看看,人家连名字都敢反传统反宗族,能不横吗?屠丽娜打小就被惯坏了,脾气大得很,还瞧不起人,反正有三个哥哥给她撑腰。许多同龄的女子对她惹不起躲得起,只有水芬,温温和和的,又没什么心眼,屠丽娜倒和她处得来,啥话都要和她讲。那天丽娜拿出一只镯子给水芬看,亮晃晃的,一来就把人眼晃花了。她悄悄说:“看!姨妈给我的!纯白金的!那些干女儿都是认的,又不沾亲又不带故,给的都是次货;只有我才是姨妈嫡亲的侄女。”说话时不停地摇头晃脑,得意非凡。水芬记得开始时丽娜说过,杜孃孃是她们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自己找上门来的——说这话时杜孃孃肯定还没给她这只镯子。
丽娜和那几个“干女儿”很有些宿怨——当然也不过是些东家长西家短的小是非。在这件事上,她总是不服气,自己的姨妈,就这么稀松平常地当了那几个小骚货的干妈,白白便宜了她们!她带着较劲的性子说:“水芬,你哪点比她们差?又不像她们疯疯癫癫的,走,上我家去,我叫姨妈也认你当干女儿!”她是说到做到的,一把就扯住了水芬。水芬吓慌了,袖子被丽娜拽出去老长了还使劲躲:“我不去,不去……”哪有上门硬要人家认干女儿的?水芬还有个脸面。丽娜说:“放心,我说话讲分寸的。”死拉活拽把水芬拖到家里去了。
见了杜孃孃,丽娜就专拣水芬的好处说,能干啦,卖力啦,手巧啦,孝顺啦,还不多言多语啦。水芬平素没有仔细分析过自己,给这么一说,自己也没想到有那么多优点,忍不住把个脸飞红了。杜孃孃上上下下打量着她,一边听丽娜的汇报,一边满意地点头。丽娜差点问:“姨妈,她像不像年轻时的你?”又觉得太露骨了,说不出口。
杜孃孃一直点头,点头,微微笑着,把水芬的头发都一根一根看过了似的,还是没有说话。丽娜有些泄气了,水芬更是臊得不知往哪个地缝里钻,却见杜孃孃去开皮包了。一见开皮包这个动作,两个人都有了希望,屏住呼吸盯着那只手,在包里翻呀拣呀,最后出来了,拿的却不是手链胸坠,是本相册。水芬心里又在打鼓了:里面是杜孃孃年轻时的照片吗?她对自己是否像照片上的人物根本持怀疑态度。杜孃孃冲她招手:来,来。她走过去,丽娜也拢上去。相册翻到一页,杜孃孃指着一张照片给她们看。上面有三个人,杜孃孃站在中间,一边站个老太太,慈眉善眼的,一边站个老头,穿着威武的军装,肩膀上两个黄灿灿的牌牌,又是星星又是杠杠,挤也挤不下似的。杜孃孃说:“这是我阿姨和姨父。姨父是个大校呢——部队里顶大的官,懂不懂?你们看,他们是不是好人?”水芬丽娜赶紧点头。杜孃孃舒缓地叹口气,说:“水芬,也是咱们有缘分……”水芬的心怦怦乱跳,来了,“缘分”终于来了。“我阿姨和姨父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他们是中国的大功臣,懂不懂?他们有个儿子,独生子,长大后也参了军,但是几年前在一次泥石流抢险工作中牺牲了!才二十多岁就当了烈士,懂不懂?”两个女孩使劲点头,水芬眼里都有泪花了。“我阿姨姨父都老了,身边又没人照应,老早他们就拜托我,到乡下探亲戚时给找个放心的丫头来,说是做保姆,其实人家是打算当女儿看待的……”
话到这里已经有相当明显的用意了,水芬再笨也听得出来,连丽娜都听傻了,竟带了无比妒忌的神色。杜孃孃偏偏在这时把话头打住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自顾自地在桌上寻了碗水喝起来。水芬那一分钟像过了漫长的四季,春夏秋冬,冷暖自知。她浑身颤抖地意识到,她还有可能拥有另外一种人生,与从前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她甚至来不及想那种人生的结果,或出路,她没有想,有的只是颤抖。杜孃孃多么精明的人,留出这一分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空白下的时间、空间只有更拥挤、更窒息的。水芬已经头晕了,呼吸不顺畅了,窗外的光线刺眼地射进来,罩在柜子上、桌面上、人脸上、都有一层光环似的,杜孃孃在这光环里动情地笑了,她伸出手,那只像男人的大手在水芬头上轻轻抚摸:“水芬你是个好女子,谁叫咱们有缘分呢……”
就是那一年冬天,水芬就跟着杜孃孃走了,去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保姆了。一同走的还有杜孃孃“嫡亲的”侄女屠丽娜和两个干女儿。那些女子可不得了,一听说杜孃孃要给水芬找那么肥的一门差事,差不多把屠丽娜家的门都给挤破了。也是,谁不想过好日子呢?究竟什么叫好,或是什么样的好,她们也说不上来,但是只要离了杨家湾,好日子总会来的。
初步的打算是这样:两个干女儿到一家鞋厂做女工,每月也有七八百元的收入呢;屠丽娜则去学打字,学成后到杜孃孃熟人开的公司里当打字员——说得好听点,是做“文秘”。屠丽娜非常满意,显然“文秘”和“保姆”、“女工”一比,身份的优越性就很突出了。别人也没话可说,再怎么说人家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也要亲上一层的。
女子们走的那天村里热闹非凡,虽然没放鞭炮,但女子们的笑声比鞭炮还脆亮,还耐听。乡亲们热情高涨,说说笑笑的,空气里洋溢着激动的情绪,一点也不亚于一年前狗娃子当兵和两年后水英上大学。几个年轻女子穿上了最上台面的衣服,尤其是屠丽娜,专门到镇上去烫了个头发,置了件时髦的大衣,大衣是乳白色的——这种极不耐脏又不吉利的素色曾引起了女长辈们不理解的小规模非议,最后是屠丽娜的母亲平息了风波,她努力用民主派家长的开通口气说:“哎,这代女子,又不在杨家湾过一辈子,随她们去吧。”婶婶大娘们无话了。是了,人家是飞出穷山窝的凤凰了,不用在你的舆论监督下过日子了,你自作多情地批评指导又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