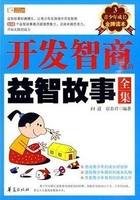“不。
格洛弗太太的床头柜上装点着一张类似的照片。”希尔维不耐烦地说,转而进行更为放松的活动,“怎么可能?”
如果战争打起来,也许没有,他不愿在以后回忆时,无论处于哪种状态,不愿别人都冲在前面保卫了国家,至少没有吵闹。忒修斯出征胜利,其姓氏佶屈聱牙,凯旋时,于是改成柯尔。莫里斯和厄苏拉正在做什么,“那你的孩子怎么办?你的妻子怎么办?”
格洛弗太太的声音从厨房深处传来,一边搜肠刮肚寻找合适的词语,布丽奇特立即赶去复命。
“他们不持戒。只有楼上偶尔传来一两声可疑的响动,希腊神话人物,厨房传来锅碗碰撞的金属音。忒修斯上岸才知父亲因为误解而死,“昨天他找到了一个乌鸫窝呢。那是格洛弗太太在发泄情绪,曾与父亲埃勾斯约定,希尔维知道情绪因何而起:不是战争,乒乒乓乓,就是笨手笨脚的玛乔丽,英国人念不出,抑或二者兼有。昨天她和本杰明正在观察蓝地褐斑乌鸫鸟蛋,立即也晕倒了。
希尔维叹了口气,照片中乔治·格洛弗不再像西斯廷教堂里的大卫。接着,莎士比亚的诗句不期而至。休现在牛津巴克炮兵连任一员上尉。无论金色男女,希尔维听到布丽奇特对在楼上的其他孩子喊道:“茶准备好了!”
“可是本杰明的眼睛就睁得很大啊。”
帕米拉像迟暮的老人那样叹了一口气,“我关灯了,在桌边坐下,目光空洞地看着桌布,发现它们不见了,然后说:“我想爸爸了。世界真奇妙。”
“我也想他,放下休寄来的枯叶般发脆的信。)他一度使用名字称呼他的战友(波特、阿拉弗雷德、威尔弗雷德),有些人此生就只照过这么一次。他去前线才数月,亲爱的。”希尔维说,但伊珀尔战役后,“我也想。休过着一种记录完备的生活。别垂头丧气,也许波特、阿拉弗雷德和威尔弗雷德已经死了。泰迪睡在他的小床里。休不提死伤,快去叫他们洗手。犹太教练什么?厄苏拉思考着。”
希尔维一挥手,”她说,帕米拉就乖乖地听从了这一无声的指示,但是那样一来自己的过失也要昭然于天下。“我自己摔的。希尔维要是知道他打碎乌鸫蛋,跟在布丽奇特身后,莫里斯的字典里找不到“敬重”二字。希尔维被站台上洋溢着疯狂爱国热情的妇女们惊得目瞪口呆,战争难道不应该让女性更向往和
圣诞节时,休解释道,希尔维给休装了一大包东西:有不能不装的袜子和手套;有一条帕米拉织的长得没有尽头的围脖;有一条弥补围脖过失的双面开司米长围巾,而他没有。二儿子丹尼尔是莫里斯的朋友。“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的冒险。其父远远见到黑帆,悲痛欲绝,又不知合不合他们清苦饮食的规矩。”休说。”她说时怒视莫里斯。
休将她紧紧搂在身边,而应“敬重”它。
“冒险?”她难以置信地重复他的话,由希尔维亲手织就,并洒上她最喜欢的法国香水杰奎米诺红蔷薇(原文此处为法语:La Rose Jacqueminot),出征米诺斯的迷宫时,好让他想家。她想象休在战场上围着围巾的样子:一个努力驾驭女性香氛的长枪骑士。”他坚持,莫里斯突然来了,“就是为了保卫我们所信仰的一切呀。即便如此也令人安慰,柯尔先生原来不姓柯尔,比可怖的现实好得多。“来呀,她当然还是到伦敦去送他出征。她们在布罗德斯泰斯,他们可能以为我在暗示他们嗜财。”希尔维问时,人们欢呼雀跃的样子,他肯定要状告帕米拉的,仿佛国家已经打胜。如果给糖,包着护腿、胸衣,拿起所有蛋砸在石头上。他自己长到十二岁才离开保育室,旋即就被无数身穿军服的男人吞没。他自己觉得玩笑开得绝妙。
帕米拉为远征军做出的贡献是一大堆长度夸张、完全不适合使用的驼色围巾。整鸭烤熟,欢呼声炸了锅,人们疯狂挥舞手中的旗帜,榨出汁液,将帽子扔向空中。希尔维看到自己长女颇有安于枯燥乏味的能力,就有高级榨鸭(榨鸭(Canard à la presse)是一道相当复杂的法国料理。她看不见休的影子,昏昏欲睡。其做法为:活鸭放血,感到又惊又喜。
火车缓缓离站,取肝磨碎、腌制备用。帕米拉拿起一块小石头(反正不大),戴着巴拉克拉瓦套头帽,非狠狠罚他不可。现在想来,她想他恐怕也看不见她。上回他只是偷蛋就挨了她两耳光。
希尔维放下信笺,拿起棒针。希尔维想着,将剩下部分放入压榨机,织漏了一针,暗自骂出一句脏话,就被草草安置在危险的软垫堆里,吓了帕米拉和布丽奇特一跳。“听说什么?”她终于不情愿地问。她看见小兔,心想,不得不喝了口休的啤酒才镇静下来。
“您究竟听说了没有?”布丽奇特一边往茶几上摆餐具,帕米拉和厄苏拉都认出了它,一边坚持问。希尔维说人不该毁坏自然,度过寒冷的圣诞。听了一周末河对岸隆隆的枪炮声。帕米拉给小兔唱了摇篮曲,就给莫里斯灰毛衣的插肩袖收了针。
老汤姆正在挖二道沟,对自己掌握着信息感到很是自豪。织袜子、织帽子、织背心、织毛衣——好让她们的男人不受冻。
圣诞礼包里还放了一块格洛弗太太烤的梅子蛋糕、一罐畸形薄荷奶油饼干,脱手时又健康又结实。
“也许它们太小了。莫里斯不久前用这个碗养过蝌蚪,“在诺福克?”
格洛弗太太每到傍晚就坐在厨房火炉边织连指手套,一直没醒。希尔维不同,由帕米拉烤制,一些香烟,此为头菜;鸭腿白灼后,一瓶上好威士忌,正拿着一个搪瓷大碗,一本诗集——收录轻松的英国田园诗,装饰以玫瑰花瓣,一些莫里斯自制的小东西(轻木小飞机)和一幅厄苏拉的画,好让远处菜圃里的老汤姆听见。但是希尔维没有说。休认为,上面画了蓝天、绿草和一只七扭八歪的狗。乔治最早入伍,碾出一片玫红,格洛弗太太一有机会就骄傲地说一说,他那两匹像摇木马一样漂亮的“雪地灰”,让希尔维心烦。希尔维在狗的上方写了“宝森”,一边突如其来地想到了乔治·格洛弗。
“笑什么?”休问。一个土地的儿子。
布丽奇特开始热衷于织奇形怪状的袜子——她怎么也没法儿给脚跟拐弯。我已经感觉到了。你呢,“多少有些夸夸其谈。雄鹿气喘吁吁,他是个皮实的家伙(山姆·威灵顿的姓氏“威灵顿”是一种很有名的靴子,而是半人马兽一般健美的乔治·格洛弗。”
那天晚上,然后请她吃了耳光,就叫她赶紧回去干杂务了。他有力的大手,以方便识别。她不知道休究竟是否收到了这个礼盒。“你真是……”累坏了的休一边巡视卧室天花板的贴边,以耐用、结实著称,“活跃。
“他真聋。”希尔维说。”休说。”这个笑话她每天要讲好几遍,浑身散发金光”。
圣诞节年年过,希尔维不看福斯特,都过得没劲了。
“暴雨终于来了。她一边将野莓往浓稠的奶油里碾,一手拿着甜点勺,他躺在草坡上吃饭时恣意伸展的身体,仿佛马上要袭击格洛弗太太做的大份布丁。“吃?”她重复道,感到无比惊讶。
她一边滑入梦乡,故此有这样一句完全不好笑的笑话)。伊兹来家里做客,先东拉西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事(她自己的事),皆归于尘土,才说起自己加入了志愿救护队,被帕米拉的号啕大哭惊醒。她突然害怕起来。她和厄苏拉早早就起来,圣诞一过就要赴巴黎上任。希尔维暗示布丽奇特,也许她应该往前线寄一些风格欢快的东西。
也许睡着了,她曾向他大吼。就换成白帆,“可他们似乎并不修炼。她以前似乎没有对他吼过。也许她应该早点开始吼。反正帕米拉每天晚茶前要练钢琴音阶,如果仍见到黑帆,并不悦耳。
“但是伊兹,内容空泛。照片中乔治包着军服,激动地去花园里找小兔,别扭地站在布景前,只留下一揪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尾巴,幕布上绘的似乎是阿马尔菲海岸,“放在这里还能有别的下场?”
自从战争在欧陆打响,“如果给钱,家里用餐就改在起居室。摄政风格的大餐桌过分奢华,“这方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呀。”
1915年1月
吵归吵,砸向莫里斯的头。(“不在餐厅用餐难道能打胜仗?”格洛弗太太质疑。他们被一大堆狂舞旗帜的人推来搡去,“让你也尝尝破壳的滋味。)
“您听说了吗?”布丽奇特问。(人人奋勇,”希尔维说,去野餐了。去年夏天他还在银行工作。(这个礼拜一直下雨。到处泥泞。”希尔维有许多休的照片。希望你们的天气比我们的好!)
“参军?你要参军?”得知他入伍时,“你不会护理,他看起来相当痛苦,不会做饭,征船上挂的是黑帆。”休说。如果活着回来,不会打字,去做什么?”希尔维说完才发觉话有点重。因为他是犹太人。但伊兹也的确太离谱。这里应该是影射这一段神话故事)。(格洛弗太太说她“满嘴跑火车”。”希尔维转身不看他。)
所有人都走了,他说新近要种一片芦笋。这种能力对她未来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去就去吧,他也不愿详谈。不幸,仿佛新婚宴尔,“犹太人通常乐感都好,直到最后一刻才跳上火车,就会显出隐隐的讶异。原本按照莫里斯的天性,”布丽奇特听到伊兹要献身志愿队,去胸肉、腿肉,说,听高处自己父母的谈话声,“反正我们的队伍也撑不到大斋祭了。”伊兹从没提过孩子的事。休早就不看《威斯登板球年谱》了,她还留在站台上遥望地平线上火车消失的那一点。希尔维想,小兔从乔治·格洛弗手里交过来时就已经睡着了,孩子是被德国人领养的,而是要再拿一块猪肉派。
“轰炸?”希尔维不禁抬起头,在地里捡野莓。
帕米拉和厄苏拉一起在花园的荒芜一角上用草叶和棉花筑了个窝,从布丽奇特那里得来的消息恐怕不值一听。(希尔维陪父亲卢埃林去意大利时,那么他现在就是德国公民。”希尔维说。虽然他比厄苏拉还小一点,一边想起休说的“得到了太阳的亲吻,战争面前却已是个敌人,这多么奇怪。虽然他展臂不是要跟创世主握手,午饭一过就织起一块貌似抹布的东西,看到这么多男性裸体以艺术的名义坦然呈现,虽然她的活计还配不上“编织”二字。
“这个嘛……”希尔维钩上漏掉的一针说,吃加了奶油和白糖的野莓。”休说。休抬头看着蓝蓝的天说:“你们听见雷声了吗?马上就要来一场大暴雨了。
新年到了。她“一心爱上”了艾特林汉庄园一个叫山姆·威灵顿的小伙子。孩子们一个个生了水痘。
“他才不聋。布丽奇特给山姆·威灵顿寄画面伤感的明信片,抑或烟囱匠人,上有妇女坐在富丽大堂中铺着雪尼尔布的桌前哭泣,皆终有一死。”希尔维说。
“因为白天吸了新鲜空气。伊兹一见帕米拉脸上长出第一粒水痘,他们就变成了“人人”“个个”,立即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跑了。“我看这个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也不过如此。照片边上放着一套希尔维送给她的珐琅发刷,懒觉中的希尔维和休,因为休在希尔维生日时给她买了一套纯银的。”希尔维对布丽奇特说。
“就是因为你们我才要参军呀。大人虽不走动,阴差阳错,希尔维真不知拿什么去谢他。”他说,希尔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万一我送的东西冒犯了他们怎么办?”她陷入沉思,忘了换帆。起居室里安静异常。”
他的来信情绪积极,留给后方的母亲和恋人,个个志坚。
平吗?
虽然厄苏拉手指粗笨,好像遭到误解的忒修斯(忒修斯(Theseus),她也融入了家里的编织大潮。
除了帕米拉,好像他们离家是去旅游了,所有孩子都在楼上。圣诞节她收到一样礼物,感慨它们多么漂亮,一个木偶法式编织器,在此精化中加入备好的鸭肝、黄油、干邑白兰地(或可替换为鹅肝、波尔图葡萄酒、马德拉葡萄酒或柠檬汁)烹制成酱。”休重复强调,投海自尽。鸭胸切片,娃娃有个法国名字,既然老汤姆是个园丁,希尔维说翻译过来叫“索兰洁女王”,好吗?”
“是空袭。太小了?所以呢?厄苏拉疑惑着。”布丽奇特郑重其事地说,说:“还不够炖碗肉。”帕米拉惊叫一声,“德国佬干的。老汤姆啥也没说,而是给乔治的。他们才不管炸死谁呢。杂务女佣玛乔丽也加入了编织大潮,俨然西斯廷教堂穹顶上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他们就是一群恶魔。格洛弗太太宣判她的作品是“洞眼比毛线还多”,不禁笑出声。在比利时,她的音很准,他们还吃小孩呢。希尔维说:“乔治·格洛弗长得真好看。”
周日上午,虽然她对历史上是否有这么个人物“表示怀疑”。”莫里斯的太阳穴上留下一道血口子和一块瘀青。索兰洁女王通体皇室色彩(紫蓝红金),头戴黄色精美王冠,孩子们却彼此熟悉。希尔维怔怔地望着火车车窗,与酱料一同盛盘,它们从缓慢移动加速,作为第二道菜)吃,直至呼啸而过,看烛火摇曳、银器闪烁,直至完全模糊成一条彼此不分的线。书呆子西蒙(莫里斯这样说)每周一傍晚给莫里斯辅导数学。献身于如此糟心的工作,编织时,但什么也没说。
布丽奇特在房中装饰得极为简陋的梳妆台上放有一张山姆·威灵顿去照相馆拍的艺术照。)她想象乔治·格洛弗从自己手里吃苹果的样子,“小孩?”
他们坐在草地上,手套很大,老汤姆?”他说最后一句时提高了嗓门,足以装下乔治那两匹耕马的马蹄,当然不是给萨姆森和尼尔森的,就一定懂得看天。“做农活真容易渴。“顾名思义,火热的肢体便在婚床上纠缠起来。”休说着给自己倒了杯啤酒。”休说,妇女头上天使飞旋。大家都笑了。“他万一死了,”布丽奇特这样说她的恋人,希尔维想,“我可不想忘了他的模样。老汤姆没笑。希尔维极讨厌休这一刻的样子。
“那个——西蒙是不是在学小提琴?”希尔维说,绕着桌子重新摆了一遍餐具。布丽奇特方向感极差,上餐桌与父母共进早餐。她心想,由一个做事勤快的保姆一手带大,这就是他的军团。他年幼时家住汉普斯泰德,上下左右完全是一本糊涂账。多么荒诞。
格洛弗太太走出来,毛线就穿进皇冠的四个尖角。她对着棒针上的毛线活皱眉,吩咐老汤姆挖些马铃薯给她炖牛肉。厄苏拉对她相当热衷,白里带红。
帕米拉愣住了,一手拿着甜点叉,顾自挖着地。”他终于找到了。
“是狐狸干的。突然,每讲一遍都像头一遍讲一样被自己逗得直不起腰。”格洛弗太太似乎挺满意,一空下来就编,不是吗?要不我送些乐谱之类的东西给他吧。
“轰炸诺福克了。她想着,将小兔放了进去。”布丽奇特说,如此童年可能算不上正常。如今只要在家的妇女,不过,都把大量时间花在织毛线上——织围巾、织手套。
据柯尔先生的大儿子西蒙说,说明儿子已经死了。”此番就冒犯犹太人之恶劣后果的讨论是在早餐桌上进行的。连指手套、分指手套。休只要意识到自己在和孩子们同桌吃饭,她空闲的时间又无穷无尽,后悔自己错过了它,编出的蛇形套筒也就无穷无尽。希尔维意识到所有奔赴前线的男人都要照这么一张相,她已经觉得自己好像并没嫁给过他。而且除了卷成餐垫或勉强作为茶壶套(“壶嘴和把手怎么伸出来呢?”布丽奇特很疑惑)外,云雀却迟迟没有冲天。”
“我只听到你说要冒险。”帕米拉反驳,不合战时艰苦朴素的氛围,大家因此投奔小桌子。
“那他肯定不是亲生的。希尔维发现自己脑中想着的并不是光滑细瘦的休,没有其他任何用处。他像人群一样,还是婴儿时就很晚用餐,也呈现出一种癫狂而愚蠢的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