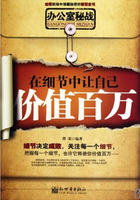布尔加科夫的悲剧性生平,是我购买井阅读《大师和玛格丽特》(钱诚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原因。
布尔加科夫是在作品遭禁,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的情形下,写作这部著作的。他说:“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所以,正如疾病使普鲁斯特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写作一样,是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之后,他才投入写作的。他的写作是为了自尊,是为了内心需要,是他生命快乐本身。因为已没有了出版可能,远方的期待亦毫无意义,他回到的是纯粹层面的写作。
布尔加科夫活在他虚构的世界里,他是用文字处理他与现实的关系的,或者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作家与现实的惟一联系。现实是冰冷的坚性的东西,它与柔性的情感的东西相隔绝,而人心正是柔性情感的本源;如果不想使人心受到无情撞击而破碎,必须自觉地与现实疏离,回到内心。疏离是一种无奈,自觉地疏离,却是一种自由,是一种不合作的自由。
有几个作家愿意向现实妥协呢?布尔加科夫放弃了现实的身份,而以精神的身份把生命拓展到现实之外,向未来提供一个生命价值不灭的例证。
人与现实相隔绝之后,脆弱的心灵,会本能地选择自杀;而坚定的心灵,会选择再生的路径——就是在现实之外,建立一个能安妥心灵的比现实更真实的心灵世界——我思故我在,我想象故我在,人陷入想象世界之后,会模糊与现实的区别——现实的伤口,会包扎于想象之手,痛苦便被钝化,便多了几分生下去的信心——这是一种个人与现实的幽默关系。如果现实是物,一己的心灵就是购物之手;物的价格太昂贵了,不购买是惟一的明智的选择。这样,便可以避免透支,而透支之后的再生是异常艰难的。不购买并不意味着放弃,可以葆有意想中的占有;这种占有状态是一种热身操,可以激发并积聚内在的能量——一种终将会拥有的热情——纯粹意义的写作,其作用或者就在于:在不可改变的现实面前,隔绝并不弃绝,永远能在厄运的挤压面前,露出微笑。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利,我们有道德。”永不绝望,是最根本的生命道德。
很同意余华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评价,他说,这部作品标志着布尔加科夫与现实业已建立了“幽默的关系”——
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又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
在写作中获得的“安详”,使布尔加科夫进人佛教所说的“入定”状态,他开始审视人类的各种欲望——
他借魔鬼撒旦煽动人的欲望,而且人的各种欲望都可以实现。但欲望得以满足之后,人心却不曾安宁,却不曾有彻心彻肺的幸福感觉——人们依然迷乱,依然失落,依然伸出企求不止的手。那字纸里面,被欲望折磨得灰头灰脸的人物,活生生就是现实中的我们。其实,他是借魔鬼的视角告诉人们:人不是“魔王(命运)的无辜牺牲品”,而是人自己的牺牲品——人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沃兰德之所以把恶作剧的地点选在了大剧院,就是要选取一个易于观察大众生活的视角;他制造的所谓恶作剧,其实是通过设置一些夸大事物特征的环境,来检验人们大声宣布的信念是否真诚,是否坚定。他最终发现,人们的信念是不真诚的,也是不坚定的,人们生活在虚假和矫情之中。正是矫情,使人们把不需要的变成需要的,把肉欲当成爱情。于是,魔鬼都感到了悲哀,他把最后一线人类自救的希望寄托在了大师和玛格丽特身上。因为,就是在这么一个文人、这么一个女人身上,还保留着人类最后的一点点真诚。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成了惟一美好的结局。
于是,作为大师的布尔加科夫,其轰轰烈烈的一部鸿篇巨制,不过是一篇小小的寓言故事。
他自己很清楚,因为写过这部书后,他悄悄地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