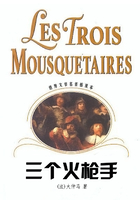这一夜没人再审于旺田,也没人理会他,关了他在小屋里继续睡大觉。却又睡不着,身上仍是烧,冷一阵热一阵,冷起来浑身打哆嗦,烧起来又是大汗淋漓。脑子里也尽是些胡思乱想,不知孟乡长和林所长要怎样发落他,要是送到县法院判个三年两年的可就糟了,那水秀谁管呢?水秀他哥的钱谁给寄呢?于旺田又想到吕书记,那可是个好心人,也不知他知不知道这些事,他要过问一下就好了。我可是为了他才去偷朱老九田里的蟹子呀。天地良心,偷多偷少,还能落到我于旺田手里一分钱吗?
到了这一刻,于旺田已认可了自己是偷,既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的事,不认又有什么用呢?
似睡非睡地又苦苦挨过一夜,天亮时,一个年轻的小警察打开小黑屋的门,把于旺田带到乡政府的院子里,指着地上的扫帚和锹,说你打扫院子吧,扫完了就自己在院子里找活儿干,谁让你帮着干啥你就干啥,只是别想跑,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旺田身子软软的,酸酸的,忙说不跑不跑,我往哪里跑呢。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底,看起来事儿不大了,不然怎么不关不审了呢。想了想,又怯怯地问:“那我的事……啥时算完啊?”
小警察说:“我先给你透个底,过一会儿所长上班后还要正式向你宣布处理意见。留你在乡里干半个月的杂活,算作劳动教养,再罚你三千块钱,交不齐你别想回家去。”
于旺田先是一乐,看来不用坐牢了;紧接着又是一愁,三千块钱啊,自己给人家养了半年多蟹子也没挣到手三千块钱,这可不是笔小数目,可上哪儿张罗去呀?他迟疑了一下,苦着脸说:
“同志,我是真屈呀,屈到家了。我认屈,让我干啥埋汰卖力气的活儿都中,再多干些日子也中,就不能不罚了?”
小警察说:“这话你跟我说也没用,是头儿定的。”说着,四下扫了一眼,小声说,“我看你就偷着乐去吧,这还是我们所长替你说了不少好话才争下来的呢。他是看你老实巴交的不像个惯犯,罚到为止吧。要依乡里头头的意思,还不知想咋收拾你呢,就是罚也不止这个数,你不也得干擎着?谁让你手欠去偷了人家呢?”
说话间,水秀骑着车子进到院里来,后架上还带了不少东西。父女见面,没张口,眼圈都红上来。小警察说了声:“是你闺女吧?”转身回屋去了。水秀到了跟前,手抚着爸爸额上的伤疤,泪汪汪地问:
“爸,他们打你了?”
于旺田忙摇头:“没有,没有,爸摔了一跤,蹭的。”
“疼吧?”
于旺田还是摇头,“不疼了,不疼了。”这才想起问女儿,“你咋来啦?”
水秀说:“水丰哥到家告诉的,说是从今儿起开始给你送饭。苏大姨让我给你带来被褥,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手巾肥皂啥的。”
于旺田急着问:“你苏大姨还在咱家呀?”
水秀奇怪了:“咋不在呀?为你的事,大姨急着呢,两眼都哭肿了。”
于旺田心里酸酸的,又问:“她……没对你说啥?”
“说了。她说你不是做贼的人,你是先被狗咬了一口,想回身咬狗时,反叫恶人抓住理了。天下老实人尽吃这样的亏,要你不要为这事抬不起头。她还说,如果乡里这事处理的不公平,她就到县里市里去找去告!”
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于旺田的泪水突然哗哗地流了满面。他拉着女儿的手,说:“秀,要听你苏大姨的话,那是跟你妈一样亲的人啊!”
“爸,我知道。”
水秀眼圈又红上来,抹了一把,忙着把饭盒送到爸爸面前,打开,是油汪汪的葱花烙饼,还有香味扑鼻的辣椒炒鸡蛋。
水秀说:“苏大姨让我告诉你,让你想开些,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把身子骨养结实了比啥都要紧。哟,我差点忘了,她说出事那天你正闹病,还让我给你带了药来。这是她昨天特意跑县里药店买的呢。”
于旺田接了药,紧紧抓在手里,说:“给你哥写封信,就说这些日子家里紧,先让他自个想想办法,伙食钱过些天再寄他。我的事别跟他说。”
“苏大姨昨天进城时已给我哥把钱寄去了。她跟我要的信址。”
“她哪来的钱?”
“她没说,只让我告诉你,家里的事不用你惦着。”
捧着饭盒,捧着衣物,捧着药片片,于旺田只觉浑身热呼呼的,陡然生出许多力气,那病后的虚弱与倦怠如日光下的晨雾一般,悄然飘散。谁说非得日久见人心?真是难得的好女人啊!
水秀忙着上学,推车要走。于旺田总觉还有点事,就在水秀骗腿上车的时候,忙又叫住了:
“秀,咱家的那三亩蟹田,谁看呢?”
水秀气堵堵地说:“爸,你真是,为那几亩别人的蟹子,你苦头少吃啦?还想它!”
“咋能不惦着,侍候了一春一夏,有头没尾呢。”于旺田叹口气,苦笑道。
“昨儿后晌孟乡长已带人起出去,卖啦。”
“起出多少?”
“听说有一亩也是一百来斤,另两亩多,一亩137,还有一亩整整140,是咱屯里单产最高的呢。苏大姨说了,割稻的事你也不用惦着,等晾过两天,她割。”
“卖蟹的时候,孟乡长没再说啥?”
“爸,你吃了一大捧生豆子,咋还不嫌豆腥呢?”
水秀骑车走了,于旺田站在那里发怔。一样的田,一样撒苗一样伺弄,那两亩咋就产了那么多呢?哦,是了,是了,一百三四的必是混账的朱老九还没来得及下手偷的那两畦,那两畦离他家的远。这么算来,黑心贼那一夜到底偷去了我多少啊?唉,有了这两亩也好,多少也算个见证,吕书记和孟乡长总会知我于旺田是个啥样人了吧?
从这天起,水秀上学时顺便将一天的饭菜送来,晚上放学时再把饭盒带回去,每天都是大米饭馒头油饼,有时还有包子饺子,都是过年般的嚼货。住处也由那间小黑屋移到了另一间闲屋子,里面有一张床,现成的铺盖,是备给警察们夜里值班用的。于旺田自有行李,便将那铺盖卷了卷,移放在一边。他每日扫扫院子,帮食堂备备柴火,择择菜,有时也跟在乡机关的人后面进进城,人家采买东西,他帮着提拿,就像电影《红岩》里的华子良。人们见他憨厚老实,手脚勤快,也不欺负他,到了夜里,值班的警察还主动招呼他到另一间屋子看电视,指着暖壶和茶叶筒,让他自己沏茶喝。这般过了几日,于旺田有时在乡政府走廊里的大镜子前照照,竟比在家时还显白胖了些,便笑着暗骂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于旺田只是对每日的那般吃食不过意,家里趁个啥呀?自己又不是住院养病。水秀再来时,他便说:
“家里平日吃啥,就给我带点啥,可别单整了。”
水秀说:“家里不用我做饭,给你做啥你就吃啥呗。”
于旺田问:“你们在家也是这么吃?”
水秀说:“苏大姨让我吃,说我功课紧,要补身体,可她却连筷子都不伸,每日还是大饼子白菜汤。”
于旺田心里感动,说:“秀啊,人活一世,得讲良心,你亲妈活着时对咱爷几个又能咋样?到啥时咱不能对不起你大姨呀。”
水秀说:“爸,我不是三岁五岁的小孩子啦,我懂。”
到了第九天的半夜里,于旺田突然被惊醒,隔壁狼哭鬼嚎般地叫,细听听,竟是那朱景发的声音,也不知警察们在用什么手段收拾他。又听孟乡长在低声吼:
“你不是犯法的不做吗?你不是犯不到我的手里吗?你不是滚刀肉鬼难拿吗?这回我等你去上边告,告吧!”
朱老九哀求:“乡长开恩啊,饶我一命吧,是我乌龟王八不懂事,是我该打,我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呀!”
又听林所长说:“该打你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抽耳光,狠狠地抽!”
接着便是啪啪的一下接一下的肉击声。于旺田听着,先还是叫好解气,可再听朱景发哭爹喊娘的求饶声,便有些不忍了。唉,打几下就算了吧,可别打残废了,庄稼人的手脚虽说不金贵,可还靠着它一辈子下地做活挣口饭吃呢……
第二天,于旺田在大院里见小警察没事,便凑过去,小心地问:“那朱景发……犯的是啥事?”
小警察冷笑:“还啥事,狗改不了吃屎,赌呗。妈的,这回还叫他跳脚跟我们叫板!俺所长是啥样人,办了几十年案子,苍蝇在眼前过,也辨得出公母,还看不出他是啥东西?所长早派人把他暗中盯上了,他就奉公守法别犯到咱手里呀!”
于旺田试探地问:“这回……他没承认是咋屈的我?”
小警察摇头:“问了,他还是那套话。”
于旺田又问:“也不知……是咋个处罚?”
“赌资没收,四千多块呢,又罚了他五千。这回,哼,他就是再剁去一只手也不顶用了。除了这,还劳动教养六个月,送大辽河入海口筑坝抬海泥去。那地方可不比留你在乡里干几天杂活啦,有他活罪受的!”
到了午后,便见朱景发被带出小黑屋,上了派出所的那辆带警灯的面包车。于旺田站在院子一角远远望去,只见朱景发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青肿得好像那种黑面大馒头,鼻子眼睛都变了模样,一副惨不忍睹的形象。于旺田看开车的警察下车跟林所长低声嘀咕什么话,便急急跑回自己住的地方去,拿了缸子毛巾和肥皂,又拿了两件厚实点儿的衣裤,跑回车门前,对朱景发说:
“随手用的东西,带上吧。天眼看冷了,早早晚晚的,别冻着。”
朱景发先还是发怔,随即就往外推:“你……你留着用吧。”
于旺田说:“水秀天天来,我让她再从家里带。都在屯中住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你就别……那啥啦。”
朱景发脸上露出凄楚感激之色,说:“老旺哥……我人浑,可谁是啥样人,我……心里有数。有些话,就等我回来再说吧。”
警车开走了。于旺田点头叹息,是呀是呀,自古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踩出的,自作自受啊!但愿朱老九良心发现,日后学好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