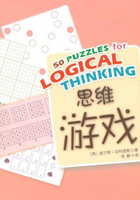却说孟乡长离开于家台后的第二天,乡里就派了一个年轻干部过来,住到了村里,说是检查落实秋收情况。年轻干部姓孙,原是市里一个局的副科长,市里为培养后备干部,就安排到乡镇挂副乡长职务锻炼。于水丰认识他,也只是见他在乡里开会时和书记乡长们坐在一起,只用耳朵不动嘴巴,对他没有多少了解。
安排了孙副乡长在条件好些的农户住下,趁他不在屋子时,于水丰便往其它村打了几个电话,一听都没派乡干部驻村督战秋收,便猜知这是孟乡长怕他小舅子的事鼓包,又不放心自己能否压伏得住,所以才打发来这么个特派员。于水丰心里不舒服,但转念一想,也好,村里迟早要起风波,有这面墙挡着,倒好摆脱责任了。
这天入夜时分,于水丰正和孙副乡长坐在村委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屯里的事,突然有人跑来,说屯东的马大仙马桂芬黄仙附体,又跳起大神儿了。孙副乡长好奇地问,村里还有跳大神儿的呀?于水丰不以为然地说,那个属马的败家娘们儿,时不时地就闹上这么一回,八成又是昨儿夜里老爷们没把她侍候好。孙副乡长来了兴致,说我在城里还从没见过这种事,看看热闹去,行不?于水丰说,想去就去呗,就当你们城里人闲着无聊看耍猴啦。孙副乡长说,你不看看去?于水丰摇头,说饺子吃多了还厌呢,我还看她魔魔障障地耍?
孙副乡长便随村街上往村东跑的人去看新奇。马家院子里已挤了不少人,院门口站着一个黑瘦的爷们儿,看样子是男主人,张扬着两只胳膊,左遮右挡不让人进。可乡民们谁管他,拥一拥搡一搡便进去了,他也无奈何。孙副乡长注意地在黑乎乎的人群中找,没有村干部,绝对没有,一个也没有,便想,这情景既可视为村干部们有觉悟,也可理解为鸡蛋掉进了油罐子,太滑,像这种闹神闹鬼搞迷信的事,管又管不住,不管又不好,谁愿往前凑呢。
马家的屋子里烛火摇曳,香烟缭绕,幽幽暗暗,阴森可怖。北墙上悬着一块杏黄布,影影绰绰不知上面涂画着什么。地心摆了一张八仙桌,上面除了香烛供品,格外抢眼的是一只刚刚宰杀的大芦花公鸡,鲜血淋漓,洒了一地。一个中年妇女赤裸着上身,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胸前的两砣肉布袋般垂挂着,全然不惧羞臊,想必这就是马大仙了。马大仙右手一支桃木剑,左手一支拂尘,那拂尘不过是乡间寻常可见的用马尾做的蝇甩子,正在地心蹦蹦跳跳,舞之蹈之,那胸前肉袋子便跟着一上一下地耸窜。马大仙呜呜哇哇地唱,听得出是在祈祷黄仙老祖,那套词路很玄很怪宛若梵语,在她口中一奔如泻,娴熟流畅。
突然,马大仙匍伏于地,对着北墙哇哇大叫:“哎哟,黑狸怪蹿到我身上了,打呀,打呀,打死它呀!”
两个棒壮的小伙子从旁边闪出来,四只手死死地按住马大仙,问:“在哪儿?在哪儿呢?”
马大仙喊:“背上,就在背上,快打呀,别让它跑了!”
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便抡开四只小簸箕般的大巴掌,风轮般地在马大仙背上抽打出一片噼噼叭叭的山响,眼见那白亮亮的脊背瞬间变红了,又变紫了。屋里院里的喧嚣在那雨打芭蕉般的噼叭声中,霎时便安静下来。
两个棒小伙必是打得手疼受不了了,又抓了两只黄胶鞋,蘸上水,照着那脊背一下紧接一下抽打得更加凶狠无情。那黑紫的脊背上有乌紫的血流下来,再沾到鞋底上,连盆里的水都变红了。
马大仙却仍在硬硬朗朗地喊:“好,好,打得好!痛快!给我往死里打!”
孙副乡长看不下眼了。这岂止是一出平常的闹剧,这是在给人上刑!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妇女,即使有些装神弄鬼的毛病,也不该这么个折磨法,要出人命了!可就在孙副乡长拨开众人想上前制止的时候,没想胳膊早被几只铁钳般的大手牢牢地箍住了,那一双双坚定的眼神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要管!
孙副乡长一时难动手脚,却又顿生惊奇,这马大仙莫非真修炼出了几分道行?不然,平常人哪受得了如此残忍的抽打?棒小伙子也受不了啊!
突然,马大仙腾身而起,轻快矫捷地直向门外冲去,嘴里高喊:“黑狸怪跑了!黑狸怪跑了!堵住它,追呀!”
院子里的人刷地闪出条通道,眼看马大仙旋风般地刮出,身后的人们立刻尾随而去,嗷嗷的呼叫声和纷沓的奔跑声让人想起那打开了盖子的魔瓶。
由数十人裹起的凶猛旋风迅速刮过村街,直向一个有着漂亮的两层小楼和高高院墙的院落扑去了。马大仙抓起一块砖石,砰地砸开窗子,腾身跳落到屋里炕上。黑鸦鸦的人群立刻拥满了楼上楼下。那家的人惊怔怔地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早被拥进的人群淹没了。只听有女人和孩子惊悸的哭喊声,“干什么呀?你们要干什么呀?”
马大仙胡乱挥舞着手中的桃木剑和蝇甩子,做奋勇搏击状,挥击了几下之后,突然一指靠北墙的衣柜和一只高大漂亮的不知哪朝哪代的大蓝花瓷瓶,叫喊:
“黑狸怪钻衣柜里去了!钻瓷瓶里去了!”
砰--
叭--
几条扁担和棍棒立刻将瓷瓶砸得粉碎,大衣柜也被推翻了,衣物被抛扔得满地都是,任人践踏。
孙副乡长急了,站出来企图拦阻,放开嗓子一声声地喊:“住手!住手!”但没人理他。他见院门口站着一个半大姑娘,便支派她:“快去村委会叫于水丰于书记,我是乡里的干部,叫他马上来!”
马大仙又往别的房间冲,她东指西点,人们便一路东砸西摔,毫不痛惜。仅仅三五分钟的飓风大入侵,那户人家的电视机、组合音响便被砸得粉碎,电冰箱也被掀翻在地,被褥衣物被堆扔在院子里,不知还被谁点起了一把火,院子里立刻腾起一股烟雾和焦糊刺鼻的味道。米面粮食被扬撒得如泥沙铺地,所有门窗玻璃都被砸碎,甚至连屋里的火炕和床铺都被蹦踏塌了……
就在马大仙率领众兵勇继续肆无忌惮地疯狂洗劫扫荡的时候,于水丰冲进院门了,身后还跟着几个村干部。于水丰断喝一声:
“给我住手,不许胡闹!”
马大仙却哪里管他支书不支书,嘴里嘶喊:“你是哪路妖魔,竟敢挡我捉拿黑狸怪!吃我一剑!”重重一剑劈下,于水丰的脸颊上顿时腾起一道青紫的楞子。
于水丰气极,恶骂:“混账娘们!还不下手把这妖婆给我捆了!”
几个村干部扑上去,拦腰将大仙抱住。那马大仙不屈不挠挣扎嘶吼:
“看我一剑斩了黑狸怪!我看你还敢不敢使坏做鬼儿!我看你还服不服我黄仙老祖!”
于水丰吩咐:“上茅房舀粪汤子来,给她往嘴里灌,我看她还咋邪性!”
却无人动,屋里和院子里的人突然静了下来,看着事态的发展。这家的女人坐在地上拍腿嚎啕:“这个家算完啦,往后的日子可让我们怎么过呀--”又见院角暗影里站出一个人来,正是乡种子站的何书信。站在于水丰身旁的孙副乡长一怔,顿时似乎一切都明白了。
何书信哭丧着脸走到于水丰跟前,嘟囔说:“于书记,你可都看到了,到时候你可得站出来给我说句话呀。”
于水丰冷冷一哼:“我看到了什么?我眼瞎,可心不瞎,我就知道别把人惹急眼了,急眼的人能把没好下水的东西活撕巴了!”
那何书信又蹲下了身子,脑袋垂在胯裆间,唉声叹气再说不出一句话。
马大仙挣扎跳闹了一阵,身子也颓萎下来,躺在地上翻白眼,吐白沫,呻呻吟吟瘫瘫软软,再不见了半点仙灵之气。
于水丰对马大仙的男人横了一眼,斥道:“不赶快弄回家去,还愣着干什么?等着开席呀?”转身又吩咐其他村干部:“留下几个人,帮收拾收拾。这么多人眼看着一个魔障胡闹,太不像话了!”
当地话,魔障就是精神病的意思。一声“魔障”,定性了。于水丰好定性,也善定性。说完,他气哼哼地大步走出院子。人们不说什么,互使着眼色,一个个很快也都离去了。
当天夜里,孙副乡长用电话把于家台入夜时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向乡长孟昭德做了汇报。孟昭德问,于水丰当时在没在场?他是怎么个态度?孙副乡长如实讲了,多多少少也加进些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说事发时于水丰可能确不知,但事情闹起来后,他一打眼就看明白了醋为啥酸酱为啥咸,制止的还算及时果断,但在处理上,明显有顺水推舟、法不责众的味道。电话里,孟昭德好半天没吭声,最后说:
“你明天吃过早饭,就回乡里来吧。那边的事,不用管了。”
孙副乡长问:“是不是再等两天?看眼下村民们的情绪,极有可能还会去乡里县里闹。”
孟昭德叹口气,说:“不会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乡下人就认这个理儿,他们已经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