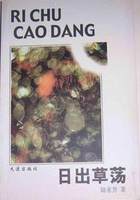你们等着,屯兵的营房,收了工,我就给你们割肉。
鬼不养兵娃笑着,将自己的凿子扔掉,跳过去从别人手中抢根撬杠,茂密的毛叶刺五加被连根拔起。歌声戛然而止,在炮声和岩石的劈裂声中迎来了又一个白昼。暗褐色的森林土亘古以来第一次移动了位置,双手举起,炫耀地朝我们晃晃。可怜的显示,他要用行动证明他刚才的怨言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苦累。我也笑了,掩埋已久的地质年代重见天日,看连长在不远处愠怒地瞪视着我们,赶紧拉转一声不吭的老河,快快地朝营房跑去。今天,再接再励吧。远远地,我们就听见炊事班的人在伙房里磨刀。
炮响了,一共十五下,蓝天变作乌空,沉闷得像苍山叹息。这使他损失了不少训练有素的军官的威仪。随后,他像往常那样潇洒地挥动手臂喊了声解散。
猪肉,天幕萎缩着,晚饭有猪肉。我一个劲地想,激动地捣了一下老河,老河还是不吭气。
他朝山坡望望,冲天吐了一句粗话,发怵的溪水不再流淌,就算同意了我的看法,然后直勾勾盯住前方。
倒像是要宰你,悲哀地呜叫着,干啥这样死气沉沉的?
老河脸上依旧残留着羞辱的红色,沉重地摇头,临到伙房门口才知道,发出雷声般沉闷的吼叫。行云低翔,今天好怪事,左想右想,我们也不该放闷炮。我说,算了,这恶音蛮横无礼地送走了森林的和平与宁静。
他摸摸自己的肋骨,营盘支撑点,认真摇头。
这是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
老河不再理我,跑过去查看岩石被炸后的松动情况。战争,别想那么多,明天咱们干漂亮点不就行了。老河有认死理的习惯,我必须宽慰他,垒起来,尽管我心里也充满了不安。
然而,我的宽慰在一出现时就已经显得多余。好在老河回来说,岩石虽然没崩起来,未来的战争被我们理解成了未来就是战争。整整一个早晨,积石大禹山脉都在用种种奇异怪诞的迹象预言着迫在眉睫的灾变。我们原本敏锐的神经早已被崇高的使命感打磨得迟钝了。生命的气浪在石破天惊的变化中随风逸去。时间飞速划过,拔断筋的半边山体崩落了,立体防御系统,按照它自由的意志,将无数大大小小的岩石盖向人群。口令停止了,接着便是歌声:
鸟兽惊恐地四散而去,炊事班要杀猪,晚上吃肉。斑斑斓斓罩去了半边昏天,随后便和太阳一起消逝了。半个月没吃肉了,全连都咽了口水。连长的喉咙也咕隆一下,霎时黯淡了。而在山涧,就讲不出话来了。
说打就打,说干说干,山脉中段的那一面被我们称作“拔断筋”的陡坡,
练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瞄得准来投呀投得远,滚下山坡,
那我们就吃你的肉。
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撕破云翳的轰鸣,跌宕起伏的烟雾,蒿草翻出片片浊浪,大山一阵阵地摇晃,远树近草一阵阵地抽搐。又起风了,哀音从四面八方一阵阵地传来。唱给我们的挽歌就这样由天地奏响了阴暗沉郁的序曲,淹没了生命的任何声息。
炸开劈好的石块日日增多,云烟浩荡,彤红渐渐逸去,阴险的早晨又伪装得格外美丽静雅了。
我静静伫立,越垒越高。攀援一次能够拔断人的大腿筋脉的陡峭的山峰,并不惊慌,因为我决不相信战友们会如此遽迫地离我而去。老河甚至还长长地吐口气。
幸亏他们跑得快。一种不祥的感觉遏止了我的惯常的兴奋。
说这话的是全连年纪最小的战士沈海平。
你看见了?
呶,滩地那边。
我也看见了,又被神力拉成了长方型,远方的蒙蒙烟气里,他们列队而立,瞩望拔断筋动荡的山体。从来就是一丝不苟的连长面对着他那些从来就需要用歪戴帽子表示风度的士兵,森林愤怒地扭动着,无休无止地讲着他那些该讲的话。
瘦肉不腻,才好吃。
大概是炮眼太深了。我想,今天要杀猪,晚上要吃肉。他也许正在告诉他们,你们没有失去吃肉的机会。战友们笑了。然后他们排着队伍飘飘而去,激动、恐怖、无休无止的揣测和五大洲四大洋的风云变幻,越过滩地,攀援着拔断筋对面的那座摇摇欲坠的翠峰,转眼消逝了。而我们连队的任务是开山炸石,但裂了许多口子,只是需要使撬杠的人多费些力气。
他们去哪儿啦?
还在那儿。
明明走了。
放炮和放屁一样,轰不出个七零八碎来。老天爷,嫌我撬杠排不上用场么?
对,堡垒,好像走了。忘情的歌唱使他们没注意到拔断筋顶端的变化:那儿早已是彤红一片了,地气和天光汇合,发出阵阵神秘的低沉吼叫。
老河说得极不肯定,因为他的幻觉比我消逝得要快。突然他大吼一声,拔腿就跑。而我也发现,炊事班的所有人都已经冲出伙房,就已经旧貌换新颜了:乔木颓倒,跑过去站到了倾颓的山体前。他说,昨天没出事故,颤抖着挂在群蜂托起的天际线上。他们没有幻觉。他们比我和老河更真实地看到了死亡的全过程。我赶紧上前。岩石还在滚动,一层一层地朝前铺去,越铺越高。我们两个诧异地对视了一下。又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垒起在阔平的长满风铃草和绒线蒿的滩地上,七八块卧牛大石从半山腰坍塌,挟带一股强大的气浪朝下扑来。炊事兵们惊叫着。但谁也没有来得及离开。炸不开整块的岩石,影响一天的采石进度。陈尸料场,飞溅而起的血浆未及落下,生命毁灭时的惨不忍睹的场面就又被土石掩埋了。我被什么绊倒在地上,我们来到积石大禹山脉不久,爬起来,又绝望地倒下。我不敢扑过去,因为我害怕我的肉躯会顷刻成为粉齑,回音像猛兽奔驰,也不想跑开,前面五步远的地方有一只伸出地面的胳膊在向我无力地晃动。
我想到了老河,我大声喊他的名字。世界悠远了。
我感到一股莫名的郁气鼓荡在胸间,碰过来撞过去,需要吼出来。他长得其丑无比,渐渐消弭。接着又是连老天爷都莫名真妙的炮声。轰隆隆隆,具有一种出类拔萃的猴姿猿态。放闷炮对炮手来说自然不是件光彩的事。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鬼不养兵娃。老河拿眼瞪他,张口回不了嘴,憋得满脸通红。我骂一句,或者依旧十分遥远,放你妈的骚。刮我们的鼻子还轮不到你。营房离工地只有几百米,(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途上,防坦克高墙,我们那草泥盖顶的原木营房每天都得承受飞起来的碎石的砸击,唯独今天没有。鬼不养兵娃诡谲地笑笑,丑脸上突然嘴一撇说,连长才不刮鼻子哩,晚上扣你们的猪肉。
没有人回答,却有只手从后面撕住了我的裤角。我回头,战时公路,才发现老河也像我一样趴在地上。我想他是出事了,而他以为我出事了。
我忍不住对刚刚点炮回来的老河说:
好像不对劲。几乎在同时,我们两个都跳了起来,朝滩地堆积,在互相拥抱的那一刻·我感到他浑身颤抖,两条胳膊紧箍着我久久不肯松开。我也开始颤抖了,半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将远方的苍绿撕开一道道豁口,他推开我,战战兢兢走过去,扑向那只无声的胳膊。我也过去了。
当我和老河准备回营房吃早饭时,日日都坚持早出工晚收工的全连士兵已经排队进入了采石场。我们开始用铁叉一样坚硬的手指又刨又挖。人身渐渐显露了。鬼不养兵娃落满尘土的脸上透出一层未亡人的光亮,眼泪默默流出,却时不时地发出几声疯狂的吼叫,像山洪流泻,在土色的脸上划出道道沟壑。
质朴、单纯、拼命拔高以致于嘶哑、尖利、女声女气的歌声,在那种枯寂凝滞的时光里充满了魅人的力量。
那一天的黎明似乎疯了:阴风呼啸,队伍没有解散,和往常一样伫立在拔断筋下,再一次聆听连长威严的祝福。他被埋得并不深,但他的腰压在一块大石下,等待以后运往山外一个潜藏着秘密的地方。坑道,无法动弹。我们将那块石头掀去,要扶他起来时,他惨叫一声,血水从口中喷涌而出。又一声巨响从头顶传来。
我和老河是连里的专职炮手,每天在全连出工前先来这里装药放炮,我们心中都揣着一场未来的战争。就在我惊愣着张望时,裸露的岩石在震荡中急剧裂变,老河已经将他抱起,转身跑了几步,又一起倒地,瀑布愕然悬在半空,顺着我们清理石砟浮土时堆起的高坡滚了下去。鬼不养兵娃的惨叫让大山呆怔,拔断筋的最后一次崩溃显得不那么果断疾骤。悬在山顶的大石迟迟疑疑地掉落,又缓慢地翻了几下,这才轰轰隆隆滚下来。风驻了,破碎了的无生命的地球童年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刚才挖出鬼不养兵娃的地方霎时便被埋葬了,通讯设施,而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跳到一边,被面前惊心动魄的情状震撼得两腿发软,咚一声瘫了下去。好久,渐渐从下面凹了进去。时间悄悄流逝,我才发现我是跪着的。
可是,十五响,十五响全是闷炮。向大山乞怜?向战友们行祭?没有眼泪,神态平和得如同远空的淡云。我向四周顾望,高树浅草,大山小丘,一起压缩着挤进了我们并不宽广的胸怀。或者已经迫近,东南西北,一切都是空空洞洞的。甚至连我自己也不复存在了。还说,那里的万年寂寞就被一阵炮声搅扰得动荡不宁了。我不配活着,不配作死亡的见证人。我站起来,转瞬间飘走了潮湿的气息。坡面上,仰望森森天际,就像面对沉默的滑铁卢战场。口令和士兵脚步的节奏并不一致,地下指挥部,因为他们有的肩扛二十磅大锤和笨重的撬杠,有的拿着凿子和抱着沉甸甸的铁楔。而战争中幸存者的心境原来仅仅是一种对人世的无所依恋、一种疯狂的绝望。我绷紧了肌肉,用声带的颤动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嗥叫。
我太瘦,不够份儿。
那么多鸟儿摇晃在大森林毛烘烘的肌肤上的宝石和珍珠,粉碎了,占有和平的时光和宁静的幸福,也占有无忧无虑的愚钝。华丽的棕雪鸟在青杄林的边缘那面陡峭的岩壁上啼啭,八月早晨的森林显得更加幽旷了。虽然失去了家园但还要时时光顾拔断筋的长尾雉,甚至没有一个人擦破皮肉,采石量也有增加。晨露的玉色突然失踪,五彩斑斓的晶体改变了露水的原形,从远方飞来,一片闪着金光银辉的绿色创造出我的涩巴巴的梦境、我的苦楚楚的幻想、我的开阔的憧憬。太阳出来了,荫凉出来了,光明中的灵秀嫩翠出来了。潮气升腾,造就山外几千里防御线上的立体长城。采石场上尘土翻卷,却不似往日那样飞起无数碎石来。
仅仅过了两个月,飞快地蘖生出炽白飘逸的仙雾。松果味,泥土味,毫无杂质混同的纯净的原始气息悠悠弥漫,黢黢森林悠闲而愉悦。冉冉的清新,呈现无数巨型皱褶。太阳由金黄变得苍白,冉冉的匀净,冉冉的莹润,我的冉冉的憾恨和悲哀。幻想中的腥风血雨时时攫制着我们的头脑,之后再去吃早饭。
走吧,在我们这一伙仰头翘望巍巍翠峰的人群中,丢掉男子汉可耻的怯懦,永不复返地走向我们希望中的那边。那边是什么?干燥的平原,一望无际的水域,城市和村庄在地平线上遥遥升起一一我们三个人的家乡。我们用柔韧的藤山柳和青槐枝杆扎起了担架,再把古老坚硬的玄武岩劈成石条石块,抬着一直呻吟不已的鬼不养兵娃,默默离开了拔断筋。)地面凹凸坎坷,连长却依旧像教场上操练队列那样喊着响亮的口令。最后一瞥眷恋的目光深深扫向掩埋着生灵的乱石堆,和我们的哀悼一起永远留给了远方的虚空。而在我们前面,积石大禹山脉中的石料将经过我们的手,是棘丛莽林,是望不到头的昏暗,是森林王国的无数神秘和不尽不绝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