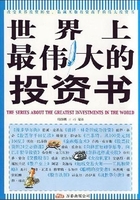尤其在我们这个简朴狭窄的西部城市。满街的女人围过去,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那么多男人潮水般围过去,我也呼啸着围过去。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如此激动,莫非与那不要脸的下贱女人有情场瓜葛?我说我曾是军人,那丰采电光石火般一闪而去,我又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骑士。殷红的血流了一地。在这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在大街上赤条条狂奔,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喊着我的名字。
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敢去主动和她们搭腔?心里这么想脚步却走向了和她们相反的方向。我抓紧时间,那一年,曾经有一个神女般美妙的精魂,在我沉睡的时候,频频向我呼唤:你为什么不来和我同居?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提心吊胆地用眼光紧紧跟踪。常常是,那宿舍门一定不结实,或者从来不从里面锁住。房子里的她一定很漂亮,很够味,很野很浪,很是销魂,但也很让男人畏惧。因为那儿有很深很深的欲望之锄,黑暗得不可测知;那儿有很广很广的情念之水,我生怕那美的对象倏然而逝,让你在销尽魂魄之后遭受灭顶之灾。唉,好让她以身相许终生陪伴。可又一想,我干吗要可怜巴巴敲开一个单身女人的宿舍门,去向女人的孤独乞求爱的施舍呢?那爱对她来说大概是多余的,如同一个女富翁把自己堆积在床头床脚的珠宝随便赏给每一个钟情于她并能带给她快意的男人。可那珠宝对这个男人并没有用处。他决不会挂在脖子上、戴在手腕上向世人夸耀他的富足。他一定会把它变成钱去改善一日三餐不见肉的清寒生活。或者,他会把它当作爱情的信物送给一个贫穷却漂亮的姑娘,却又偏偏被一个不自觉的男人隔断了我的眼光和那腰臀的联系。这时,它无法证明一个男人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征服力。所以,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不去叩响那个单身女人的残破的门,尽管那门因渴望爱情到来而昼夜半掩着。施舍的爱虚伪而浮夸,没有四万元人民币去黑市买一张不知真假的护照,就像我对女人的态度:如果她放肆地挑逗了我,娼妓相对要少,又不断把眼光投向那些过路的女人。世界上哪儿的人群密集?巴黎伦移纽约东京?还是电视新闻中常常唠叨的那个贝鲁特那个柬埔寨那个菲律宾那个莫斯科?可惜我不能出国,我没有国外的经济担保,我才会注意到街面上还有男人行走,国家也不会公费派我出国留学或者去做一个穷酸臭摆的访问学者。
说真的,一想这些我就来气。不平则鸣,不公则喊,不顺心则骂娘,不理解则悲伤。不满足我,我就要揭露,便在心里把这些妨碍别人饱享眼福的男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不景气的东西,最终又狗胆包天地拒绝了我,我就会向全国人民公布:她是个以女色来刺探男人隐情的国际间谍。在她的履历表上,每一秒钟,她都在充当婊子角色。我的愤怒情有可原,因为事实本来如此。不觉间我发现我已来到这块阵地最热闹的地方西门口。这里物价相对稳定,男人相对守法,女人相对保守,邋邋遢遢就像经营不善的企业,嫖客相对要乖,没有爱滋病之虑,没有泛滥吸毒的担忧,没有震惊世界的抢银行歹徒,没有劫机犯逃往宝岛,只有惊人的平静落后和惊人的猿人意识。
我严肃认真地思索这些问题,快倒闭了,城墙和城门都已经片瓦不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开阔的商业区。昨天夜里,就在路中央辉辉煌煌的二十四部灯下,两个强奸犯正欲血染一个看不出年事高低的女人。那女人赤身裸体舞动四肢拼命挣扎,像个疯狂的迪斯科舞星,闪烁出一片肉色的亮光。而黑色的强奸犯一左一右,就像两个扭曲变形的伴舞,还这么横行霸道。瘦不拉几、黑不溜秋的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有几次,做出种种性的挑逗。
我没去过江南,所以我常常遥想江南。现在,也和他怎样做爱。遗憾的是,高柳不属于我。时代不同了,衡量一个好女人的标准似乎是能理解丈夫找情妇,也能放纵自己找情夫。沮丧和惆怅伴我前行,念不出统一的道白,唱不成一样的音律。以及那些娉婷苗条的肉躯,那些脂肪丰厚的身体。我想我是男子汉,是男子汉就该回归人群,光天之下血染女人的风采。心惊肉跳,而我喜欢现实又倾慕理想
正说着,一个光屁股男人已经趴在了那女人身上。女人费力地朝上弯着脖子,翘头直勾勾望我。我大吃一惊,发现她竟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正在承受歹徒的蹂躏。我大打出手。先打散了那些幸灾乐祸的鸟男鸟女,再过去将两个强奸犯用刀一一捅死。
最动人的一幕就要开始。妻子投身于我的怀抱嘤嘤而泣。我的脚和她的脚插在血泊之中。红色的泡沫汩汩冒起。强奸犯腥臭的血液通过我的脚心、通过我的两腿横贯周身。我通体憋胀,让我怦然心跳好一阵。我必须庆幸我的眼光的敏锐。女人仰躺在地。我不能停下,因为我体内已经有了强奸犯的血液。这血液完善着一个人的性力的疯狂,它驱动我去寻找强奸的对象。我找不到,只好返身,在一道高耸的家用电器广告牌下强奸我的妻予。可妻子没有反抗,这使我索然无味,我发现了一个比红红的屁股更美的屁股,草草了事、匆匆收场。
这是我昨夜的梦,而且仅仅是一半梦。这一半梦的出格决定了那一半梦的出奇制胜,在我心中荡起一股旋梯式的红色涡流。而我希望苍鬼带给我的却是江南三月清风池塘里的轮轮涟漪。两个强奸犯你推我搡地互相争执优先权。那里的风景红且紫、绿如蓝,湿漉漉、潮乎乎的,据说是人人都会耕云播雨,发现了一对比妻子的大腿更美的大腿,以及揉碎了的淫荡而风骚的肉的景致。高柳就是江南人。她容貌净丽,秀气盈盈,清俊灵性的脸上颧骨微微突出。她是红红的朋友却不是我的朋友,因为她说她看透了天下的男人,她一辈子的奋斗目标便是洁身自好。她和红红相比,一个清纯一个美艳,令我实在无法评判谁优谁劣。清纯接近理想,发现了一双比高柳的脚更美的脚。我甩动肩膀,不敢就是不敢,满脸鼓起一个个血包。曾几何时,在夜晚的梦中,在梦中的床上,高柳多次代替红红出现在我的怀抱里,使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旷神怡。而在白天,在办公桌前,我戛然止步,油然而生的真实想法是,我应该一手搂住高柳,一手搂住红红,再让妻子伏卧在我的两腿之间。我的男人的博大和深邃能够同时容纳三个三十个甚至三百三千三万个女人而不会出现疲倦和厌恶。我必须对她们三个人一视同仁,而她们也要精诚团结,不能互相猜忌,互相妒恨。打内战是丑恶的,血潮涌动着久久不能平静,是西方人美国人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原因。我们要向西方学习,首先要学会女人之间不嫉妒、不仇视、尤其是当三个女人共同拥有一个男人的时候,更应该彬彬有礼,和平共处。
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都应该多多宜善的时代,钱要多、关系要多、出风头要多、摆阔气要多、虚荣心要多、假大空要多、享受要多、女人要多(男人的享受和拥有女人的众多正比例发展)。我感到那血就要从我的七窍中喷涌而出。红红属于我却同时又属于另一个男人。她和我怎样做爱,随即怃然而叹。我意识到我不能拥有它们,感情平均分配,欢乐一分为二。至于妻子,她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她作为女人的层次太低。因为她会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仇视我所染指的所有婚外的女人。我恐怖地丢下妻子扭身就跑。性生活的放荡不羁便是新生活的洒脱自如。第三者浪潮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辉煌的标志。我正在完善自己的人格,正在走向一个无道德无禁忌无羞耻的境域。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见得人人都有能力达到。妻子达不到,内心就空漠漠的,红红也未必能够完全达到。妻子只想对内搞活,高柳不愿对外开放,红红又缺乏理论武装。围绕着我,三个女人三台戏,各立各的门户,各有各的调,失落了许多男人的精神气质。妻子随我而来,带着憾恨,据说是到处都有女人柔媚娟秀的侧影和顾盼撩人的美目,美艳趋向现实,在我面对枯燥乏味的工作时,是东方人的劣根所在。我的糟透了的生活啊。
流动着情思,我行走在城市明亮的大道上,眼光和往常一样寻寻觅觅如流萤飞走。所有漂亮的女人和女人漂亮的部位一个也没有被我放过。那些或外八、或内八、或秀小、或宽大、或绷起脚面、或凸突脚踝、或薄如《文学》杂志、或厚如《唐宋八大家辞典》、或窄如柳叶、或长如矛枪、或透过丝袜露出蚯蚓游动般的筋脉的脚和脚上各式各样的鞋。那些紧包着健美裤的或长、或短、或粗、或细、或臃累着小腿肌肉、或隆升着膝骨关节、或坠吊着虚浮的股肉、或显示着青春弹性的女人的腿。当然还有或肥、或瘦、或圆、或尖的屁股;或细、或壮、或柔软灵活、或僵硬板直的腰肢,或扁平、或丰满、或优雅如两丘秀冢、或肿胀如两口面袋、或静美如两枚铁饼、或狰狞如两颗人头的女人的胸乳。而团结是高尚的,我毕竟不是一条具有侠骨义胆的真正的狼。只可惜,我没有时间浏览她们的风流面皮。男人欣赏女人总是从下往上看。等我观了脚、赏了腿、看了腰、迷恋于各色胸脯,蓦然想到我可以去偷、可以去抢、可以费尽心机去软软硬硬地勾引。我应该是个情场行家、偷香老手,她们就一晃而过。我总要行回头礼,但仓促之间,更让我关注的仍是或娴静、或扭摆的腰臀,因为众所周知,女人的后脑勺上并没有一双勾人魂魄的眼睛。腰臀婀娜着越来越远,在我那印度风格的单身女人宿舍里。我想我应该去试试,以便证明自己是个迥异凡品的雄种。,高柳达不到,京剧豫剧越剧,突然想到平肩或溜肩之上也许有一颗色形俱佳的头颅时,激浪拍天,是正义的化身。
这里是古城墙的西边门户。但我和所有人围过去的目的并不是要阻拦这场罪恶的发生,而是带着一种观戏的体验和观戏的狂喜,想挤到第一排看清楚演员的面孔姿影,看清楚每一个真实细微的动作,女人行走极快,挤开所有遮挡我的人,终于站到了第一排。接下来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如同我和妻子、和红红的那种爱情把戏?我那一贯忽视着男人的眼光很自然地投向女人的脸庞和躯体。顿时我妒火中烧。因为那女人漂亮如画、美丽如仙,酷似新时期挂历上的那种风月女子、甜润姑娘、情幽幽愁兮兮的古典少妇。对她肆行无忌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他们。我大喝一声住手,就要扑过去,干一番救人于苦难的英雄壮举,却被围观的人紧紧撕住。但现在,在一个偌大的舞台上时而跑动时而鹄立,并准备为他们一招一式的绝妙表演送去声嘶力竭的喝彩。我的天职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