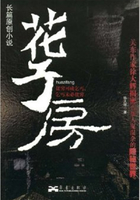它的旧主人在它刚飞上天不久就用类似的招数逮住它,驯成了一只猎鹰。相处几年中,它多次反抗过那人,一直到这次最后的叛逃。那次是个多么激动异常的出猎!主人肩上架着它,骑一匹快马,奔驰在山野上追逐猎物。它兴奋极了,逮了一只又一只野兔山鸡。只要主人一轰跑野物,随着他的一个手势一声口哨,它就如闪电般地飞扑过去抓住猎物。当然它还没吃到嘴里主人就赶到,把猎物从它爪下收过去。它知道这是打猎的规矩,只有到了晚上,主人才把最后逮到的野兔或山鸡扔给它吃。中间不让它吃是为了刺激它更猛烈地进攻猎物。可那天它一直等不到那个血淋淋进餐的时刻,天已经黑了,主人仍贪婪地追逐着野物,一次又一次地从它嘴里夺走猎物,并且拼命地吹着口哨打着手势让它干活。它不满意了,主人的贪心和一天没吃到肉的空肚肠使它暴躁起来。它实在疲倦了,当主人抢下那只它非常想吃的肥兔时,它被激怒了。它再也没有回到主人的肩上。围猎行上称这种现象叫做“厌主”。主人慌了,骑着马追逐它,并发出一声声的悔恨自责的召唤,把那只夺走的肥兔给它仍过来。但它不屑于吃了。它飞出一段落下来,也不完全飞走,等主人哀叫着靠近过来时,它又飞走了,不让他逮住它。它就这样停停飞飞、飞飞停停地跟主人追逐着。这时,从森林里突然飞出一只漂亮的野雄鹰,一声尖利的唿哨,闪电般向它飞扑过来。登时勾起了它雌性的欲望,忘却了一声声呼唤它回归的主人,一阵拍翅高飞,追随着那只向它调情的雄性苍鹰升入了高空。
那可真是个充满激情的“私奔”。
它们甜甜蜜蜜地一起生活了几天。一起进攻野兔赤狐,一起飞冲云层雾障,一起露宿悬崖古树。然而,凡事情终归有个结束。它们很快又厌倦了。它无法忍受跟同类长期厮混的方式,它们是个独立性强的猛禽,把一方拴在另一方身上的方式,太古老了。它们都要追求新的天地,新的世界,新的刺激。经一场激战之后,它跟它终于分道扬镳,趁狂热的激情,它一头闯进了这一带沙漠世界。
结果,它又误入了这个矮小老人的圈套。它觉得这个世界哪儿都被这两条腿的繁殖力极强的人类占领了。连这荒漠里也设有他们的陷阱。
经历了六七天的摇篮驯化,主人给它松绑了,只是在一只腿上还拴着一根长绳。挂在脖子下的小巧玲珑的铃铛,时时发出悦耳的声响。
有一天主人右手臂上套上一只长长的皮筒,让它落在他微弯起的手腕上。它熟悉主人们的这个用意。它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训练:捕猎。
二十米外,一个女人把一只活鸡抛到半空中。
“啄!”主人一声猛喝,手腕往前一推。
登时,它身上的本能恢复了,眼睛闪射出凶狠锐利的光束,倏地向前飞扑,还没等那只鸡落地,它的铁爪就抓住了它。它刚要撕开鸡肉吸吮它心血时,主人夺走了那只鸡。接着又往上抛鸡,它更为迅疾猛烈地扑过去。
“真是一只聪明又凶猛的鹰,捕猎的本事恢复得很快!”主人欢快地喊叫,把那只鸡扔给它吃了。
它天天如此训练。后来腿上的拴绳也撤了,它已经淡漠了逃离的欲念,熟悉和习惯了老人的爱抚。它完全被这位新主人的魔力征服了。
它等待着新主人带它去出猎。可奇怪的是,主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他跟那个女主人一起似乎等待着什么。
悠闲中它有些烦躁。它最不习惯这种缺少激情的平安日子。
伊琳把水和干粮装在包里,正要蹑手蹑脚走出屋,小明明还是醒了。
“妈,带我去,带我去!”
“明明,留在家里跟郑爷爷一起玩!”她哄着儿子。
“不嘛,你答应好今天带我去的!郑爷爷老坐在坨顶向东看,不理我,也不让碰猎鹰。”小明明抗议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光着脚就下地。
她没办法,只好迅速给儿子穿好衣裤,把一顶小草帽戴在他头上。然后她拿起老郑头的那杆砂枪,领着儿子走出屋子。她踏查方圆几十里的苦沙坨子已经好几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要走完苦沙坨和大漠接壤地段的最后一段路程。她干得很认真,决心对这座三面环沙的沙海孤岛苦沙坨子来个全面踏查,从它的地理位置、土质、植物密度和生长情况都进行一次普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萌动了这个念头。想推翻那位“博士”的权威性结论?还是只想完成一下场部领导交给她的任务?或者什么也不为,只是想干点什么,以摆脱生活的沉寂。
“妈妈,你看,郑爷爷又坐在南坨顶上!”
果然,老人抱膝坐在高耸的南坨子顶上,那只猎鹰落在他肩头上。老人嘴里咬着烟袋,默默地凝视着东方的地平线。她知道老人是昨天傍晚时就坐在那儿的,不知是夜里没有回来还是今早重又上去坐的。瞧着他那一动不动的神态,会以为是一尊黑岩石雕像。
“妈妈,郑爷爷还在等他的儿子吗?”
“是的。”
“他儿子在哪儿?”
“在东方的一座城市。”
“是不是又爱上了森林中的美丽姑娘?”小明明突然问。
“哦?哦,是,大概爱上了森林中的姑娘。不过,郑爷爷说儿子会回来看他的。”
“回来?会不会是回来取他爸爸的心?”小明明又冒出一句。
“你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呀!”她赶紧制止儿子。同时,一种莫名的伤感情绪袭上她的心头。她抓住儿子的手,加快了脚步。
她经过南坨子西侧,进入最后路程的踏查。老郑头发现了她,挥了挥手,走下坨子来。
“郑叔叔,有什么事吗?”她迎上去问。
“我今天去场部,下午回来。你去转坨子小心着点,早点回家。”
她知道老人这是去场部看有没有儿子的信。儿子答应回来的日期早已过了。
老人肩上架着鹰,沿着坨子里的小路,向东走去了,很快消失在草坨和沙丘后边。
她也赶路了。惦记着老人的事,心里有些发沉,觉得老人把挽救苦沙坨的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早已忘却故乡的儿子身上,是不是明智和幼稚。即便是他儿子说服场领导继续保留这个经林所,可他能有回天之力挡住大漠的东移吗?她并不想伤害老人,可经这几天的踏查,她正在得出一个可怕的完全违背她心愿的结论:那位“博士”的判决也许是对的!
西边大漠的推进是惊人的,它已经把阻挡它东进的苦沙坨子地带切割成很多小块,并用它的漫漫黄沙包围着它们,用不了多久,这些小块就完全被吞掉。老郑头居住的经林所这部分坨子情势稍稍好些,大多坨子上长出了青草和灌木丛,如黄柳、胡枝子、金鸡叶等,它们的固沙封坨的能力是无以伦比的。这归功于老郑头几十年苦心经营。然而,尽管这样,面对大漠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从莽古斯大漠近几十年向东推进的速度和面积判断,苦沙坨子一带将被沙漠淹没,这一点也许是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
她为自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感到不安,觉得对不起郑叔叔。同时,她也隐隐感到自己忽略了一个什么因素。她想找到这个因素。因为她心中一直有一个想推翻那位“博士”的结论的强烈欲望。
清晨的凉爽还没有退尽,趁天热之前她要完成今天的计划。她从南坨子的西侧插过去,由大漠和坨子接壤处往北赶。这一带分布最普遍的是新月形沙丘,这是在单一的从西北吹来的主风下,或在两个大小不同、风向相反的风力下逐步形成的沙丘。这种沙丘的平面图很像是一个新月,沙丘两翼之间的交角有的大、有的小,随着风力大小演变着。迎风坡缓而长,背风坡陡而短,高度大约十五米左右。她知道这种沙丘移动速度较快,危害较大。不过,她越往北走,靠近老郑头的实验地一带时,这种新月形沙丘逐渐少了,出现了很多灌丛沙丘。这是属于那种固定和半固定的沙丘,流沙受到植物群丛阻碍后堆积而成的。随着植物的生长,流沙堆积的增加,灌丛沙丘也不断增高增大。这种沙丘多是由黄柳沙包、白刺沙包、锦鸡儿沙包组成。
发现了这片灌丛沙包,她为之一震,心中不免兴奋起来。她知道,这里多数沙包上的灌木都是经老郑头的手培植起来的。肆虐的风沙,在这一座座由灌木武装起来的沙包面前退缩了,失去威力了,明显地回避着这一带,随风向南转移,于是形成了她刚才经过的那片新月形沙丘。其实,这些灌丛沙包的原状也是新月形。她隐隐感到自己正在发现着一个什么东西。
已近中午,太阳有些热了。明明玩累后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她只好背着他爬上一座有树荫的坨子顶上歇息。携带着这么一个幼儿在荒漠莽坨上搞踏查,在过去她早骂自己发疯了。她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也显得消瘦,只是那双忧郁的眼睛很兴奋地闪动着,望着连绵起伏的大漠,她心胸也开阔了许多。从西边的大漠吹来阵阵灼人的热浪。被强烈日光照射的沙漠变得刺目耀眼。大肚子蝈蝈在草丛里拼命鸣唱着,此起彼伏,相互呼应,太阳晒得越猛,它们脊背上的透明蝉翼发出的声响越响亮,越富有节奏。大自然赋予万物各种本能,万物又以此组成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大自然。
喝了水吃了午饭,小儿子又在树荫下睡了一觉。她觉得对不起儿子,不该带他来这大漠里受罪,过几天还是送回场部的老母亲那儿好,这里太苦了。
下晌落日前,她踏查完了最后一段路程,当背着儿子往回返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从路边蹿出一只野兔,小明明高兴了,从后边追出了几百米远。她刚要喊住,一件使她魂飞魄散的事情发生了。由路的斜岔跑出来一条灰色的比狗粗大的野兽。长尾巴夹在后腿中间,伸出通红的舌头,眼睛绿莹莹的,直朝前边的明明扑过去。
“狼!”她失声惊叫,浑身发凉,“明明,快跑!后边有狼!”她发疯地大叫着向儿子跑过去。一跑才发现手里还有一杆砂枪,她立刻举起来,可儿予和狼正好在一条线上,想朝天开枪又勾不动扳机,原来她根本没有装火药和铁丸。她只是为了壮胆才带枪的,没想到真要用时却不知道如何装火药。
那条狼听见后边的喊声,停下来回头瞅一眼,这是一条饿红眼的很有经验的老狼,它很快判断出后边这人并非猎人,于是又转过身扑向前边的小孩儿。
明明发现了狼吓傻了。不知道跑,也不知道喊叫,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愈来愈逼近自己的野兽。
“救命呵!救救我的儿子!来人呵!”她向四周呼救,旷野沉默着。她不顾一切朝狼跑去,可软软的流沙地上跑不快,赶不上前边四腿腾空的恶狼。
明明惊醒了,哭喊起来,拔腿就向右侧跑。他想绕过狼跑到妈妈这边来。可这一跑更缩短了他跟狼的距离。大灰狼从二十米远处飞身跃起,扑向明明。她惊骇得喊不出声来。与此同时,从她头顶上闪过一个黑影,闪电般迅疾,还没等老狼扑下来,这只黑影在狼的前额上狠狠抓了一把。狼一声嚎叫,摔落在地上,立刻又前身伸屈着趴在地上,张着血红的嘴,呲着尖利的牙齿,凶狠地向上寻视着黑影的再次进攻。
伊琳这才看清那是郑叔叔的猎鹰。
恶狼只好放弃到嘴边的童孩,等候猎鹰再次扑下来。猎鹰在狼的上空低低飞旋,狼紧张地随着鹰原地转圈。
“啄!”从坨顶上传出一声猛喝。刹时,猎鹰又一个闪电般的俯冲,正好在转圈转得晕头转向的狼的前额和眼睛中间猛抓了一把,还没等老狼张开嘴,鹰又飞速地上冲到半空中,气得老狼无可奈何地干嚎叫。这次老狼又吃亏了,一只眼睛连皮一起全被撕下来,喷出的黑血染红了它尖长的嘴脸。
老狼不停地嚎叫着,原地打着转,血渐渐模糊了狼的眼睛,看不清头上盘旋的猎鹰的影子。于是老狼一声长嚎,夹起尾巴,钻进柳条丛里飞速逃走了。
伊琳跑过去抱住了吓瘫的儿子,呼唤着:“明明不怕,我的好儿子不怕,老狼跑了……”
老郑头不慌不忙地从坨子上走下来,看着老狼逃遁的方向,问:“明明没事吧?”
“谢谢你郑叔叔,幸亏你赶回来了,不然——”她眼里浸着泪水,嗓音发颤。
“不要谢我,要谢它!”是它救了明明!老郑头亲昵地抚摸着肩上的鹰。那只鹰似乎不屑于理会人的感谢,在老人的肩上蹭了几下利喙,抬起锐眼望着老狼逃走的方向。“早晨我去场部时,东坨子路上发现了狼的脚印,心里放心不下,没敢在场部多待就返回来了。这畜牲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这里好多年没见了。”
伊琳抱过老人肩上的猎鹰,用嘴亲着鹰的头脖和翅膀。老郑头叫明明站在沙地上尿了一泡尿。他说吓呆的孩子尿一泡尿魂就能安宁。倒真的应验,明明渐渐脸色转缓过来,有了血色,眼神也正常了。他抱住郑爷爷的脖子说什么也不下地了。
“欧,你这个男子汉,还怕什么狼哟!”老人高兴地抱着明明,肩上落着苍鹰,迈着健步往回走。
“郑爷爷,你为什么不打死那只恶狼放它跑了!”明明仰起脸问。
“孩子,你不懂。沙漠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珍贵,包括狼。我们这世界是由万物组成的一大家子,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少一个也不行,吓跑就行了,不会再来了。”
对老人的话,伊琳思索了许久。
她问起老人的儿子有没有信来,老人陡地沉默了,脸变得阴沉,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她发现老人怪异地坐在院门口的木墩上,冲落在膝头的鹰发呆。那只鹰歪着脑袋望主人,伸腿拍翅,挂在脖下的小铜铃,时而发出悦耳的声音,随晨风四处飘散。
老郑头站起来从房柱钉上拿下挂在那儿的一只野兔。吹一声口哨,猎鹰便从他肩上飞落到地上。只见他用刀把野兔切割起来,割下一块往下扔一块,猎鹰就伸出嘴迅速而准确地接住那块肉。猎鹰的喉咙里发出阵阵欢快而急促的声响。老人默默地喂着鹰,那张被大漠的风吹得黑苍的脸没有什么表情,唯有那双眼睛偶尔闪出未能锁住的悲凉。
喂完肉,他又绐鹰倒了一小铁碗水。那只鹰把头一仰一伸地饮起水来。他干这些事,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庄重和严肃,好像进行着一种什么仪式。
“走吧,咱们该走了。”他冲着鹰嘀咕了一句,打了一下手式。鹰腾地飞上来,落在他的肩头。他架着鹰兀自往外走去。
伊琳纳闷,走过去问:“郑叔叔,你去哪儿?”
“放鹰”。
“放鹰?去打猎吗?”她没懂放鹰的意思。
“不,放鹰。”老人又极简单、短促地回答。
“爷爷,我也去看放鹰。”明明跑过来央求。
“愿去就去吧。”
她领着明明,跟在老人后边。她想知道个究竟,一路没话,不久他们来到北边的一座高坨上。老郑头仰脸凝视片刻湛蓝迷人的天空。他从肩上拿下鹰,抱在怀里依恋地抚摸着,然后解下了小铜铃。
“你们来告别吧。”他突然说。
“告别?跟鹰告别?”她不解地盯住老人。
“对。跟它告别。”
“你是说把鹰放走?彻底放走?”
“是。这是一只雌鹰,开始发情了。”他并不看她,自顾自说着,“再说,鹰是一只自由的高贵的飞禽,它应该在高空中生活。我也不打猎,老让它伴着我在地上生活,会毁了它的。”
“那你儿子小龙……”她脱口说道。
“你又提起他!”老人突然吼了一句,随即意识到失态,放缓了口吻,“他……来信说再过一个月才能回来。”
原来是这样,难怪他情绪这么坏。
“爷爷,不要放走鹰!过一个月小龙叔叔来了怎么办?”小明明跑过去抱住那只鹰。
“来了再说。这一个月我没闲空管它。给我,明明。”他伸出了手。
“不,我不给你,它救过我的命,我不放走它!”明明紧抱着鹰不放,向一边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