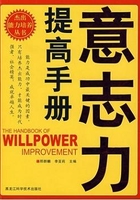近半年来,已有了借书看的门路,同时还买了些内部读物。可惜想看书却没有完整的时间,成天被生活琐事所烦扰,似乎还不如在干校劳动省心。差强人意的只是你妈妈的病还没有大犯,基本上维持在沈时的状态。而我虽有点小毛病,却也无妨。看来老天是同情我的。
你姐姐前些天才从哲盟返京。休息一天,接着就编排“十一”节目,十分紧张。不但暑假休不成,工作反而增多了。所幸她的精神还好,整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学习尚未病例。
月初你哥哥带小梅来京,他是因有工作任务向“海司”来汇报的。现在也住在家里,生活十分热闹。
上月给你三叔寄去一包食品,料已收到。给你姜叔配的老花镜早寄出,同时还寄去30斤全国粮票。文化局政治处已把两封介绍信挂号寄来,大概是电报起了一点作用。创评室的领导先生们得拖即拖,尽管你跑破了鞋底、磨破了唇舌,这些老爷们还是得推且推。哀哉!
工资皆收到,勿念。盼你常来信。虽然我们很少写去。
祝愿你安心工作,身心健康!你哥哥、姐姐问候你。
爸爸、妈妈
十一日(1974年8月)
1974年4月底,姐姐家由西四搬到月坛北街单元楼房,两室,另有厨房、厕所。除了楼层高,可算一步登天了。
1974年初,因为民族学院搞教育革命进驻工人宣传队,需要腾房子。姐姐一家四口搬回同住,老少三代济济一堂生活十分热闹。姐姐夫妇早出晚归工作忙,家务多半由爸爸承担。六七十岁的人偶尔还扛煤气罐爬五楼,他并不抱怨辛苦,令他烦恼的仍然是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他责备自己成了“尸位素餐,无功受禄的东西”。爸爸曾在信中不无羡慕地对我说起姐姐:“他们虽是劳累一些,可比我们生活得有意义。”他渴望对社会有所作为的雄心不减当年。他在《故国》中写:令威非所羡,志在鲲鹏翔。一击九万里,生死寓八荒。翮摧投东海,命危避北邙。彤魂绕故国,何须骨还乡。亲爱的玉儿:首先向你道个“不是”,这样长时间没给你写信,是不容原谅的。九、十月来,华儿曾几次要写信去,都被我阻止了。因为告诉你真情,一定要影响你的工作(何况你正在工作不顺心的时候)。而写平安信,更将引起你疑虑,反倒让你不安。现在好了,一切全好了,我也能提笔给你写信了。提起笔来似乎有许多许多话对你说,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明,过去两个月是个“病月”,大小病包围了一家人。本来很平静的生活,搞得马乱营哗。主要是你妈妈和我,她是老病轻犯,我则是轻病重发(长时间感冒,引起半身麻痹)。现在幸而好了,病痛又成过去,慢慢也会健康起来。毋庸为念!
两月来读到你两封信,使我们少了一些牵挂。教学工作逐增乐趣,确是可喜的事。但两封信里都未提起你的终身大事,未免过于慎言了。我们虽远处异地无力助你玉成,能听到片纸只言的佳音,也将能给我们平淡生活增添一些色调。这种心情你当理解的。
来信仍须挂号付邮,以防遗失!
祝你一切如意!
爸、妈十月廿九日(1974年)
妈妈的精神仍然处于抑郁中,但其他宿疾如气管炎、肺气肿、腰椎骨质增生等越来越严重。爸爸的健康状况也不乐观。近一两年来“病月”
亲爱的玉儿:
托毛主席的福,你三叔总算病愈出院了。这些日子够你操心的,如果你没有病倒,那真是万幸!但我估计你必定要病的。
你责难我不把家里的真实情况告诉你。我倒觉得不告诉你为好,让你知道也不能分忧,而只能给你精神上增加一大堆负担。这既影响身体又影响工作。你说对不?
你英哥再次来京廿多天了,这次来主要是动手术,附带办些公事(夏天来主要为公事,其次是治病)。廿三日在301医院顺利地做了甲状腺肿瘤摘除手术,廿七日就可拆线。经多次诊断到肿瘤取出,均确实证明是属于良性的。因此大半年乌云盖顶,一旦一扫而光。
你哥哥的病一直瞒着你妈妈。经301门诊、会诊、到手术完了,这才把医院诊疗书给她过目。就这样,也不免受些刺激。幸好最近托人弄到些“谷维素”,这药你妈妈服用较好,有调解神经、镇静与增加睡眠的效果,绝无副作用。可惜市面药店买不到。
上述一场虚惊,也是事后才告诉你。你一定又要埋怨我了。好在风波已静,一切如常。埋怨就写信来吧,我是不会丝毫介意的。只要你内心不存什么亲疏之分,我就不怕。
元旦前想给你寄点香肠去,可是近来这里有些食品控制较紧,香肠之类市面很难见到。节日过去可能好买了。
工薪均收到。越越、楠楠也都健壮。勿念。
祝你一切好!
妈妈、爸爸十二月廿六日(1974年)
1975年7月30日,罗烽给女儿玉良的信。在哥哥病情没有确诊的半年里,对于爸爸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了。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希望,爸爸妈妈落难后,更是把一切都寄托在子女身上。1961年,爸爸在《伤逝吟》中写到“故园青青身却故,革命自有后来人”。玉儿:幸亏你送我上站。否则,我个人即便上得车来,也未必找到坐位。列车一直误点,至金州已将到五时,其晚点一个半小时。如在冬季则天黑矣。
到家第一道关:房门锁锈了,干着急进不去屋子。无奈只得去找董连芳同志,幸好她在家。于是搬来救兵,二、三青少年连敲带砸,总算破门而入。可是屋里尘土满眼,霉气扑鼻。原来三爿后窗玻璃被恶少弹石打碎将近半数。为此,风雨、尘埃皆可自由闯进。暮色沉沉,几乎害得我投宿无地。这也幸亏连芳同志,指挥小将们连忙打扫一过。我则被拖到她家去吃晚饭。之后她又送来干爽的铺盖。第二天大早又送来米、油、菜……一大堆,真是盛情难却。
几天来,都是在逐屋较彻底清扫一番。有连芳同志派来即将下厂的一位知识青年做我的帮手,减了许多操劳。今天清扫工作盖可基本告一段落。你来时略可顺眼。
如挂面好买,给我带三至五斤。这里米、面、油俱全,但我懒得动手做。一个人吃饭不入味,你经年累月生活想亦如此。有家未必成家,我实在为你着急!
猪油炼过没有?瓷缸底下压着四十元,备你零用。下月八号左右能来否?能来,时间来得及的话,先函告我一声。
祝你健康、幸福!
爸爸七月卅日金州(1975年)爸爸借暑假姐姐照顾妈妈之机,绕道沈阳回金州。自1972年离家至今已三年。爸爸陪妈妈易地客居多年,其中的辛酸和不便可想而知。他一辈子最怕给人添麻烦,哪怕是子女也不愿轻易打搅。这次他只身北归虽然没对我说什么,但我猜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瞒着我。亲爱的玉儿:你的来信和汇款已先后收到。
我回来的第三天夜里,又从床上摔下来,这次摔得较重,右肋、胯以及头部皆受了伤,服药后逐渐痊愈。现在只是全身动转失灵,头还有些阵痛。本来摔了一下,无甚要紧的,只是上了年纪,恢复慢些就是了,勿念!
沈站匆匆而别,实觉遗憾。最最难过的是未能如约在沈停留一、二日,看看你和德明同志。我平生最恨失言爽约。无怪你不高兴,其咎在我。
你妈妈的精神还好。华儿催我速返京,多半是怕我一个人在金生活不便,但也是由于你妈妈对我过分悬念。你给妈妈买的床单和给楠楠、小梅做的小裙子,大家都十分满意。小梅那件,过些日子给邮去。
粮票怎样处理都行。换全国粮票的事,你也不必着忙。如果调换不便,就不必换,免生枝节。
你三叔最近有信否?你老奶奶健康如何,均在念中。
需要什么,来信说一声。
祝你一切顺利!
爸爸、妈妈
九月八日(1975年)
8月27日接爸爸电报:“华催速归28日31次返京沈不停留。”我凭电报购站台票进站与爸爸会面。列车尚未停稳,车厢里的爸爸先看到我,他的座位恰好临靠站台。因停车短促又兼车内乘客拥挤,爸爸离不开座位。父女俩一个车内一个车外,从开启的车窗握手言别。
那时,大连到北京的直快列车仍需运行30小时,爸爸却买的是硬坐票。但只要陪妈妈旅行,爸爸总是设法坐软卧。楠楠是姐姐的女儿,小梅是哥哥的女儿。亲爱的玉儿:前后两封信都收到了。该及早回信而没回信,既不是我们的健康有问题,更不是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一切归罪一个懒字,是思想上生了锈,热情逐渐降温。这可能是一些没出息的老年人的通病。若不,就是我个人的药石不治之症。过去偶然表现在梦中,而现在却时常表现于清醒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能不感到它可憎,可怕!
大约有半年(或许更长一些)没给你三叔、姜叔、你哥哥他们写一个字去。廿多年前我的警卫员来过多次问候信,我竟如此不近人情地置之不理达一年以上。这一切给我精神上的压力很重,但我仿佛无力改变这种极端反常的状况。我明明知道他们在怪罪我,这是合情合理的。我没有理由希求原谅,因为我的错处都是自觉的。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总是对曹公的“我宁负天下人……”之类的人生哲学不能理解。老人斥之为奸之雄,从演义观之,亦不过火。待略知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之后,对照史实看曹公残酷镇压“黄巾”,再利用“黄巾”安抚的军事力量而争夺政权,继之当上魏朝的太上皇。对此,则不能不感到郭院长的“替曹操翻案”的翻案文章,言之过火和操之过急。看到曹公的“横槊赋诗”形象,而避讳上述的历史真实,更讳谈曹公大造迷宫“铜雀台”寄托“长枕大被”的最终志愿。称做什么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但我读过(仔细读过)郭院长的宏文巨着,倒也有受益的一面,那就是我也在学“宁天下人负我”硕识远见。
话扯远了。这叫无病呻吟,不足为训。
回京将四十天,仅落地两次,不为多。况且伤痛早已痊愈,不爸爸不仅仅四肢受伤,其中有两次头部撞伤血流不止。虽然他自己不以为然,但确实吓坏了我们。必遥念。你想到的做条厚褥子夜里垫在地上,这事你姐姐已为你实现(有两寸厚的棉褥子,即便摔下床来,也能继续睡下去)。越越和楠楠都争着要睡在地下哩,你看可笑不可笑。
我已经有两件毛衣,你再给我织一件,就叫我变成地主了。钱处理不当好改正,浪费时间可是一去不返。学习、工作你会安排得很好的。毛衣应不织或为后再织。多腾出些时间,多读些有用的书为好。
提起书,我该告诉你,《史记》已购得一套(十厚册)。得空并转达德明同志,毋庸物色此书为我操心了。
全国粮票60厅如数收讫。余数留你处,别再托亲告友地调换它了,实在太麻烦!
你的终身大事,何时才能报喜?
祝愿一九七五年让我们看到喜报。
妈妈、爸爸
1975年10月6日
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时,爸爸住在我那里。他对于郭沫若扬李抑杜到不合情理的程度,颇有微词。他曾赋《无题》:秉烛长思寻佳句,行间字里窜蠹虫。睥睨黄巾尊魏武,供奉谪仙损圣雄。铜雀台成拥大被,长安道禁吟哀鸿。只缘不索风流债,千姿万态摆摇中。亲爱的玉儿:“前后两封信及两个月的工薪均收到。”上面这两句话大约是一个月以前写的,记得是周洲去沈阳后几天的事。说实话,这个把月以来,我真忙,忙家务,忙照料病号。周洲离京前,你妈妈开始闹肠胃病。稍好之后,楠楠就患了病毒性感冒,从此就排号病了起来。楠楠刚送回幼儿园,越越又发烧躺下了。越越没全好,你姐姐接班。我是插在越越和你姐姐之间凑了几天热闹,托毛主席福,很快便好了。周洲于上星期天从大连返京,他正赶上你妈妈在唱压轴戏,感冒与气管炎、喘息并发,来势颇猛。经及时注射“卡那霉素”、“安茶碱”和适症的口服药物,才算稳定下来。可是现在我给你写信时,你姐姐正在西屋躺着,感冒重犯。其实她从个半月前做人工流产手术以来,一直未能很好疗养。上班则搞大批判(批判“清华”反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反党集团),下班则忙于家务和照料病号……如此,病当然要反复的。今早给她打一针“卡那”,估计很快就能退烧。我已恢复正常,勿念。
周洲说他离沈去连前,曾特意到家去看望你。你锁着门,灯亮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找到你的住处,偏你不在。否则,至少可以从表面上看看你这几年的生活状况。使我们略可放心。
北京大、中、小学的大批判运动早已开始了。从十一、二月的《人民日报》及十二期《红旗》杂志上的文章,都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的。目前,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大、中、小学校,都已是大字报满墙。上边已联到教育部长周荣鑫。沈阳如何?你和你三叔都身在教育界,深望十分重视这一运动,切不可半点含糊!
你哥哥已回汉。此次来京公干,仅在家呆了一星期,来去匆匆,身不由己。江江与小梅都好勿念。你三叔处如何?上述情况希转达,不另。
祝,工作顺利,身体好
妈妈、爸爸十二月十三日(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