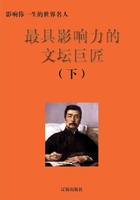爸爸他们到盘锦后,修筑胜利塘的“忠”字坝。工地离驻地田家大队五十多里,不能往返,学员们挖地窨子住。一天,大家正在工地劳动时,爸爸的住处起火,把他所有的行李烧得精光。
妈妈回13连,“造反派”分配她刨冰,烧水给大家喝。有一次,天刚亮,妈妈误将冻土块当石头搬来支在锅底下,她趴在地上点火、吹旺。不料锅里的冰融了,锅下的冻土块也化了。锅掀了,水洒了。她正懊悔不及,“造反派”还要骂:“这个老废物,成心不想给我们水喝。”爸爸趁“歇晌”的机会悄悄帮妈妈捡些毛草,而某些人还要说三道四。那一年的冬天,妈妈的双手、双脚甚至脸颊也长满冻疮。
第二年春耕,大队人马到十五里以外的十四方台种地。出工的路上,妈妈连跑带颠儿也跟不上趟儿。爸爸一个人被分配到村外的大堤边种菜园子。劳动之余,爸爸在小日记本上写《惜园》:一夕风浪破围墙,嘲晖乍冷露成霜。寸丹困守西蕃柿,宁为芜园赴东江。
一九六九、八、卅日在盘锦田家菜园。爸爸记不清一条小黄狗什么时候跑到他那里。爸爸可怜它,喂养它,他们成了患难之交。爸爸白天干活儿,它跟着;晚间回村开会、学习,它也跑前跑后不离左右。盘锦地处辽宁西部,是十河九梢的地界,雨季发水是常事。一天半夜,下起大暴雨,水快没炕沿儿了,劳累一天的爸爸一无所知。小黄狗跳上炕,生拉硬扯把酣睡的主人拖醒,他们刚迈出门槛窝棚就倒塌了。许多年后,爸爸时常念叨“小黄儿”救主的故事,念叨他和妈妈离开盘锦时,小狗跟在卡车后边狂奔,直到看不见。每当讲起这些,爸爸的眼神里总是塞满过多的忧伤。是为那段生活,还是为那小生命?
爸爸妈妈喜欢小动物是朋友皆知的,他们对一切生灵都充满怜惜和喜爱。听爸爸的老朋友讲:“在延安,边区政府给你爸爸配一匹黄马。他常常把马洗刷得干干净净,就是合不得骑。”1961年在阜新矿区劳动改造时,爸爸拿着供应卡去小卖店买火柴,看见一条被咬伤的小狗,他花高价买了几块饼干将伤狗引逗回家。然后,和妈妈给小狗上药、包扎。最后小狗还是死了,爸爸挖坑将它埋掉。
在盘锦“五七”干校的时候,一般学员不能随便外出,什么东西也买不着。大刘(振江)叔叔赶车,谢群叔叔跟车。偶尔他们趁赶车外出的机会替爸爸妈妈买点香烟什么的,先藏在马吃草的料斗子下,再找机会从老白家(妈妈的房东,是心地善良的寡妇)后窗户递给妈妈。
1994年3月23日,妈妈去世一个多月后,我见到已退休的大刘叔叔。他流着泪说:“罗烽、白朗同志对我太好了。我孩子多,挣几十块钱养一大家子。在盘锦,罗烽同志几次给我交伙食费。我一去交,管收费的就说罗烽同志给你交了。下乡插队,临走罗烽同志给我拿钱。我不要,他说下去安家买水桶什么的……”
方冰叔叔讲:“在盘锦我劝你爸爸别抽烟了。你爸爸说:‘太寂寞了,像个孤鬼似的。’有一回,你爸爸来沈阳开会,你妈妈在家。罗烽同志拿出白朗的信给我看:‘我们的蝈蝈死了。’那时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他们把感情寄托给小动物了。我曾经问你爸爸喜欢京戏哪一流派?他说‘原来喜欢麒派,现在喜欢言派,他把人物心理刻画透了。’言菊朋唱的大多是悲剧,从这些可以看出你爸爸内心很苍凉,但脸上一点都不露。”
1969年10月末11月初,爸爸陪着犯病的妈妈离开盘锦干校。回沈阳,暂住大南门省作协机关办公楼里,妈妈的精神病稍微平静了一段时间。原作协没去干校的几位工人师傅时常去看他们。适逢我因病由青年点回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间,搞防空演习。不远处传来尖利的警报声,全城一片漆黑。恰在此时,原机关食堂的许宝元师傅竟从家里摸黑给爸爸妈妈端来一小铝锅热腾腾的清炖羊肉。烛光下妈妈像平时一样和许师傅聊天。
临近年底,妈妈因对组织一再动员她退休难以理解,感到追随革命四十余年却被动退出革命队伍,觉得晚年生活无望而病情逆转。她反复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叛徒”,逼着我去北陵找爸爸在呼海铁路传习所的同学姜德明叔叔,让他证明当年营救爸爸出狱的经过。妈妈滔滔不绝讲个没完没了,急坏了我和爸爸,我们担心她闯大祸。恰巧家里有个打气的煤油炉,燃烧起来呼呼响。为了遮盖妈妈的胡言乱语,不管是不是烧饭,我们都把炉子点燃。后来,她又要求把在武汉海军工程学院教书的哥哥和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的姐姐全部召回来。在拟电文稿时,她坚持要写“母病危速归”。爸爸怕吓坏哥哥姐姐,与她商量:将“危”改成“重”,她坚决不同意,声言不吃、不睡,坐着等他们回来,还说:“造反派不是给我存几千块钱吗,让你哥哥姐姐包飞机回来。”就这样足足说了五天五夜,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时没留神香烟掉在毛主席当年赠送的棉被上,当我们发现已为时过晚。等31日(除夕)哥哥姐姐赶来时,妈妈的嗓子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了。妈妈发病时,一遍又一遍地背诵陆游的《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她曾写:“我最爱主席的诗词--特别是《咏梅》”,“但最能说明我长期以来的处境和目前的心情的,则是陆游的原词。”元月3日,姐姐护理妈妈去北京治病。妈妈到京给我的信中说:“我一到北京,尽管把你姐姐家弄得乱糟糟,鸡飞狗跳墙,但我的心情确实完全舒畅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扎)一尺长的针我也咬牙忍受……”
5日,哥哥和已经累病的爸爸整理三四年以来的随身用具,并打包托运回金州。旋即,星夜赶赴京城。玉儿:今天已是五月九日。你绝想不到现在我还在金州给你写信的。原来七日即由金去瓦房店(复县),可是县革委会安置办公室对我们安置在复州城一事,毫无所知;省“五七”干校与他们并未联系。事出突然,一时难得在复州城找到合适房子。在县招待所呆了两天两夜,没个结果。最后由省“五七”干校驻在复县革委会安置定点负责人孙同志一再请示干校负责人,决定原车人马返回金州待命。干校派专员高同志于明日到金处理下一步如何安置问题。现在我同王、邱二人暂住站前旅社里。家具、行李又运回金州旧居。耗时三日,行程不及二百公里,往返汽车运输费竟达四百余元。虽然是公家开支,也是极大的浪费哩。
此行你未来,真乃大幸。否则,将狼狈不堪矣!
第二步即便顺利,估计十五日前后,我很难离开新安置地点,这是肯定的。因此你三叔来沈时,千万不要等我。佳会交臂失之,实觉怅然。奈何!
客复县,心寐神聊,偶成七律,呈拔公教正,略赎爽约之咎。
东方星红启环球,
泥足南渡何躅躇。
四十一年争战梦,
独酌还醒笑留侯。
回首京都光四溅,
白头小儿敢低头。
髦血未寒丹心在,苹花春老雪复州。你的户口落实否?甚念!要认真治病。还得给你妈妈她们写信。
祝你幸福
父五月九日喜雨夜于金州(1970年)
1970年初,爸爸他们离开沈阳去北京时,有关部门让他们写了退休申请书并要去两张照片。
3月,沈阳电召爸爸去办理退休手续。
4月13日,又接“罗烽速来沈干校”的电报。爸爸安顿好妈妈,匆匆回沈阳办理退休手续。然而,却遇到意外的变化:更改“退休留金州”的原决定,重新按老弱病残安置在复县。事情来得突然,爸爸没有随身携带金州家门钥匙。他二话没说,连夜赶回北京。取上钥匙,再返回沈阳会合负责安置的同志去金州搬家。假如,拍电报的同志能为老弱病残者着想多写两个字,爸爸就不会往返徒劳了。
第二次抵沈时,恰逢4月24日我国长征一号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轨道,向全球播送《东方红》乐曲。爸爸赋诗欢庆祖国发展空间技术迈出第一步的同时,还写另一首《金州再迫迁复州湾途中遇雨》:春花绣半岛,细雨注金城。迢迢靡行止,虚幻似游僧。故国盛四海,故我偏飘零。孤山穷千里,苍茫浮落英。
看到这里,谁不为之动情?谁不为之黯然神伤?你决不相信偌大九州,居然容不下一对风烛残年、为革命呕心沥血大半辈子的老夫妻。
迁复县未果,原车返回金州。因为新的安置地点遥遥无期,经“五七”干校安置办同意,爸爸5月17日途经沈阳回北京照顾病人。亲爱的玉儿:来信已收到。你寄京那封信,周洲没有转来,这可能他以为我们这月初即返京之故。
今天晚车我就陪你妈妈去京。原来本想在你兄嫂处多住些天,但她在武汉不甚服水土,又想外孙,只得提前离汉。武汉暑期已至,今、昨两天均上升35度,月中将增至40度。早点回京也好。
上月十九日曾函干校张连德,嘱他速把我们六月份工资汇京。但这个人不是办事人,工资既未照汇,也不回信说明原因。大概这是少数造反派变成小官僚之一。今天我又写信催他一催。并言明托我的侄女去他处代领(六、七两月份工资),料无周折。如果此人仍然扭捏做态,你可询明原委,并要求他把“意见”写成文字由你转寄给我。如果顺利照发,你可尽快汇京。
在交涉工资中,如遇什么困难,你可以直接找徐桂良同志请教。大概他还没有去盘锦。
你兄嫂及小江江均好,勿念。
临行匆匆。祝你户口落实如意!
妈妈、爸爸七月二日下午(1970年)5月下旬,在爸爸妈妈老年生活中有了一桩喜事一他们抱孙子了,哥哥家生个孩子是父母盼望的。为了使妈妈高兴,以便找到精神好转的契机,6月中旬爸爸陪她去武汉。因为姐姐早已离京回干校,爸爸计划在哥哥家多住些日子,也好有个依靠。然而,在武汉不及半月妈妈又急着回北京。无奈,爸爸只好顺从妈妈的意愿于7月2日晚车返京。
近一年来,由于旅费和妈妈的医药费不断增加,家庭经济捉襟见肘。偏在此时,爸爸他们赖以生存的工资却不能按时收取。原来他们的工资关系在盘锦干校,从6月份开始转到省“五七”干校沈阳善后处理小组。亲爱的玉儿:十二日收到你汇来的工资。第二天就收到了来信。昨午又收到由盘锦汇来的工资。很快,这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你妈妈说,这该归功玉儿办事得力。我也这样想的;“善后”不善,那只有靠“专员”去督促了。事情就是这样子,此说并不过分。
我们是三日到京的。你妈妈这次武汉之行,夙愿总算是如愿以偿。看望了年迈的舅父母,看到了儿子和儿媳,更看到了初生的孙子“江江”,也看到了新中国一绝:长江大桥(六月十四日夜,我爸爸妈妈是姨表兄妹,这里提到的舅父即他们母亲的同父异母兄弟。1937年由上海撤退,奶奶和待产的妈妈就是先到武汉投奔在邮电局工作的舅父家。不久,在舅父家的危楼上生子傅英。建国后,因舅父家子女多,工资低,爸爸妈妈经常寄钱。们同你哥哥,冒着狂风暴雨并带冰雹,安然在长虹散步),而最最使你妈妈神旷心怡的是这阔别卅二年的武汉,追忆了辛苦酸甜的一生。所谓“四代硝烟尚同舟”,此乃她一大自慰也。不虚此行。
但她也有遗撼,这即是沙洋咫尺,未能得见你的华姐。在感情上看得出她是在大力控制着的,但仍耿耿于怀,时而烦躁。加之武汉褥暑已至,夜不成眠,对于她的病甚为不利,因此不得不早期归来。
回京后她安静地休息几天,精神、健康已好转。这些天来她又惦记你的户口问题了。她很赞成你参加街道学习和负起一定的工作,根据自己病情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总是好的。落户口事不忘努力,“尽人事而听天命”。急也无用!假如公社不嫌你这个“病夫”,还能召回,岂不也好。我们认为你也这样想法。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方设法治好病,还要愉快地生活,还要多学多用毛泽东思想。你还非常年轻,为革命大有可为哩。
缺什么药物就来信,只要北京能够弄的就好办。
你姐姐已替你妈妈买到川贝,足够半年用的。你可不必着急了。
六月信也读过。你三叔现在是真正的甘为孺子牛。这项劳动我也干过短时。组织能如此照顾他,连我们也为之感动。这项劳动对他的病是有好处的。
代向你姑父母问候(上封信忘了问候),见到福瑞、桂良同志亦代问候。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到农村插队。后因病被生产队退回。但当时沈阳市对“知青”的户籍政策“只准外迁不准回落”,我成了城乡都不收的“黑人”。每个月到区教育局临时批粮、油票。当初下乡我的住房已交房管所,回来后借住亲戚家。那样的生存状态是不言可知的。即王福瑞,原省作协的汽车司机。解放初,他给爸爸开车。爸爸对待下属,不论是秘书、警卫员还是司机都非常关心爱护,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劳动。所以,爸爸的群众关系特别好。即使爸爸妈妈、落难,这些人也不另眼看待,关系如往常一样密切。
祝你精神健康,万事如意
爸、妈七月十六日(1970年)
32年后,当爸爸妈妈重新踏上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他们徜徉在长江大桥时,回首往事思绪万千。爸爸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怀,作《漫步长江大桥述怀》:昔渡长江踏狂涛,而今漫步七彩桥。龟蛇有山仍相峙,黄鹤无楼更逍遥。鹦鹉赋溅芳洲血,水调歌舒楚天焦。矫时慢物唯君子,奈何兰蕙没莱蒿。
7月末8月初,省“五七”干校安置办先后两函催促爸爸赴沈落实安排他们到黑山县芳山公社某生产队落户。爸爸鉴于妈妈的病情及自己年逾六十且毫无劳动能力的实际情况,复信安置办恳请组织重新考虑安排地点。亲爱的玉儿:难为你了,这些天让你无穷的悬念。不写回信是我的罪过,实在是罪过!因为我尝过惦记亲人的滋味。附去的长信,你读过后,也许能减轻一些对我的责难抽时间送给姜叔看看。暂时你替我妥为保存,不必让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信在廿四日已分寄有关组织及个人了。且听下文。
妈妈的病略有好转,但十分不巩固,仍有一触即发之势。幸有几位好同志帮忙,一切困难都可以度过。望勿为念,愿你专心一意地工作、劳动和学习,千万不要为此过于分神。代向你姜叔、婶致意。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写信。望他们原谅!
祝进步,健康!
父
廿五日夜(1970年12月)
9月初,妈妈的病情再度恶化,强烈要求复去湖北。7日,爸爸匆匆起程陪她去武汉。17日返京。“为时不及两月,两次往返京汉间。生活动荡,昼夜不宁。加上八九个月以来,为安置、为病人,东奔西走,顾此失彼,几无宁日。”年过花甲的爸爸也被折腾得心衰力竭,几尽崩溃的边缘:宿疾肋膜炎复发,疼痛起来就吃土霉素顶着,也不就医;人秋后先是关节炎加重,后转为半身麻痹。
安置办方面对爸爸的请求既不回信也不寄工资。
10月,爸爸再函请安置办以下几点:
(1)安置芳山公社的决定是否可变?
(2)仍留居金州是否可行?
(3)依靠子女,迁汉口,有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