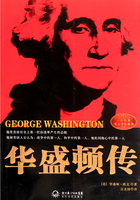从第二次审讯到10月初引渡伪警察厅,爸爸没有再被提审也没有照相,凡承认是政治犯的都要照相。由日本领事馆引渡伪警厅,爸爸与胡起、徐乃健、杨安仁等同在一辆大卡车上。车停伪警厅门前移交花名册时,爸爸看见祖父和妈妈在石阶上远远张望。原来是家里得到青柳的通知说他于今天引渡伪警厅后即会被释放,父亲和妻子是来接他回家的。点名毕,车子把他们载到伪警厅留置场(拘留所)。开始与盗窃案、民事案等犯人杂居一处。后因强盗案犯人诈狱未遂伪警厅重修留置场,于11月间转押道里监狱,住在临时腾出的印刷厂厂房里。穿着夏季服装在不生火的水泥地上生活将近月余,满身生了疥疮。后又转回新修坚固的留置场,与省委交通姜学文、哈尔滨电业局职员王景侠住一个监号。这时胡起、张观等也关在这个牢狱里。
在留置场爸爸与看守山东人刘、冯二人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年轻些的冯对所谓政治犯很同情。有一次,爸爸求冯把他在留置场的情况设法告诉《国际协报>;的妈妈。后来冯把这个差事转给了刘,大约从1935年初刘即和家里接上头。这时候起,爸爸才知道家里一直托亲求友设法营救,并说很快就能出狱。
自到留置场一直没有过过堂,也没照相,只是在入监收押前量了身高和记下特征。约于2月间伪满公布《临时惩治叛徒法》,伪方将该文法送到狱中传阅,“临时惩治法”强调判刑要证据。
1935年4月初,留置场再度降低犯人伙食标准。姜学文领导发起全监改善伙食的斗争,向伪方提出要求,伪方允为考虑。与此同时,伪警厅开始传政治犯复供。胡起因被捕撞车之事坚持原供而被打。与胡起同一监号的中东铁路某机务段段长、政治嫌疑犯胡××复供后释放。4月20日,爸爸被提到伪警厅刑事科未曾复供,经马警佐宣布无罪释放,即日恢复自由,按照小林警佐的要求写了保证书,大意是:我因行为不慎误交共产党徐乃健为友,致遭嫌疑。今后奉公守法,为满洲国服务,并画了押。回监号取衣物时,姜学文秘密告诉他假如出去找不到组织关系时,可到道里石头道街地方检察厅找王推事的太太接头。
十四、营救与脱逃
妈妈是在1934年6月18日上午从车务段一位职员偷偷打来的电话中,得知爸爸被捕的情况。对于爸爸的突然被捕虽然妈妈早有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仍然为他担惊受怕。妈妈匆匆处理完稿件,同时也没有忘记其他人的安危。妈妈打电话告诉左翼朋友金人,并让他转告中共哈尔滨西区宣委金剑啸同志以后不要联系。这一切处理完,当妈妈赶回南岗大直街家里时,敌人早搜查过了。粗略地看一下,敌人只拿走她的一本日记、几封家信和一本阿志巴绥夫的《血痕》。显然,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反满抗日”的罪证。车务段段长齐永延是爸爸的上级又是邻居,故此,齐永延当晚被传讯,次日被释。齐永延告诉罗家,罗烽被关在南岗义州街日本领事馆。祖父母心急如焚,痛不欲生,不只因为爸爸是他们的独生子,更主要是了解儿子所从事活动的严重性质。很快家里开始了营救。
在他们所认识的人中,唯一可以求助的只有祖母的干妹丈张树棠。此人四十多岁,某轮船公司经理兼哈尔滨猪业同业公会会长。他在哈尔滨商界有些朋友。大约1929年初,祖父母由齐齐哈尔到哈尔滨投奔尚在呼海铁路传习所实习的儿子,当时在江北马家船口租住的房子就是张树棠的。两家毗邻而居,张的妻子与祖母相交甚厚,结拜为干姊妹。后来两家先后迁往哈尔滨,张的妻子没有生过子女,对干外甥分外喜欢。当祖父母去找她设法营救时,她是不遗余力的。张本人却有些顾虑,一再追问是否真的没有什么“不法”行为?在祖父母保证和妻子的督促之下,张树棠很快找到日满商行的经理小野。通过小野认识日本领事馆高等系副主任青柳,青柳和小野是老同学。
爸爸被捕的四五天后,张树棠和小野一同到家里,要他们以被难家属的身份去找青柳。祖父因患过神经病恐他言语有失对事情不利,只好由妈妈出面。小野只会几句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勉强可以理解。青柳则只能说一半个不成词的单字。小野首先问妈妈会不会俄国话,当她说不会时,小野即表示:谈话不方便,青柳俄国话很好。由于没有共通的语言,第一次见青柳主要是小野和青柳谈。一两天后妈妈去日本领事馆要求见爸爸时,青柳板着冰冷的面孔把她带到后院一间小平房里与爸爸见面。而青柳通过朝鲜翻译叽里呱啦说了许多,企图软化爸爸的气节。爸爸和妈妈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了握手。五分钟过去了,爸爸被带走。没多久一个姓屈的狱卒传话说:“傅受刑后腹痛不起,病得很厉害。”建议“家里送个腹卷(毛围腰)给傅以暖腹”。这名狱卒也是张树棠介绍认识的,妈妈曾去屈家看望他的老太太,并送去四色礼。妈妈带了“腹卷”、《新旧约》和仁丹等物再去探监时,没有见到人只把东西留下。十余天后,家里收到爸爸从牢里偷偷捎出来的一封密信,信中说徐乃健诬陷他是共产党,他不能承认。
第二次妈妈在高等系探视爸爸时,他刚能走动。会面时因为有高等系主任松原在旁监视,仍然不能交谈。妈妈给爸爸带去一条小手帕,上面绣着“珍重”二字,暗示他放心。为了解救虎口中的亲人,即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他们几次通过张树棠给小野和青柳送礼,而青柳总是表示“慢慢的”。
10月某日,张树棠传来消息说爸爸将无罪释放。家里不放心乃去找青柳叮问。青柳明确告以:明日上午到警厅办个手续即可自由。次日,祖父与妈妈带着一件大衣早早去伪警厅大门外等候。谁知囚车到伪警厅前稍停又扬长而去,仅仅与爸爸远远地见了一面。家里怀疑受骗,妈妈去找青柳。青柳却两手一摆,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
据张树棠对祖父说,青柳未能实现诺言,与伪警厅小林警佐从中作梗有关。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此之前,中东铁路地亩局清丈科徐科长,在职时曾经因清丈地亩贪污。被损失者告发,小林负责处理这个案子。小林受徐贿赂处理不公,后被原告告至日本领事馆。经青柳调查结果证明小林受贿,徐科长被押小林受处罚。因此,小林有意报复。尽管这次努力落空,祖父母并没有放弃继续通过青柳用金钱赎买儿子,这是唯一的办法和希望。为了筹更多的钱同时也怕失业(因为此前爸爸托人给妈妈捎信,妈妈不在,信交给别人引起报馆怀疑。
虽然不知监狱里关押的人与妈妈是什么关系,报馆还是剥夺了妈妈的编辑权),妈妈于1934年初冬,通过她祖父故友孙x帮忙,谋得中东铁路材料处办事员的兼职(报社见妈妈进了中东铁路而释疑,又让妈妈做编辑,因白天要到中东铁路上班,改为晚间在报社上班)。同时,爸爸呼海铁路的同学、同事也自发的募捐营救。祖父母又给青柳等人送去金镯、金表、宝石戒指等重礼。前前后后用去千余元。
1935年4月中旬,青柳通过张树棠告诉祖父母采用连环保的方式保释爸爸出狱。所谓“连环保”,就是由他保小野和张树棠,小野、张树棠出面保爸爸。他确信这次是牢靠的,果然,4月20日爸爸无罪释放。
爸爸被捕后,祖母曾到日本领事馆要求见儿子。遭到拒绝,回家服安眠药自杀被救,祖母在菩萨面前许了愿。儿子出狱后祖父母一为酬谢“恩人”青柳,二为“还愿”,在家里请客。席间,祖父对儿子能否回铁路复职表示怀疑。青柳一口应承说保证回铁路复原职,如不愿回原铁路,愿到满铁株式会社工作也可以帮助推荐。青柳的热情引起爸爸的警惕,他插话说:在日本领事馆受了不应受的重刑,把身体和脑子全弄坏了,第一步是先治好病。当时青柳又慷慨介绍在斜后街南头,某医院一位有名的日本内科医生。爸爸勉强陪着喝了两杯酒,席未散便假醉退席,躺在床上狂笑并胡言乱语耍酒疯。
约隔两三天,妈妈陪他到青柳介绍的日本医生那里检查病。结果诊断他患较严重干性肋膜炎及营养不良症,需医疗、休养半年方可痊愈。因此,他也当真吃药、休养。买了钓鱼用具,差不多每天到松花江僻静处独自钓鱼,什么人多的地方都不敢去,也避免与熟人接触。经观察证明确实无人盯梢,才去地方检查厅找王推事,而传达室说王已离职。找不到党的关系爸爸很失望,但也不敢打听或过江去找以前呼海铁路的党员,怕暴露了同志,发生是非。无奈,与妈妈密议决定俟机逃离东北。首先,把祖母打发去沈阳外祖母家;然后,迁离赵段长的官合免得连累赵夫妇。由霁虹桥街搬到道里外国四道街一个大院的西厢房。这个大院的楼上,住着呼海铁路同寅徐造端及其妈妈兼职于中东铁路的同事周树铁。同时,左翼青年金人每天晚饭后到这院一位苏联妇女处补习俄文。爸爸原本动员与党已经失掉联系的金剑啸一块出走,但他因家庭所累走不开。爸爸让金到齐齐哈尔邮电局找他的同学王任侠。金剑啸通过王任侠的介绍到黑龙江民报工作,暂时隐蔽。
爸爸出狱半月后,狱中展开罢饭斗争。冯看守带出姜学文口信,要他买些黄蜡,吃下黄蜡可以多熬时日。爸爸请祖父买好黄蜡交给冯。此间,他一面找党,一面尽自己所能帮助同志。不但如此,还运用文艺这一武器继续和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如:1935年6月11日和7月2日分别在《大同报》副刊《满洲新文坛》上发表诗《为了你》、《(我不是逃避》、《藏着什么东西》等。
7月8日,妈妈在中东铁路局材料处快下班时,同事周树铁说接伪警厅电话让他转告妈妈再转爸爸第二天上午到刑事科谈话。当晚,全家围绕去与不去反复考虑、分析。最后认为如期前往才是上策。当时估计,假若有什么新的严重情况发生,敌人尽可以立即逮捕爸爸,不会电话转告。去,表示理直气壮。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爸爸到伪警厅刑事科。日警佐小林把他带到楼下一间密室谈话。小林一会儿和颜悦色,一会儿暴跳如雷,目的仍然是要他承认“九一八”之前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开导”他说大日本不究既往,只是讲清楚备个案。而爸爸一口咬定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共产党。就这样,谈谈停停从上午到下午,最后小林急了,亲自开着摩托车把徐乃健从监牢里提来对质。徐向爸爸赧然一瞥低下了头。小林呵斥徐叫他赶快对质。徐犹豫一下对爸爸说,自己受刑不过牵连了同志,使同志也吃了苦,又说:“你能出来,减轻自己一些负疚。”翻译制止徐说下去。小林听了翻译后,粗暴地摇着徐的肩膀叫徐复述他的口供。徐乃健懦怯地说,他已经说了几遍了,再没有新的好说了。小林追问徐,傅是不是共产党?徐说是。小林马上叫翻译把徐带下去,狞笑着对爸爸重复一句话:“乔山道(共产党)的不是?”等翻译回来,小林逼爸爸赶快承认,不承认也要枪毙。爸爸坚贞不屈。于是,敌人发疯似的用皮鞋踢他,打他的耳光。失望之余,小林叫翻译把爸爸送回留置场。翻译出去一会儿回来对爸爸说,留置场快要下班,不收押了。于是又把爸爸引到楼上刑事科。小林又叫准备车子,送南岗警察署拘留所寄押。这时马警佐出来“说情”,让爸爸先回去,说他有保人,要跑也无处跑,但是,叫爸爸写个保证书--关于今天的审讯要保守秘密,不得告诉他人。并于明天上午九点到厅听审,还把爸爸的一顶新草帽扣下。这次没有录供也没有画押。
当爸爸走出伪警厅时,看见祖父已在门口等候。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对祖父说情况严重,不惜牺牲一切,乘敌人不备,坐晚车离哈去沈阳。祖父告诉爸爸,妈妈以接母病危电报为由,向社长张复生请假一周,明早车去齐齐哈尔,并预支七月份薪水。回家后整理简单行装,床上被褥及一切什物均原样未动。
天黑后,金人陪祖父拿着行李先去香坊小站。金人代买三张到沈阳的火车票和站台票,若被敌人发现就说是送祖父走。开车前半小时,夫妻俩假装去江沿儿散步,住房拉着窗帘,电灯没关,房门没锁。事先等在僻静处的徐造端为爸爸换上绸长衫和新买的礼帽,爸爸、妈妈雇辆汽车飞速去车站与祖父会合。祖父和妈妈先上车,分坐两处。爸爸始终站在站台上,一直等信号员给了发车信号他才敏捷地跳上去。
列车抵达沈阳南站,爸爸、妈妈等候在站前小客栈里,祖父行色匆忙去通知家住大西关太清官后边的外祖母。妈妈与寡母、弱弟晤别,情急中外祖母也没有忘记给女儿拿些盘缠。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女二人更不会想到这匆匆一别,竟成永诀。爸爸、妈妈经沈阳到旅顺,乘日本商船“大连丸”号潜赴上海。爸爸化名张文,身着长衫、头戴礼帽装扮成商人。轮船行驶到青岛港需要停泊装卸货物,为安全计,二人不敢在船舱中停留等候,只好上岸在市区“闲逛”半日。海上漂漂荡荡几日总算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