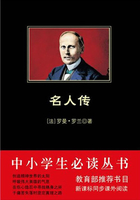写作上最勤快的是弋白,她的《(悚栗的光圈》较比《夜哨》上的《叛逆的儿子》,无论在结构与技巧上都有相当的进步。
中篇小说有彭勃的《星散之群》,这篇小说的企图是很大的,彭勃是诗人,他要以诗情描写地下室的群像,那文章起始是重而有力的……他的小说正在刻画两个对峙人物性格的高潮处,突然中断了,这是田倪、田娣离开哈尔滨不久以后的事。
……康德元年(1934年)年尾,《文艺》在无声中停止了它的呼吸。北满文艺基于人的星散终于一蹶不振了。
其实,《文艺》并非在无声中停止了它的呼吸。20世纪90年代初,哈尔滨文联主席刘树生同志曾寄来一张他珍藏多年的1935年1月15日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那上面刊载妈妈写于这年1月9日的《文》终刊词,题为“结束了《文艺》周刊”,署名刘莉。她在文中说: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周刊《文艺》悄悄地来到了人间,它经过了重重磨难,苦斗着,挣扎着,颠簸着,得以维持将近一年,延续了四十七期。现在,它好像松花江之秋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现在,为了本社变更出版计划关系,一切副刊均行停刊,因之《文艺》亦随之灭亡!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即如为本刊执笔诸作家,率毕星散:田倪君与田娣女士中途相携出国,彭勃君又浪迹天涯,莫期行止!巴来君不幸失业,吃饭问题没法解决,已无心创作,惟有山丁君自始至终,努力撰稿……至于我呢,不过是军中小卒;虽然也时或随众摇旗呐喊,又是幼稚不堪,难入大雅之堂!徒负编辑职责,自知一无建树。但,《文艺》本身究竟如何?评论者自不乏人,如今也无需我言之喋喋。就是这样结束了吧!现在为谨向执笔诸作家致谢,并向爱护《文艺》的广大读者诸君表示“毫无贡献”的歉意。
同时,我捎带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离开本社,仍然继续服务,不过现在我仅仅是一个撰稿者,不负其他责任。当然,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常在报纸上见面的。
20世纪90年代,中共哈尔滨党史办的王式斌说,东北革命文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广泛地进行文艺宣传,建立文艺阵地,创办画会和剧团。从1933年春到1934年这段时间,是东北抗日革命文学兴旺的时期。
捕前与被捕
1934年3月,由于满洲团省委宣传部长杨坡的被捕与叛变,引起团省委领导机关及哈尔滨市团委的大破坏。并牵连党组织的局部被破坏,但党的省委机关未遭破坏。约4月下旬,呼海铁路工程科的徐乃健突告失踪,消息传遍路局。徐乃健弟弟徐乃金和爸爸是呼海铁路传习所同期同学。1929年爸爸、徐乃健同时入党并在同一党支部工作。
1932年1月,爸爸党内关系由呼海铁路“特支”调哈尔滨道外区(也叫东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直接领导人老张即***同志。他的家也由江北的马家船口搬到哈尔滨道外区。此后,徐亦脱离铁路支部,另任党的工作。调离后的两三年间彼此很少来往,这是党的纪律。
徐乃健失踪约半月后,省委秘书长老马即冯仲云同志告诉罗烽:徐乃健同一女同志刘樱花假扮夫妻住在红砖街88号满洲省委接头机关,二人同时被捕。刘樱花即1933年被捕的省党委书记王达理的妻子宋兰韵。王达理入狱后,曾以土匪嫌疑罪判刑一年。此时复被杨坡指供,受刑不过供出刘樱花。徐乃健当时任省委会计。据内线消息说徐、刘在日本领事馆刑讯数次,均坚不招认。刘樱花刑后流产,徐乃健曾用眼镜片割脉自杀未遂。冯很有把握地估计徐完全可以熬过去,同时指示罗烽不必动,但要设法将上述情况通知原支部书记胡起和支委张永福,万一情况有变被捕,应坚不承认为共产党员。张永福在松浦警务段当办事员,通知他不难。唯胡起当时在石人城车站任副站长。爸爸通过铁路电话约他在哈见面。
爸爸再次清理家中书籍、函件、照片等。书架上摆起《古文辞类纂》、《古诗源>;等线装书和山水画册等,以防搜查,使敌人无证据可寻;此后他身上经常带几十元钱,以备事态突变时逃避之用,并嘱咐妈妈,倘若遇到不幸,一定不能泄露任何机密。
大约5月下旬,冯仲云再次来爸爸家时,他已剃去长发准备离哈他往,冯要把他们的小女孩送到爸爸家寄养。爸爸因自己也处于惶惶不安中,不得不婉言拒绝。同时爸爸告诉冯仲云为防不测,他们正设法把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夫妻送离东北。
6月18日,爸爸由哈尔滨三棵树车站乘客车过江到松蒲镇车务段上班。还没开始办公,日本领事馆便衣警特即跟踪进入办公室,声称他因反满抗日立即拘捕。敌人不容申辩,马上要将人带走。爸爸要求整理公事、交待日籍顾问,被允许。他在整理公事时悄悄告诉办事员老陈,设法给在《国际协报》上班的妻子打个电话,好让她有所准备。
爸爸在该铁路服务五年,不但工作认真业务能力强,而且与上下同寅的关系也好,刚刚被晋升车务段分段长。公事交待完敌人给他戴手铐时,车务段日籍顾问安达向警特表示抗议,说他是个好职员并保证他是个好人,但警特不理睬。在等候北来的客车时,敌人把他带到警务段段长的办公室里对他突然袭击说:徐乃健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赶快招认,免得到日本领事馆受苦。敌人这一审问竟让他及早得知被捕的原因,使他如何对付敌人心里有了准备,开始还担心是萧军、萧红未能安全脱逃而牵连了他。在解往松浦站时,爸爸故意把手铐暴露在外面,暗示给松浦站电报室里正在打电报的共产党员范用存,好让他尽早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呼海铁路的其他共产党员,如机车厂的工人老梁、车童高希霖、电报生林鸿飞和车队长李荣弟等。当时,这些同志虽然都不在一个支部,但这个警号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爸爸在三棵树车站下车等候日本领事馆的汽车时,发现日籍顾问安达同车追来,仍然力保他,但终被警特所拒。
关于拘捕后的细节,爸爸在1957年9月12日写给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和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的材料中说,18日当天被关押在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第七监号,号内原有日籍犯人四名,鲜籍犯人一名。19日早犯人集体到洗脸室洗脸时,路过其他监号听到徐乃健小声叫他的名字。徐乃健坐在地板上,侧倚着木栅栏,带着歉意悄悄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你!”爸爸深恐被看守发现增加麻烦,一闪而过,什么话也没说。在同一天的上午,他被提去过第一堂。审讯内容是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状况、简历和有哪些朋友。关于“朋友”,爸爸回答说第一、二届铁路传习所有许多朋友。在具体列举时,选的都是与党与反日同盟会无关的人,多半是他领导的足球队和蓝球队队员。但其中包括传习所一期同学、车务段段长齐永延,也包括徐乃健。之所以不回避与徐乃健的朋友关系是争取主动,这样可以在政治问题上迷惑敌人。在这中间敌人把中东铁路姓窦的工人拉出来严刑拷问,该同志坚不承认。窦被带下后,敌人叫爸爸承认,爸爸否认。敌人叫他回去考虑并在笔录上打了指印。
距第一次审讯四五天后的一个早晨,再次被提审。在取调室旁一间小屋里他意外地遇见妻子。他用力握着妻子的手,相对无言。而敌人却在一旁唠叨不休,什么“说几句话吧,五分钟快到了”,什么“傅君,现在能承认大日本立即恢复你的自由”。夫妻二人仍旧一言不发。时间到了,他被带进取调室。审讯开始敌人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的好朋友徐乃健是共产党,他是个聪明人,已经承认了。他也供出了你,你要学聪明人,马上承认吧。”
爸爸回答说:“徐乃健是我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但我不知他是什么共产党。哈尔滨大水后,1932年秋天我们路局由松浦迁来哈尔滨。我仍在松浦镇办公,早去晚归公事很忙,与徐乃健两年多不见了。这两年多他做了些什么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承认是共产党我也不知道,与我不相干。我不了解共产党究竟是做什么的,在铁路上我是好职员。若不信,可以调查。”
敌人说:“我们早已调查过了,你和徐乃健一伙人干了很多反满抗日的勾当。徐乃健都说了,你也说吧。说了罪轻,很快就得到自由;不说免不了吃苦(指着室内刑具威胁着),终归还要你招认……”
爸爸回答说:“我不能随便胡说。你们要好好调查,不能诬赖好人!”这句话激怒了敌人,一边拍桌子一边拿起桌上的木屐狠狠砍他的头,并大叫道:“你就是共产党,什么诬赖好人!”
爸爸理直气壮地质问说:“你们无根无据就逼我承认是共产党,法律是不允许的。”
敌人说:“徐乃健就是证据!”敌人翻来覆去就是要他承认。爸爸最后无奈地说:“假如你们非逼我承认不可,就请随便写几条,我来画押好了。”敌人感到受了侮辱,拿起木屐又要打,但是立刻又放下,笑嘻嘻地说:“以前你们的张作霖才这样做。大日本帝国的法律是依据犯人自己的供词论罪的。你不懂,你的常识太少。”接着厉色问:“常识不多,可是你会宣传抗日反满。你家里的油印机已被搜查出来了,这不算证据吗?”说完拿起爸爸的右手,仔细查看中指的厚茧,得意地说:“承认吧,傅君,证据多得是。”
一听敌人说搜出油印机,他心中反而更踏实,知道敌人并不掌握什么真凭实据。事实上,家中的拌子房里确曾藏有一台日本掘井式的油印机。知道这件事的除省委领导和他的家人外,还有徐乃健、林鸿飞二人(原因是1932年春,有一次为了赶印大批传单和标语曾约他二人夜间来帮忙,平日里都是妻子和父亲帮助)。但是,1932年秋天松花江决堤时,它被大水冲跑了。因此,他泰然而坚决地否认有油印机,但他承认刻过蜡板,而且很多。那全是铁路公事,不信可以调查。
午后,敌人继续审讯,态度很随便,问话前后矛盾。敌人说:“傅君,我们知道皇军来到满洲以后你是个好职员,可是在‘九一八’以前确是共产党啊。‘九一八’以前大日本管不着,过去的事也不想追查。只是你要承认,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承认了,就能很快把你释放的。”
爸爸看穿敌人的圈套,决不上当。于是,敌人狰狞的面目露出来了。把他牵到为灌凉水特制的木凳子旁边,用绳子把他的胸部、膝部及两脚绑在木凳子上。然后,把院心洋井的凉水灌进约二十磅容量的扁嘴大铁壶里,再用大铁壶往爸爸嘴里灌,并大声叫喊:“说,快说!你是共产党,不说灌死你!”边灌边用胶皮线抽打他的肋部,灌了两壶,他的头和肺几乎爆裂开来,但脑子是清醒的。敌人除了声嘶力竭地叫骂,丝毫没有击中要害的内容。他推测徐乃健的口供一定是简单而含糊的。关于呼海铁路特别支部自1929年成立到1932年春的几桩重大事件,如:发展的十余名新党员;呼海铁路党的外围组织“知行储蓄合作社”及手抄本的《知行月报》;1931年冬“特支”援助马占山部队北撤,截阻日军追击而发动铁路员工抢机车、拉车皮过呼兰大桥,然后焚毁该桥:1932年春,领导由路警组成的别动队配合宫部义勇军袭击松浦的日本驻军等,可以肯定徐乃健均未供出。否则,敌人决不会抛开这些有力的材料不加追问。
第二次审讯熬过去了,没有画押。因灌水过多发际渗血,肚子剧痛,十余日不能起床,也不敢吃饭,每天以酱汤泡面包度命。熬是熬过来了,但是他却落下终身后遗症,每当睡熟后四肢就不自觉地抽搐、挥舞,有时手脚或头部被碰伤甚至从床上摔下来。年岁越大越厉害,无奈他在睡觉前用软垫铺在四周保护。
数日后,全监放风。监号与监号衔接绕网球场散步、晒太阳时,爸爸看见头缠纱布的胡起。因相距较远,爸爸乃假装肚子疼稍停等胡走近时,乘机说明互守原约坚决不供之意。并知彼此被捕均系徐乃健所供,还有“九一八”后增补的军委张永福也同时被捕,但未送日本领事馆。
约于入狱二十多天后,同号鲜籍青年朴某将取保释放。爸爸在刑讯后朴曾服侍、照顾他,轮到爸爸倒便桶、擦地板都是朴某替做。他不爱讲话,有时偷偷地掉泪。这次他愿意给罗家里捎个信。爸爸也想把审讯情况告诉妈妈,使她心里有底。信纸是从《新旧约》全书上撕下的白边,用小扫帚棍儿蘸擦鞭伤剩下的一点碘酒而写成的。信中说:“……徐乃健咬我是什么共产党,这都怪我没眼力,交下这样朋友。他们用刑逼我供,但我至死也不能招认。我的身体尚好,请勿为念……”这样的内容即便落到敌人那里对他也有利无害。信是装在妈妈送进来的小仁丹管里,上敷仁丹。信带走后不及一周与妈妈在高等系办公室会见。她带来一盒糖果、一条小手帕和一管跟装信同样的仁丹。经敌人检查后,糖果被扣留,仁丹和手帕给他。手帕上绣有“珍重”二字。一切都在意会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