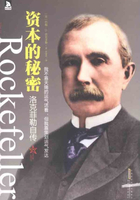虽九死其犹未悔
1935年7月15日,爸爸、妈妈躲过敌人四伏的陷阱到达上海,回到了“家”。然而,踏进“家”门并不意味着来到人间天堂。十里洋场,高楼耸立,人海茫茫,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却上无片瓦,下无寸席。无奈,他们只好投奔唯一的朋友萧军、萧红并暂时寄居在他们极其简陋的家中,然后再做计议。
二萧是半年前由山东来上海的,那时他们只住一间阁楼。房主唐豪是律师(曾出庭为“七君子”辩护),他住二楼,楼下是他的办公室。这时的萧军夫妇刚刚开始发表些短文,生活也异常窘迫。幸亏爸爸还剩下四十多元盘缠,四个人勉强维持了两个月的生活。后来,萧军介绍说唐豪准备办小学校,那里可以住。爸爸、妈妈便搬了去。但是学校没有办成。在无可奈何之下,他们于9月下旬搬到法租界亭子间与舒群同住。先在这个里弄居住的有沙蒙、辛劳、塞克等一批潦倒文人。不久,爸爸、妈妈单独搬到英租界。祖父母在沈阳避居半年有余,不仅生活困难,更严重的是长期无户口不能久留,亦被迫尾随来沪。祖父母来后他们又由英租界搬到日租界的北四川路。七七事变时,爸爸、妈妈又在法租界与舒群、丽尼等人为邻。
从萧军处搬出时,爸爸、妈妈几乎囊空如洗,只好靠典当身边的衣物过日子。听妈妈讲:第一次舒群和爸爸、妈妈去当铺典当妈妈在齐齐哈尔的女朋友赠送的纪念品--一块坤式手表,舒群不好意思,远远地等在当铺外边。那时,“一件毛衣常常典当几次”。但是,生活的拮据并未使他们落寞和消沉。反之,却寄予一个强大的希望:只要爸爸找到地下党接上组织关系,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因此,爸爸、妈妈总是怀着乐观的心情追寻着、奔波着。
然而,生活确是逼人--他们写了文章寄出去没人要;10月,典当已空,借贷无门。“三个人简直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又兼妈妈妊娠五个多月。在此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刻,只好每天借二房东的报纸看有无招考书记员的广告。一日,他们发现《申报》有一条“某书店招考粤籍女打字员”的广告。因为妈妈原本有华文打字之特长,虽非粤籍也只好投函报名,以冀万一幸取之计。未几,得复信:可往试。初到上海,妈妈的路径不熟。爸爸、舒群陪她前去面试。妈妈凭着一手漂亮的小楷和娴熟的华文打字,当即被录用。他们三个人总算暂时解决了断炊之苦,没有流落街头。尽管如此,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和妈妈也只能共吃一份客饭,事实上也仅仅将及半饱而已。
爸爸、妈妈流徙上海、武汉、重庆的几年间,在生死须臾可至的险恶日子里,假如单纯为了生活、为了苟安,爸爸完全可以凭着铁路供职七年的履历、凭着东北流亡交通界的资格到南京政府交通部报到登记,即刻便可以得到职业(这是国民党对沦陷区从事铁路、邮政逃亡人员的一种特殊措施)。不仅如此,就是在上海时的沪宁路、在武汉时的湘赣路、在重庆时的成渝路和川滇路都有从东北铁路逃亡出来的旧同寅,他们在那里担任许多重要职务。同寅们也都为他的生活考虑过,希望他能到各自所在的铁路工作。但是,爸爸对于这些出路都认为有碍于他的政治前途,而一次次地拒绝,一次次地放弃。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个人生活优裕与赤贫间,爸爸妈妈选择了后者。为了寻找党,为了追随光明,他们宛如飞蛾扑火虽九死其犹未悔。
1935年9至10月间爸爸经舒群认识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周扬,见面接谈并填写详细履历,于11月正式接上党的关系并加入“左联”。罗烽、舒群、陈荒煤、周立波、沙汀在同一个党小组,领导人是戴平万。几乎与此同时,爸爸、妈妈开始在进步文艺期刊《海燕》、《夜莺》、《作家》、《光明》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
1935年底,妈妈在吕班路家里生一男婴。小家伙儿聪明伶俐,逗人喜爱,十多个月时就能随着房东的风琴声摇头晃脑地哼唱。可惜,未满周岁却患了脑炎。那时的老百姓是万万得不起病的,挂一次诊号就要五块钱。动荡中的爸爸、妈妈再次忍受痛失爱子的煎熬。天下父母有几个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又有谁不盼望孩子能茁壮成长?更何况这是他们夭折的第五个婴儿!
1936年初,为了组织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6月7日,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主席茅盾。“协会”在6月10日创刊的《光明》半月刊上发表了宣言,刊载了简章并公布了加入该会的会员:王任叔、朱自清、洪深、杨骚、郑振铎、欧阳凡海、罗烽、艾芜、臧克家、王统照、艾思奇、任白戈、沈起予、茅盾、谢冰心、白薇、周立波、徐懋庸、郭沫若、陈荒煤、丰子凯、沙汀、郁达夫、郑伯奇、叶紫、欧阳予倩等八十九人。在简章中说:“本会以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为宗旨。”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从当年夏丐尊6月25日发表在《光明》二期的《文艺家协会成立之日》文中简略地看到协会成立时的盛况。文中介绍说:“成立会是星期日下午二点。郑伯奇打开名单一看已有一百几十多名……后来三间打通的屋子竟然没有座位,许多人只得挤在墙边去站立。”
爸爸被聘为协会的驻会秘书(另两位秘书林淡秋和欧阳凡海不驻会),负责“协会”日常业务,联络各部负责人以推动文艺运动。会址在法租界霞飞路支路环龙路中间的一幢楼的地下室里。这里环境较清静,行人不多,路两侧是高大的法国梧桐。因为是半公开的会址,爸爸为了安全常常以“散步闲谈”的方式与同志们接头会面、交换信息、传达工作。
“两个口号”展开论争后,爸爸最后虽然是在“国防文学”派这边签名,但态度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爸爸在《文学界》(1936年8月10日,一卷三号)发表的表态文章《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中,根据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论述了“国防文学”口号的必要性。他认为:“……正因为我们有了战线的统一,才有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需要。所谓国防,也只有有国家的民族才配去‘防’,然而,根本没有‘爱’国的决意,自然‘防’字也就无从谈起了。”文章中含蓄地批评了统一战线不要阶级斗争的右倾情绪,同时也要警惕“民族主义文学”派借“革命”的假肢破门而人。
鲁迅先生病故的那天中午,罗烽、荒煤、舒群等刚开完党小组会,在环龙路街角的小餐馆里吃饭,从报童叫卖的“号外”上惊悉这一噩耗。三个人饭也没吃完,抱头痛哭了一场。爸爸的痛哭可谓百感交集。早在青年时代开始接触新文艺便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他十分景仰先生。当初鲁迅先生知道爸爸、妈妈到上海,在给萧军的信中说:“你的两位朋友南来了,很好,等身体好些再见他们。”后来听萧红说先生要见他们,然而却被某种缘故耽搁了。送葬时爸爸是纠察队员,在殡仪馆里无比悲痛的爸爸得以瞻仰先生的遗容。
从关外潜赴上海后,爸爸、妈妈虽然生活动荡、日子艰苦,但文学创作却一步步走向成熟。爸爸仅1936年一年就在《海燕>;、《作家》、《文学界》、《光明》、《中流》、《文学》等刊物发表大量小说、散文、诗歌及评论等。稍后,分别由北新书局和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及中篇小说集《归来》。短篇小说《第七个坑》被译成英文在《国际文学》上转载,《特别勋章》和《到别墅去》被选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印的《1936年短篇小说佳作集》。
妈妈虽有家务之累,可她也努力地去创作。她先后发表了小说、散文《伊瓦鲁河畔》、《轮下》、《沦陷前后》、《探望》、《哀愁中》、《女人的刑罚》等等。为了纪念“九一八”这个悲愤的日子,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收有罗烽、舒群、李辉英和白朗等人作品的《东北作家近作集》。
爸爸、妈妈以上的这些作品大多以反封建、反侵略、反投降为主题,反映了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蹂躏下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英勇的反抗斗争。爸爸、妈妈在上海文坛的出现,特别是爸爸的迅猛崛起引起读者和评论界广泛关注。《光明》八期(1936年9月25日)沈起予在《本志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的报道中写到,出席9月8日座谈会的一位读者说,小说我们喜欢《呼兰河边》、《野战演习》、《蒙古之夜》等篇。另一读者说,是的,我们特别喜欢罗烽、舒群两位的作品,因为里面都告诉了我们许多事实;像《王秀才的使命》那样从图书馆中得来的材料我们感不到多大的兴趣……
诗人杨骚发表在《光明》二卷二号(1936年12月25日)的评论文章《历史的呼声》中说,罗烽的《伟大的纪念碑》等诗,是国情危重的时代的“愤激反抗之声”,“这儿没有叹息,没有懦弱;这儿只有呐喊,刚强”。而对于罗烽的小说创作,立波在《1936年的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1936年12月25日《光明》二卷二号)里有详尽的论述和评价。
罗烽的《狱》等,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的水准……
另外,一位描写东北社会的新创作家罗烽和舒群有着不同的风格,如果说舒群是明朗,那么罗烽就是沉着。他没有舒群的锋芒,有时却比较深刻。他描写的范围很广阔,火车站附近的人们和狱里的人们写得最真切。他的《呼兰河边》是敌军蹂躏之下的一个牧童的悲剧……
罗烽大约是目击了或身受了敌人的残酷的待遇吧,他常常悲愤地描写敌人的残酷。《第七个坑》也是这种主题。他在那篇上的成功,不是他的关于敌人的残忍的描写,而是他描写皮鞋匠耿大的恐怖心理的很少的几笔,和他反映九一八以后的沈阳的乱离的情况……
罗烽的描写“满洲国”官员荒淫和卑鄙(《到别墅去》),描写铁路工人的被损害的生活(《岔道夫李林》)也相当成功。年底,几位东北作家办《报告》半月刊,编辑者署名是黄硕(即黄田)。1937年1月10日出版,可惜只出了一期。
1937年4月初,爸爸在上海迎来了哈尔滨的老朋友金人,他带来金剑啸英勇就义的消息。在沪的朋友无比悲愤,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英灵、更为了继承烈士的遗志,他们着手出版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在爸爸的倡议下,联合在沪的东北作家萧军、萧红、舒群、白朗、金人、杨朔、林珏等集资(个人稿费的一部分)与自愿捐助,出版了64开本的《夜哨》文艺小丛书,由上海科学图书公司发行。白朗、金人担任义务主编,罗烽则帮助跑印刷所和负责校对等杂务。书是在静安寺路哈同花园对面的中华书局印刷所印刷的。5月,小丛书陆续问世,有舒群的小说《松花江的支流》、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和金人翻译的苏联绥拉菲莫维兹的短篇小说集。丛书出版后,林珏在霞飞路摆摊销售,很受读者欢迎。计划出版的还有周扬的一篇文艺理论文章和胡风翻译的罗森达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可是,未及交稿,七七事变发生了。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了募捐办公室,由爸爸和欧阳凡海负责。同时,爸爸还与周扬等组织“文艺家战时服务团”,爸爸为该团的宣传部长,欧阳山副之。他们一面编印《抗日壁报》,秘密张贴各租界;一面深入难民区,慰问十九路军伤病员;同时组织劝募队为难民和伤员募捐。8月13日那天,日本飞机在上海“大世界”扔下炸弹,战时服务团正在那里募捐。炸弹在怀孕六七个月的妈妈身边爆炸,所幸没有伤着。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随着上海战事吃紧,9月5日,爸爸、妈妈奉组织命令撤退内地。同行者有任白戈夫妇、沙汀夫妇、丽尼夫妇、舒群、杜谭、黄田及他的小女儿。由于上海到南京的铁路桥被炸,火车走走停停。目之所及都是争相逃难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杂乱而无序。出发前为安全计,要求每个人轻装,不能因个别人而拖累整体。尽管如此,兵慌马乱中还是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差错沙汀花两块钱让挑夫扛他的衣箱,拥挤中衣箱被拐跑,沙汀急得坐在铁轨上哭骂龟儿子。后来发现丽尼提的箱子是他的,原来两个箱子相似,情急中错把丽尼的箱子交给挑夫。妈妈晚年对我们说:“舒群挺憨厚的,一路上的苦活累活像扛行李什么的都是他。一次生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黄田的包袱给扔了。其实黄田带的东西并不多,黄田也不分辩,自己捡起来了事儿。你爸爸脾气上来不得了,他分配杜谭在车下看行李,他和舒群往上扛行李。结果杜谭挤去抢座位,你爸爸跟他火了。那时候同志之间毫无芥蒂,深了浅了并不记恨。大家都不容易。”
爸爸和舒群从上海出发前计划由南京北赴山西战场,祖母专门为两个年轻人各缝一个大大的行军包。在南京的下关,爸爸与祖母和待产的妈妈分手。她们去不了前线,只好投奔爸爸、妈妈在武昌邮电局当邮差的老舅崔紫祯。身怀六甲的妈妈上船时差一点被蜂拥的人群挤下江中,幸亏祖母一把抓住她。她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腹中的婴儿、肩负的背包,累得她双腿发软、眼冒金星。若不是一名船警跑来帮忙,婆媳俩连身背的包袱也解不下来。
此时,任白戈、沙汀回四川。爸爸与舒群住南京的平津流亡学生同学会。在那里遇见荒煤和北平来的金肇野、师田手、李墨林、何佶(吕荧)、刘天达(雷加)、白晓光(马加)等。在同学会,爸爸一面等待北上交通恢复的消息,一面帮助同学办同学会的小报。这期间,华汉(阳翰笙)通过荒煤约爸爸留下编刊物,爸爸没有同意。事后他说拒绝的理由有二:“一是个人被‘打回老家去’的热情支持,决计去山西前线参加抗战;一是在上海对他被捕有许多传闻,而究竟如何不甚了然。”随后,大同失守,北上火车不通。又兼何去何从无人负责,特别是身上的钱几将用尽。当然,只要留下办刊物立即就可以摆脱经济上的窘境。但是,半个月后爸爸还是毅然去武汉。从上海撤退时组织关系在沙汀身上,沙汀的南去使爸爸失掉党的关系。
追寻心中那片彩虹
爸爸到武汉后旋即与聂绀弩、丽尼创办文艺半月刊《哨岗》。《哨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0月16日正式出版。此时由上海到武汉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多,《哨岗》不啻是抗战后武汉进步刊物的开路先锋。从山东大学高兰教授保存至今的一本创刊号,可以多少了解一点当年条件的艰苦及他们因陋就简的创业精神。为了快速地配合抗日宣传,更因为那短缺的纸张,杂志没有封面,只在首页的右上角由罗烽手书“哨岗”二字为刊物的名称。三个人配合得很默契,稿源也充足。第二期有柯仲平、白朗、赫公等人的文章。发稿送审后却得国民政府汉口党部“不准印行”的通知,就这样《哨岗》被封杀了!
在《哨岗》面世前夕,胡风亦于10月1日来汉口。罗烽、白朗、丽尼、绀弩同去看望胡风。谈及正在筹创中的《哨岗》,胡风希望他们停办《哨岗》,和他共编《七月》-以免分散力量和稿件。并说已得到友人资助,经费无问题。当时,爸爸考虑《哨岗》系小型战斗性的半月刊,以刊载杂文、通讯、报告及漫画之类的小文章为主,恰好与大型文艺月刊配合战斗,遂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