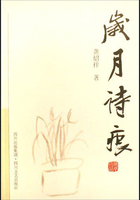精神的存在有待一双精神的眼睛去发掘。果然,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更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庞大身影无处不在,至今仍力图主宰人们的心灵。如果说我一开始便看到了“真”,那么现在就时常感到“善”和“美”的包围了。在市中心广场附近,有一长方形的巴罗克风格的古建筑,已是褐绿色,屋顶上的青铜骑士雕塑群像,一个个跃马昂首,伫立于苍穹,别有一种古风余韵。这建筑是马西莫歌剧院,建于十八世纪初,曾是欧洲第二大歌剧院,地中海最大歌剧院,因上演维尔第的歌剧,名重一时。真所谓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它是这般老迈、式微,但人们并不遗忘它,它周身围满脚手架,据说因经费原因,修修停停已多年。我注目良久,眼前幻化出薄暮时分,华灯初上,穿着夜礼服和百褶裙的贵族男女纷纷步入剧院的情景,他们之中,也许有痴恋烧炭党人的少女法尼娜,也许有《牛虻》里的亚瑟和琼玛,也许还有皮兰德娄讲述的凄伤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手捧西西里柠檬的青年密尔库和思断情绝的乡村女歌手苔里娜,一种沧桑之感忽地涌上我的心头。但歌剧艺术并未在意大利稍衰,至今仍是人们最喜爱的,与足球共称意大利人的两大骄傲。我想起国内为振兴歌剧呼吁多年,成效甚微,倒是赵本山们的“小品”畸形发达,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民族欣赏习惯的差异,还是文化境界和审美水准的距离。其实,何止歌剧?作为古罗马文明的故园、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意大利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无不精美绝伦。在这些方面,巴勒莫与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即便如此,你仍会深深感到,这里是黑手党的渊薮固然不假,但它更是艺术的王国,艺术精神已沁透了城市的躯体。看路灯辉映下的“羞耻喷泉”,你会为裸体石雕的美妙叫绝,抬头看山顶上残阳斜晖中的古堡,你会为历史的庄严神往,甚至在街角你看到老百姓自发地保护的一小块方尖碑,也会为人们珍惜文明成果的情操所感动。从本质上说,艺术乃是自由的象征和人类力图超越自我的表现,它具有天然的解毒作用。很难想象,一颗幽暗的罪恶灵魂或者一个只知数钞票的经济动物似的人,会真正倾心于艺术。
我们参观最多的还属教堂。尝听到有出访者抱怨说:“一天到晚看教堂,真没劲!”说这话的,可谓只知看热闹,不知看门道。意大利的教堂之多,决不亚于国内的佛寺,所不同者,佛教在我国已近衰落,而天主教虽几经变迁,教廷对教义的阐释虽迫于科学的发展一改再改,但它作为精神象征的地位并未改变。一个人从生到死,哪件大事能离得开教堂呢?教堂不仅是精神堡垒,而且是搜集艺术珍品的殿堂,它倒是集认识、教育、审美功能于一体。我常在想,倘若没有教会这块沃土,西方艺术还能如此绚烂吗?反过来说,没有艺术魔力的张扬,宗教的神圣感和神秘感还能如此久长吗?为了提高宗教的感化力,各种艺术家们真是殚精竭虑。蒙特利教堂的穹顶画也许还不算最有名,但那巨大的耶稣的一双永远追踪着你的勾魂摄魄的眼睛,会让你颤栗。且不同的角度耶稣有不同的神情。新的科技手段也开始进入教堂,如复杂的现代声光设备代替了管风琴。在一教堂,我们想细看壁画,苦于光线不足,经人指点后将五百里拉硬币投入一黑箱,只听咔嗒一声,立刻光明大放,一室辉煌,可惜好景不长,刚到两分钟,它就很客气地熄灭了。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队队儿童在教堂里围着牧师听讲的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或阶级教育展览会的情景。看来,他们的“思想工作”也抓得挺紧。我注意到,各教堂都设有多座“忏悔室”,那是个小木屋,三个门,中间是教士席,有小窗通二厢,教士安坐中央,可倾听跪伏者低诉自己的罪愆。记得我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钱单士厘(晚清人),在她的《归潜记》中也曾详述“忏悔亭”的形状,所谓“中室与旁室不相通,惟有铜网一小方(亦有以不透明玻璃代者)漏达声浪而已。旁室无门,无座位,有小几,为诉忏者跪久倚手之用”等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忏悔亭倒毫无变化。我没见到一个人忏悔,便怀疑它是否已沦为观赏物了。但据罗贝塔说,自有人忏悔,但要在指定时间进行,她又笑着补充说,是不是真心忏悔、毫无隐瞒,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印象最深的是建在海岸高岩上的罗萨尼亚教堂。罗萨尼亚是位女圣徒,十二世纪人,终身不嫁,把一生献给慈善事业。我看到她的一尊卧像,周围撒满了供奉者的钱币,她的神态既痛苦又甜蜜,似正进入一种“神圣交感”的境界,与贝尼尼塑造的圣女苔列莎很相像,确有股令人既惊讶又感伤的力量。听说她最灵验,类似中国的海神。我们看到神台下堆放着一些旧轮胎、铁锚、救生圈之类,不解其意,经打问才知道,那是海上遇难的水手有幸苟活下来,奉献给她的。更奇特的是一面大墙上,挂满了银制的人的各种器官的影型,举凡手、脚、心、肺、肾、眼睛、耳朵,应有尽有,如挂了一墙小首饰。原来是病苦之人为祈祷解脱痛苦而奉献的。究竟是病愈后的感戴,还是病苦中的希冀,就不得而知了。
在教堂外的台阶旁,我们见到一个乞丐,是一中年男子,穿粗呢西服,样子不怎么褴褛、可怜。地上铺一张纸,经翻译,知道上书:“请帮帮我这穷人吧。”我想此人堪称心理学家,因为他能抓住人们步出教堂心情激动的瞬间化缘,但那盒子里的收获似乎并不丰盛。王宏甲热衷搜集民俗,就要抱住乞丐的肩膀合影,但相机出了故障。谁知这乞丐竟示意我上卷并扳动一小部件,果然障碍排除,照片拍成了。如此乞丐,倒也罕见,我们不禁面面相觑。
出了教堂,在一海岬上,我们看到了罗萨尼亚的另一尊铜塑像。她面对大海,一手高举十字架,一手紧握权杖,神色冷峻,狂风刮起她的长发,不复那尊卧像的温柔。我定定地望着这位狂风中的圣女,刹那间似乎明白了许多。任何一个民族,要在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前行,就必然有它的文化根系。精神动力和宗教信仰,这些东西沉埋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虽然时移事迁,它那基本的框架却不会改变,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不会绝灭。
第三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当晚十点去参加一直等待中的蒙德罗文学奖授奖仪式,这也是我们此行最主要的活动项目。会议在哪里举行,将出现什么情景,我们都在心中暗暗悬揣着。汽车又一次路过炸死法官的现场,又一次穿过火树银花、光怪陆离的商业中心,终于在一座叫玛丽亚的教堂前停下来。我们有过各种猜想,但谁都没想到会在教堂举行。门口已停了很多车,男女警官林立,有的在用报话机联络什么,气氛似乎又紧张了。
但是,一踏进教堂,仿佛进入避风的港湾,我们立刻感受到一种高雅、温馨、安详的情调,似乎屋外汹汹的商品潮,抑或黑手党的阴影,全都远遁敛迹了。眼前确是一块超凡脱俗的空间。平时做弥撒的地方,摆上了观众席,主教大人的讲坛,成了评委们的座位。来人不少,约三百多人,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奖者,特邀代表,大多是当地的文化界人士。真没想到,这座动荡不安的城市,还蕴藏着这么多彬彬有礼的文人雅士。
蒙德罗是巴勒莫海滨一个风光迷人的小镇,文学奖即由此得名。自一九七五年设立至今,已历十八届。它设有处女作奖、翻译奖、意大利作家奖、外国作家奖、特别奖等多项,评奖范围是该年度的作品,对象则以本国为主,兼及世界五大洲,评委均由教授专家组成,旨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学繁荣。中国作家王蒙和翻译家吕同六,曾经获过此奖。这项奖的骄傲是,有四位获奖者后来或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据我国驻意文化参赞李国庆先生说,目前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文学奖,就是它了。它的发起人是兰蒂尼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兰蒂尼先生曾是西西里的着名法官,仪表堂堂,魄力非凡,他的热衷于此道,完全出自对文学的热爱。此刻,这位总导演静静地坐在一角落里,正心情激动地观看他操劳的成果的展示。
这确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发奖会。国内的发奖会,大都是领导出席,分宾坐定,然后宣读名单,获奖者鱼贯上台领奖状,再推举一名代表上台念发言稿,说些感谢领导、感谢评委,继续努力之类的套话,最后演些小品歌舞之类结束,未免板滞。这里则是由电视节目主持人手握话筒,全权主持仪式。获奖者上台后,当即有评委一人起立,宣读对其人其作的书面评价,并颁发证书。证书素朴大方,不见大红大紫或钢印图章之类,乃一白纸,除印上作品作者名字,下面全是评委的亲笔签名。然后主持人提问,获奖者即兴回答。由于获奖者的年龄、性别、个性殊异,常常妙趣横生,颇不单调。墨尔本的提麦因女士,研究但丁有成就,她却幽默地说“我没有研究但丁,我只是读但丁”,突出一个“读”字。台下报以热烈掌声,想必人们为她的谦逊和真诚鼓掌。那种不认真读原着的研究者还少吗?小说《十一月的飓风》的作者,捷克作家哈巴尔,据说名气不在昆德拉之下。他是个老人,一生经历复杂,受过不少苦,他不修边幅地倒披一件毛衣上台,站久了就自己搬一把椅子来坐,惹得台下爆出一片善意的大笑。我团代表杨牧,即席朗诵诗歌,他动作夸张,带表演性质,女上们不断掩嘴吃吃地笑,笑得我们心里发毛,生怕砸锅。原来这是文化差异所致,等到翻译了内容,台下的掌声又十分热烈。这里,不同种族、国家、肤色、语言的人们汇集一堂,却毫不隔膜,气氛是那么友好、轻松、活泼,好像有股热流在每个人心头激荡,那就是文学。不记得是谁说的:一个民族没有了文学,就意味着精神的死广。
梦幻般的长笛声轻扬起来,泉水般的钢琴声滑过了大厅,会上穿插的文艺节目,一律是阳春白雪,绝无杂耍闹剧的地位。我望着圣母塑像慈祥而严肃的神情,环视周围典雅的圆柱,穹顶壁画中翱翔的天使,听着仿佛只有天上才有的音乐,有种灵魂深深飞升的感觉。这哪里是一次普通的文学颁奖,这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次辉煌展示,是美的骄傲的炫耀,在这样一座不安的城市举行,尤其显示着文学艺术顽强的生命活力。
明天我们将告别西西里,前往罗马,那里会有更多的艺术瑰宝可观,但我仍依恋着这块神奇的土地。歌德说过:“不亲眼看看西西里,便不能透彻了解意大利。”西西里把传统与现代,古代英雄的美德和现代都市的罪恶,深固的家族观念与商战技巧如此奇妙地交错在自己身上。不是说它“变动最小”吗?这一方面固然是它背负着传统的沉重包袱,另一方面它又无时不以人性之光、理智之光反抗着物欲的压迫。再见吧,西西里,我此生大约无缘再踏上你的土地,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启示的。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日
12.听秦腔
我的一大爱好是听秦腔,爱听到了酷爱、入魔、自唱自叹、手舞足蹈的程度。到北京都二十五年了,这癖好居然有日甚一日之势,不免搔首自叹,这是否一种遗老心态?我曾宣称“秦腔是中国戏曲中最伟大、最深厚的剧种”,招来过一片讪笑和讥诮,却无愧无悔。内子是北京土着,小儿女都在北京长大,我每放播秦腔,便遭到他们的顽强抵抗,小女捂着耳朵跺脚尖叫,小儿涨红了脸摔门而去--破坏了他们要听流行歌曲的雅兴,那一刻他们甚至是仇视我的。然而,我的秦腔癖有如钢筋般坚固,最终还是我征服了他们。于今,妻子和女儿不但默认了秦腔的合法,有时还跟着节拍轻轻附和,只有小儿冥顽不灵,始终对秦腔不屑一顾,或暗暗冷笑。
我积有三十多盘秦腔磁带,北京固然大,无奇不有,我深信在拥有秦腔上我必在“首富”之列。这些磁带来之不易,每到西安、兰州便广为搜求,有时索性到朋友家里巧取豪夺。在西安,王愚、张素文夫妇是我的兄长辈,为我翻录、选录秦腔废寝忘食。有一回,王愚直录到鼻尖冒汗,脖梗上青筋噗噗地跳,他一面捶着腰背,一面说,达弟啊,也就是你,换谁我也不卖这个牛劲。李星和我年纪仿佛,又同好秦腔,对他我就不客气了,进剧场,跑商店,选磁带,每回必得陪同到底。我的那套《百名演员集锦》,就是花七十元托他搞到手的。在兰州,我和作家王家达一见面,话题马上就转入秦腔。在大学读书时,他是我研习秦腔的引路人。谈起名老演员如刘毓中、田德年、苏育民,我们感慨唏嘘,无限神往;谈起早夭的一代名伶苏蕊娥,《花亭相会》的婉转多情,我们轻轻叹息,不胜其情。我发现,我俩对秦腔名角都有种“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崇拜心理。尽管谁都知道秦腔演员的文化水平一般不高,有的还不乏俗气,但我们谁也不提这些,惟恐破坏了心造的圣像。等到我要检阅一下王兄装磁带的柜子时,融融乐乐的气氛就突变了。他局促不安,支吾其辞。毕竟是远道客来了,最后他还是慷慨解囊,送我一二盘市面已脱销的磁带。
说起来,某些西北人对秦腔的痴迷也着实叫人错愕。我有个侄子,比我还大两岁,是个八级钳工。记得小时候,他的床头就总有一摞戏本,至今他已四十六七岁,胡茬子都白了,多年不见,我偶翻他的床头,居然还是一摞戏本,令人怅然。听说“文革”前国务院有位主任叫贾拓夫,是陕西人,每天下班一进家门,双手把帽子往茶几上一放,咳嗽一声,便只说“秦腔”二字,家人便用老式留声机为他放秦腔唱片,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又听说,西北某大学学生宿舍,全是本地农村学生,只有一个南来的学子。这位江南秀士对秦腔深恶痛绝,秦腔声一起,他便溜出宿舍,到校园里胡转,孰不知他已获罪于众同窗,终有一天,为秦腔争论起来,有人逼问他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尖酸刻薄,众人大怒,挥动老拳,把这位秀逸之士打得鼻青脸肿。他爬起后到校方告状,校方惟苦笑规劝而已。这些传闻或有所夸张,但多年前在扬陵镇我倒是亲见,几个赶车的脚户哥儿,因春节期间电台的秦腔节目太少,蹲踞在车头上,朝着路旁的大喇叭吼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