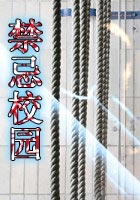按照北方的习俗,结婚时间由两家商定之后,还有一个正式议程--送日子。由男方派媒人,带上礼品和经星相家选定的最适于婚嫁的上上黄道吉日,正式通知女方。送罢“日子”便只剩下到了吉期,派花轿抬新人了。
由于韦家希望早日完婚,杨家“送日子”便紧跟在下聘之后。大喜的“日子”选定在七月初六日--七月七“天河配”的前一天。这是牛郎织女跨过天河相会的日子,恩爱夫妻一载长别,终于盼来朝思暮想的佳会之期,织女姐姐总要高兴得痛哭一场。难怪每当到了七月初七,十年有九年,总要飘洒下几阵织女的热泪。
有时,那泪雨头一天便开始飘洒不止。而婚嫁大事,最忌讳的是下雨。“老天发愁,夫妻不到头,大不吉利。那样的天气,万一让谁家碰上了,虽然当场极力做出欢乐的样子。但婚后的夫妻,连同双方的家长,亲朋好友,多少年同,心里都结着一个疙瘩,捏着一把汗。担心着不定什么时候,“夫妻不到头”的预言会成为现实。所以,韦王氏一听说程半仙选定的“上上大吉”好日子是七月初六,便极力反对。不料,惜玉小姐却说:“织女姐姐盼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盼来个一夜团圆,笑还笑不赢呢,怎会哭?那眼泪明明是人家高兴得笑出来的!”
“这小祖宗,啥事也跟旁人格路!我不昝啦--随她去!”做母亲的无可奈何,只得服扶。
这样,杨月楼与韦惜玉成婚的大喜之期,便定在了今天--同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
新租来的婚房座落在同仁里,是一个四正三偏的独院。散发着油漆气味的大门上,已贴上了大红洒金喜联。“柳暗花明春正半,珠联壁合影成双。”横额是:“天作之合。”从大门望进去,一架长春藤遮住了东侧半个院子,西侧则是一株粗大的合欢树,花盛期巳过,一束束羽毛似的残花,仍飘出阵阵余香。丹桂戏园和同乐戏园的“文场”和“武场”自告奋勇,做了今天的喜乐队。此刻,正在长春藤花架下,起劲吹拉敲打。那远远听蓟的喜乐声,正是他们吹奏出来的。
院子正中,安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已经摆好了香案,烛台,三牲,十盘,和十个大面供。新人到来后的“拜天地”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正房门上贴的喜联是:“凤管悠扬彩凤至,玉笙高吭金龙翔,”横额是。“举案齐眉。”
粉刷一新的正房客堂,已经布置得金碧辉煌。正北墙上,悬着一幅红地飞金大双喜中堂,两边的对联也是粉地金字。三面墙壁上,悬满了闪着缎光绸彩题着各种吉祥庆贺词句的喜幛。其中,有曾历海和丁少奎合送的,也有戏园老板及陈宝生等人单独送的。
洞房设在客堂东间。挂着大红熟罗帐子的罗汉床,以及长几,扶手椅,梳妆台,方杌等一应家俱,都是新买回的。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通常所说的“嫁妆气味”。新人到来之后,将在这里坐床,吃宽条富贵面,喝交杯合卺酒。然后共度洞房花烛良宵。
起轿迎新人的时刻到了。乐队吹打着,跟随着披红插花的新郎官向外走去。一乘彩轿,一乘官轿,已经停在弄堂口。八名轿夫侍立在轿两侧。他们头戴喜帽,身穿绿布短褂。前后心各绽一幅有着飞马图案的圆补子。等新郎官坐进“官轿”内,领班的喊一声“起轿”。在喜乐的前导下,两乘轿子便沿着宽阔的长街,向女家所在地安乐里走去。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辟为租界以来,沪人结婚的风俗逐渐仿效起了洋人。如。坐花轿,改为坐亨斯美马车,将四轮生风的马车,用彩绸披挂一新,也很时兴风光。但杨母在北京生活惯了,不喜欢那些时兴玩意几。所以,今天的婚礼,原封不动都是照着北方的风俗办事。
安乐里距同仁里不过二里之遥。不到一个钟头,欢快的喜乐声,便把两抬花轿引回同仁里。王妈和韦家南邻的当家女人,充当了伴娘。两入搀扶着新娘子从花轿内跨出,跨过搭着长串制钱的马鞍,在新郎的带领下,踏着“铺毡童子”铺在沿路的大红毛毡,慢慢来到了新居院中。然后,在赞礼官陈宝生的高喊下,拜天地,拜高堂,入洞房,吃合卺酒--完成一整套繁琐的仪式。直到撒完“喜钱”分完喜饽饽,新婚大礼第一阶段,才算告一段落。
今天的婚宴设在离同仁里不远的“十味香”。杨家是在客居地,除了戏班同事,无亲友来贺。韦家虽然久居上海,但主人多年在港穗经商,沪上常常来往的客人并不多。所以,今天的喜筵,只摆了四桌。等到盛宴结束,客人先后告辞,以丁少奎为首的一帮戏班年轻人,便涌进了新房。开始了让新娘子既难堪,又头疼的“闹喜房”。
闹喜房又叫闹洞房,不知哪朝哪代流下了这风俗。新婚头三天,不分辈分高低,远房近支,连叔公公、大伯子,也都有了抹下脸皮跟新娘子大闹一通的权力。取闹的花样,更是由着性儿,花样百出。可以问不该问的话儿,只要不伯脸红;可以撤臊,说出任何平鬻当着人面不该说的脏话儿。至于摸新娘的油光头发,柔嫩粉面;扯过嫩笋似地细手,捏搓一阵子,更是家常便饭。如新娘子使出冷脸子,表现出一点儿不耐烦,惹恼了闹喜房的刺儿头,还会吆喝一声,抬起新娘子撂几个高儿。据说,越闹腾的厉害,主人家越高兴。闹红(哄)闹红(哄)嘛!只有往舞里闹哄,不但婚后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脾气再暴烈的媳妇,被这一闹,也会变成棉花团似的小羊羔几,柔性儿。但是,对新出嫁的姑娘来说,闹房这一关,实在比新郎官吹灯上床,解她的纽扣,都不知可怕多少倍。“合情合理”地作践人嘛!所以,一到了闹房这个时刻。新娘子不论在娘家脾性是刚烈还是柔顺,个个吓得缩成一团,躲在床角,红着脸,下巴抵在胸“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今天,闹房的人一拥进喜房,个个不由一惊。他们见到了异乎寻常的情景。新娘子已经卸下凤冠霞披,只见她,上身穿一件软缎单褂,腰扎细折长裙,头上斜插一支株花--打扮得淡雅俏丽。她不但没缩在墙角,垂头缩脑,等侯哄闹。而且一见人们拥进喜房,竟腾地从床上跳到地下,恭恭敬敬地往新房礼让。然后,把已经斟满热茶的十几只茶碗,先敬给丁少奎一杯,然后一一敬到闹房人的手里。进来的人多,茶碗敬完了,便打开红漆描金木匣,捧出各种蜜饯,果点,往人们的手中塞。
热茶在手,果点在“的闹房人,原先想好的俏皮话,恶作剧,一时都被热茶、甜点,堵在嗓子眼里,使不出来。新房巾竞出现了少见的冷清场面。领头的丁少奎,正要想个点子,开口取闹一番,不料新娘子忽然退回到床沿上坐下来,秀美的明目,茌众人的脸上掠一圈儿,然后朗朗说道。
“我真高兴,大伙儿都来祝贺。今天台面单薄,请诸位多包涵。没上席面的朋友,请多吃点果子,多喝几杯茶,也算是杨家的一点心意。”一席话,俨俨是主妇的口气。说到这里,她站起身来,捧起茶壶,又给端杯的人斟满杯。放下茶壶,又分了一圈果点然后退到床侧,继续说道。“月楼在上海临时安家,举目台面-!海人称酒席为台面无亲。凡事还要大伙几多关照、帮衬。这里,我替杨家先谢谢大家。刀说罢,她恭恭敬散地敛衽施礼。
邪不压正。新娘子彬彬的礼仪,完全遏止了粗俗的混闹。书惜玉竟是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女人!人们不由地点头敬佩。
经常闹喜房的人都知道,有个别缺乏耐性的女人,一开始尚能极力忍气吞声,听凭闹房的戏谑,胡闹。但后来往往克制不住。以致使出冷脸子,甚至日出粗话。更有的,手抓脚蹬,大伤和气。结果,闹房的甩下一连串骂声,忿而离去,落得家里人永远埋怨新娘子失礼,不懂事。韦借玉却是用礼貌的招待,驱走了必然发生的哄闹。结果,挤满新房的闹房入,或坐或站,尽管后面有几人站上了板凳,但没有一句混话,粗话,更没有人动手动脚。从始至终,只开了几句轻松的玩笑,有人竟谈起桌面上茶具的质料,有人评论梳妆台的式样。有人甚至领头赞誉起新郎官的高超戏艺。两三个钟头下来,闹洞房完全变成了文文雅雅地饮茶吃点心,漫话谈心……
临来洞房之前,杨太太曾经悄悄嘱咐丁少奎:“媳妇年纪轻,脸皮薄,千万护着点,别让大伙闹得太出格儿。打现在看来,不但没出格,人人一本正经,反而显得太冷清,实在不象个闹洞房的样子。于是,他想出了个题目,站起来高声说道:“喂,大伙光这么漫卢细话地闲扯,太没意思不是?我告诉大伙个秘密,别嚷,听我说。新娘子不但会写诗,填词,还会唱词牌。她写的一首叫做《点降唇》的曲儿,别提多好听啦。现在,让新娘子给大伙唱一唱,好不好呀?
丁少奎抖出借玉在求爱信中的词牌,想出个难题,让新娘子脸红红。不料,惜玉一听,立刻站起来,羞涩地一笑,答道:“丁老板的提议我接受。不过,唱得不中听,大伙剐见笑。炒她望着丁少奎,诙谐地说道:“丁大哥是顾曲行家。要求你不要见笑小妹--行吗?”
韦惜玉左一句“丁老板”右一句“丁大哥”弄得丁少奎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只得含糊地应道:“行是行,不过还得再唱唱《西厢记》里《酬柬》那首,叫做什么,成就今宵欢爱,魂飞在九宵云外才算完。”
“好!”众人一齐喝彩。
惜玉微微颌首。略一定神,便轻启朱唇唱了起来:昼永夜长,柔肠一寸愁万丈。数叩参商,奈何勾魂枪。红氍曼醉,雷动巴掌响。莫辜负,春嫩花娇,楚楚春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