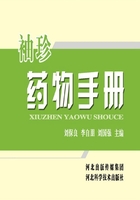我想向公众朋友们提个倡议。这个倡议很简单,只四个字便可以说清。这个倡议就叫“拒绝足球”。拒绝踢足球,拒绝看足球,拒绝谈足球,新闻媒介拒绝宣传报道足球,从而,将足球这个奇怪的玩意儿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剔除出去。
“这圆圆的、黑白相间的、装着一肚子气的玩意儿叫足球吗?”每当看见足球,我就常常作如是之想。我的这个句式是一则外国幽默给的。萧伯纳在公园里散步时,与一位绅士狭路相逢。绅士挥舞着手杖,指着萧伯纳头上又破又旧的帽子说先生,你头顶那破烂玩意儿,能叫帽子吗?”萧伯纳听了,微微一笑,他也挥动手杖,指着绅士头顶的那件华贵时髫的帽子说先生,你帽子底下那圆圆的玩意儿,能叫脑袋吗?”
足球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痛苦。远的不说,单从北京“五一九长镜头”开始,我们那脆弱的渴望虚荣的心就遭受了多少次打击,我们的脸上一次一次落下多少无情的耳光。城头变幻大王旗。那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的脸,每一张脸带给我们的都是痛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依次是:曾雪鳞一一高丰文一一施拉普纳一戚务生一一霍顿。
5·19之夜的第二天,已故的作家路遥曾经给我谈起过曾雪麟。他说那戴着金丝眼镜、扎着花领带、西装革履的曾雪麟,是个伪博士、假学者。那一次屈辱的失败深深地震撼一广球迷,据说事后男人们寄去了自己刮胡子的刀片,女人寄去了自己的头发,请曾教练自裁以谢天下。路遥作为球迷,虽然狂热,但毕竟深沉很多,他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嘟嚷了上面两句。
我所以想起这事,是因为前不久在电视上,见曾雪麟侃侃而谈九强赛,猛然想到不久以后的1月17日,就是路遥的七周年忌日,于是,因曾雪麟而路遥,因路遥而曾雪麟,想起这些事。
高丰文长着一张诚实的脸,他说起话来也是朴实无华。我一直喜欢他。他好像取得过几场胜利,但是最后还是在关键场次上,以失败而告终。也许他那一阵子,中国的球员队伍处于低谷吧。失败了的英雄。
施拉普纳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热情、诚恳、幼稚。鬼使神差,谁知道他怎么执上中闰闰家足球队的教鞭的。他对足球的理解还处在幼稚园水平。不过下野之后,他为自己找了份工作,这就是经销“施拉普纳牌啤酒”。施大爷终于知道中国足球的致命伤在哪里了,这就是缺少日尔曼民族的那种酒神精神,所以他像个盗火种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拿来德国的啤酒卖。可惜这时他已下野了。
戚务生那张晦气重重的脸,一开始就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十强赛那一摊队员,是经过职业联赛锻炼的中国踢足球以来最整齐的一茬球员,可惜这些球员耽搁在他的手上了。十强赛失败之后,看到戚务生离开国家队后,又去掌武汉美尔雅队的教鞭,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真是健忘和宽容,日本和韩国,他们的教练冈田和车范根,曾经把队伍辉煌地带到法兰西,仅仅因为在法兰西赛场上表现不佳,便被视为民族罪人,弃之如敝履,并被规定十年内不准去沾足球。现在我收回我原先说过的话,中国毕竟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度,总得给这个戚指导一条生计之路吧。况且,败军之将尚可以言勇,戚务生还是有一套的,先是美尔雅保级成功,后是云南红塔冲上甲人。一霍顿是个好老头。他成熟,努力,顽强。当然,他也固执,自负,愚蠢。中国足球是他的牺牲品,他也是中国足球这个祭坛上的牺牲品,彼此彼此而已。九强赛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太极推手与约翰牛之争》。韩国人暗算了霍顿,韩国教练员在场上玩的那一套叫“十人太极推手”,东方哲学的产物。记得当时看电视实况转播时,我就暗暗叫苦,明白霍顿要栽了。东方哲学那一套,霍顿毕竟有隔,南韩国旗上那太极阴阳图,霍顿大约并不明白那怪模怪样的东西是什么。软中带硬,一推一送的太极推手,终于制服了怒气冲冲、心高气傲的约翰牛。霍顿饮恨,英雄有泪哪!一一霍顿走好。
这几张面孔,像翻挂历上的美人图一样,让我将这几年的中国足球历历数遍。岁月可以消磨一切,火气大了会致病,因此让我们宽释和谅解一切。包括对曾雪麟。我所以在这里语言有些刻薄,纯梓是因为想起老朋友路遥的缘故。他已作古,永缄其口。我有责任将他当年的愤怒在这里写屮?由视卜寿曾雪鶊曾雪鶊也去了
想想我们真可怜。可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球迷。那么这个球迷,不做也罢。
当然还有比我们更可怜的,这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些足球节目主持人。他们因为职业的原因,不幸与足球结缘,这就注定了他们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上帝的弃儿的表情。他们得没话找话说,得强按住自己的难堪。九强赛最后一场,费健翔说了一句话“只有有勇气的人才能看这一场球。”这话叫电视机前的我潸然泪下。这些年轻人很有才华,博学又有现代意识。比如黄健翔,比如师旭平,比如张斌,比如刘建宏。看到他们在电视屏幕上旁征博弓,口吐莲花,我常常悲哀地想,如果让他们写小说,肯定比我写得好。面对中国足球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他们不该浪费那么多的唾沫。
拒绝足球吧!没有它,我们的耳根可能更淸静一些,我们的日子可能过得更舒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