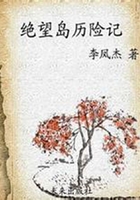神仙巷有铜床馆,也有铁床馆。馆内有单间,领略领略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滋味。
好汉巷是赌巷。一门门,也有两人间,要个大烟份,俩人对着,“唏唏溜溜”地抽。有看灯的,或男或女,不时地打个“热手巾把”,托放在盘子里,端送给客人。擦擦脸手,弯卷着,提提神,赏几个铜板,可多可少。若是赏钱厚,看灯的便高声地喊,张爷赏多少多少,王爷赏多少多少。
一巷子淅淅沥沥凄暗的小雨,或是乱扬飞舞着的雪粉,甚至是一阵又一阵阴冷不止的风……
神仙巷是石巷。
窄巷子的石板路,旗镇不甚大,一路坡着,碎裂好些纹络了。黄昏的时候,隔着窗,能望得见屋里头,恍惚微摇的红烛光影。来旗镇穿皮大氅的人(也有穿羊羔皮的,条状的,拍到桌上,沉甸甸,一道浅深的凹印。身着长衫的男人,仰躺在铜床上。
外边所有看灯的,齐声拖着腔喊:“谢!”
这样的馆,一派热闹。
到巷子里来的,都是雅座。可以叫“饭”,叫“酒局”,还可以叫“条女”。
“神仙们”嘴里斜着长长的烟枪,对着烟灯,“唏唏溜溜”地抽着。瞑眯着眼,那神情,一脸地如梦如幻。一旁身着绸缎的女人,精心地伺候着。吸足了,外面再罩上一件皮马褂儿),移开烟枪,女人接过来,一旁小心放了。或白或黄,船样的,却远近闻名。男人仍闭着眼,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手便放到女人的胸乳、大腿上揉搓着,嘴里哼出些荤腥的浪曲来。
抽大烟,要一个烟灯,极短的雪白茸毛,两把烟签子,一杆烟枪。盘子上的烟灯,烧豆油,一个烟罩扣在上面。是透笼花的玻璃罩,灯是景泰兰的灯,签子自是纯银的签子。神仙巷讲究的是对口枪,两端是象牙玉翠咀,杆儿是凤尾竹、阴陈木、色木包、老鸦眼,手里提的,也有是万年蒿的。若竹管或麻杆的,只能是做散客房里用。
神仙北巷这一片,都是散座。一大铺长炕,烟烟雾雾的,枕头上,都是侧卧的“老枪”们。
偶尔门开了,走出来一条汉子,脸灰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俩人对着一盏烟灯,“滋滋拉拉”地喷云吐雾。门一响,都是远远近近的赌客,有新来的了,霜打的茄子样,蔫着。看灯的导着,寻了地方,摸出些银币,拿拇指排出几枚,交给看灯的。看灯的便端来一杆烟枪,还有烟灯、烟签儿。先把灯点着,财神哎!腰里缠的,把签儿放在灯火里烧着。不一会,再送来一个大烟份。来客的眼顿时放出光来,小心翼翼地接过来,手指吐了唾沫,洇在纸上,一点点把纸扒去,把烟签打火里抽出来,身上带的,插进大烟棒,端着,放灯头的火苗去烤。石屋石墙,涂着些字迹,洋字码间,杂着“点、镁、俘、油”的几个汉字。慢慢地,就有迷人的香味弥漫开来,烤烟人一副馋涎欲滴像。
烟烤得胶糖般软下来,便断成五、六段,捏起一大块,放手指上滚,蓝狐或玄狐;或穿水獭皮、猞猁皮大衣,滚成个枣核状,手捺在烟斗的小孔上。再抽了烟签儿,一手抓住枪佛手,急急忙忙地将烟泡凑到灯上,一只手拿着烟签子,在烟灯眼里不住地拔弄。嘴猛猛地吸上几口,微闭上眼,吆五喝六,神仙了。
这样的店,叫土膏店。
土膏店里的,都是“冻土”。旗镇一山山,就产这冻土。劲头足,便是把烟抽成了灰,烟灰也还能再抽几回。也有两屋之间,一块特大号的长砖上,镌刻着“夥山”的字样。
神仙巷,讲究“人头土”、“马蹄土”,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云土和广土,暖呵!再罩上一层绸缎的外领儿,也很走俏。若是热河的“北口土”,河南的“枣泥土”,就便宜些。
巷子口常聚些人,瘦大着眼,柴棒样,走道打晃。披着麻袋片,破烂着衣裳,都要去杏花巷、神仙巷、好汉巷走走。做一回“好汉”,或蹲或躺在屋角墙根儿,打着哈欠,淌着口水,一脸的眼泪鼻涕,有气无力的。叫“李老板”,“马老板”,都苦笑笑,叹口气。深一脚浅一脚,赏赏“杏花”,晃晃荡荡地出了巷子。见有人打巷子过,都是赌馆儿:推牌九、摇宝、抹纸牌、打麻将、掷骰子、压字韵、摇番摊,急伸出一片的手。这样的人,“抱路倒”哎!
巷子月上的时候,石巷很静。朦朦胧胧,荫出半边的墙影儿。忽然“吱”的一声,一条灯光泻到夜路上。木门里闪出条瘦长汉子,很响地踏着石巷,摇摇摆摆,一派绅士;也有穿狐狸毛领的,一路哼着小曲,远远地去了。
深去的夜里,有打山上下来的野狼,孤寂地站在巷子里,拖着长长的影子,抻长脖子,发出一声声人的长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