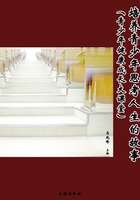雪说化就化了,天又融融地暖热起来。
七、八个人,聚了老榆树底,矮板凳、木块、大石头上坐了闲谈,打着盹儿。石头凉,把帽子摘下,垫铺上,便不再觉得硌得荒。
老树底聚人。
从夏到秋,福寿老榆树底下,人不断。
大热的夏天里,树荫浓重,树底便歇着好些人。荫凉下躺着睡觉,闲坐。歪斜着的,暝眯眼半睡的,也有摇着蒲扇,把几片凉风,赶来赶去。或下意识地,凭感觉,把落在脸上的蚊蝇拂走。
直等到日头斜开,畏缩的树影,再一次地渐渐长大,树底的人便精神起来,揉揉眼,抻抻脖颈,敞开怀,开始谈天说地,五候十六国起来。
朱掌柜常老远望着想,人天生就是爱聚堆的东西!不然,哪来的这屯子、这镇子,还有城市?赓先生说得有理,人这玩意儿,吃饱了,睡足了,睁开眼晴要看,张着耳朵要听,鼻子要嗅,脑袋要想,然后就说出一大堆混怅的话来。许就惹下一场横祸,叫人直是后悔不迭、捶胸顿足,悔青了肠子。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唉,沉默是金!
天乍冷,待稍一暖和,也还是都凑过来坐会。
有人正说得唾沫横飞:
“麻子大帅来的时候,是坐着火车,打西北来的。人老鼻子了!连车顶上都满是人,架着一挺挺地机关枪。那会儿,卢胖子镇守在这,闹叛乱,奉天就派麻子大帅带着兵,前来镇压。卢胖子有一千多人马,埋伏在道两旁。火车开得慢,打西达山弯处拐过来,瞅得清,都是兵,连车箱顶都架着机关枪。
卢胖子的兵见了,立时吓破了胆,爬起来漫山遍野地跑。麻子大帅一弹未放,便俘虏了卢胖子,收了旗镇。
麻子大帅的兵,其实只有一个营,三、四百人,空着车箱,只虚张声势,兵全爬到了车顶上。卢胖子一听就昏过去了。直叫他悔掉了牙,往肚里头咽……
这事叫人说烂了。人阴阴阳阳瞌睡成一片,东倒西歪,在大树底摆出一幅街头风景。
一个人挑着担柴,远远而来。看得出,是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不时地放慢步子,倒换下肩,掀起衣襟儿抹把汗。
树底有人瞅着说:
“烟客又送柴来了。不忘本,这人忠厚哩!”
“哎,好人无好报!弄得家破人亡,这世道。一双儿女,至今也没下落,怪可怜的。”
“听说那小姑娘,是叫人卖到窑子上了--”
两大蓬柴禾,小山样,晃晃悠悠到了大树底。有人喊:“放下歇歇吧!”
柴禾间露出一张褶皱的老脸,冲树底笑笑,瓮声瓮气地说:“不妨事。”
脚步仍是未停,没人高的两大蓬万年黑老扫苕,梢子枝枝丫丫地挑一片薄籽,打一树底的脸前幌过去。
岔过道,一直挑到了朱家铺子门前。
一落地,一些细碎的树叶细枝便震落到地上。柴靠着墙斜放了,人脱出来,满头满肩的扫苕枝叶儿,扑拉扑拉,进了铺子的门。
伙计“小南方”正在柜台里看啥,抬了下头,见是烟客,又低下去,继续看他的书。烟客冲着后屋叫了声:“大哥在屋没?”
烟客的山东味极浓,大哥的哥字,便叫成了“锅”。
一个女人应道:“你大哥进货去了,过两日才能回来。”
“嫂子,俺给捎来一担柴,有水没?”
女人打后屋出来,舀着大半瓢水。“这么远的道儿,多沉。家里还有烧的哩!”
烟客隔着柜台接过来,放到嘴唇上,仰起脖,“咕嘟”“咕嘟”一阵喉咙响。一些水溜儿,顺着脖子直往下淌。
好一阵,才把水瓢拿下来,一大瓢水,竟空剩了几滴,亮晶晶地挂在瓢沿上。
瓢放上了柜台,烟客抹了把下巴,推开门,打柴禾里拎出两只兔子来。
深秋的“山跳子”,肉乎乎垂着。青灰色,一身的绒毛,只颈上深勒着一根细亮的铁丝,提在烟客的手里。
小南方头“霍”地抬起头,两眼顿时放出光来。
“今早套了俩“山跳子”,顺便提了来,给俺大哥补补身子。生意上的事,累心哩。头场雪后的毛,都是绒毛,给俺大哥缝个坎肩,挡寒!”
女人接过兔子,不大好意思地说:
“别老惦记着你大哥。山上活累,你也别舍不得吃!天冷了,下回再来,把棉袄棉裤带来,我给你把棉花翻翻。”
“嗯。俺把柴禾挑到后院去。”烟客的话里,依旧是透着一股山东人的犟劲。
烟客是朱掌柜打草垛里救的,那夜一场清雪,又刮了半夜的西北风。朱掌柜大早起来抱柴禾,救了打鸡毛店被撵出来,已冻得半死的烟客。
大树底的一群,望着烟客远去的背影,一个正抽烟的老头叹道:“好人唉!”
“傻子!”半靠在树上的瘦长汉子说:
“买卖人,谁信谁是傻子!脸上笑嘻嘻,打一肚子骗人的鬼算盘!”
“别瞎说,朱掌柜可是个好人。”
“爷们儿!我二溜子不算个好人,却不瞎说。他这店是咋开的?”二溜子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边说着话,边不停地挤咕眼,像是在像哪个做着啥暗示。
一树底的人都不在意,知道二溜子天生的毛病,一说话眼就挤咕个不停。
“那是他爹的事,和他没啥关系。”
“没他爹能有他?这铺子越开越大,不赚人钱,是气吹起来的?我就不信这爷俩个比鸡巴,不一个吊味?”
老人叹息说:“赚不完的钱,过得完的年!”
二溜子突然住了嘴,半躺的身子,忽地一下直起来,眼珠儿直勾勾再也不转,只定定地去瞅。
街上走来个小媳妇,泥花着脸,傻笑着,掩不住那一笑就露出的俩浅浅酒窝儿。穿一件大襟的花棉袄,胸饱满地圆鼓着。肩头一大块破着口子,散着棉花,竟露出一块雪白的肉来。二溜子的眼神,被直勾勾地粘了去。
不知谁喊了声,“疯子!”
“你才是疯子!”小媳妇突然变了脸,冲那说话处恶了一个大眼白。又笑起来:“俺有钱了,有的是钱!俺有两支大元宝,嘻嘻。”
小媳妇怀里抱着两大块砖头。突然看见二溜子,一脸的惊喜,朝着二溜子走过来,一直走到跟前。一树底的眼都瞅着,叫二溜子有些惊慌起来。
“俺到处找你,你咋跑到这里来了!快跟俺回家吧,有钱了!”女疯子话说得柔柔的,叫二溜子简直忘掉了是疯子,骨头都要酥了。
“你看这两个大元宝,能买甜心饼、买金戒指、买毛大氅--”突然就一松手,两大块砖头,全砸到了二溜子的头上。
二流子疼得“妈呀”一声尖叫,一个高蹿起来,两手抱着头,没命地远跑。
一树底的人一惊,按着“哈哈”地笑成一片。
女疯子怔怔地呆一会儿,突然捂着脸哭起来,“俺的元宝来?俺的元宝来?”
蓦地冲向那刚才讲大帅的磕巴汉子,厉声吼道:“你还俺的元宝!”
那汉子吓得转身爬起就跑,树底下的人也都一哄而散。
女疯子坐到地下,“哇哇”地哭起来:
“还俺的元宝!还俺的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