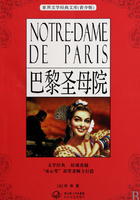原来这二先生是瓷器行家,二先生在潘家园一走,不说话,只是把某件瓷器多看两眼,拿在手里摸摸,立时这件东西就被人们认作是俏货,不惜大价地买回去,买回去后,假的也成了真的,因为是二先生看过的。所以,一帮人就悄悄地跟定了二先生,二先生到哪儿,他们到哪儿。二先生是机灵人,心里自然明镜儿似的,在市场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似随意,其实有心,至于和摊主们有什么猫儿腻,外人是难以揣测的。这回,二先生倒好像很认真,临出“荟古斋”还回过头来,嘱咐老宋再仔细看看碗沿。
广东买主已经把价提到了一千五,老宋还是说碗不是他的,他无权做主。其实金瑞就在他旁边坐着,他完全可以和金瑞商量,但他偏偏装得和金瑞没有关系一样。金瑞呢,也不言语,坐在那儿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把个屋里熏得烟气缭绕,呛得人眼睛发辣。发财从来没见他爹一下抽过这么多烟,他不知爹今天是怎么了。他想,既然这是个仿制的不值钱的假货。能卖出一千五就已经是大大地赚了一笔,纵然老宋从中要提去不少,但那比撂外头一块钱俩也划算多了,甚至比来时商量的一二百也翻出去了几倍,爹不发话,人家老宋自然不敢贸然做主。只好这样推了。广东人一咬牙,说愿意出两千五。老宋拿眼睛扫了一下金瑞,金瑞无动于衷。发财咳嗽了一声,金瑞瞪了他一眼,又抽自己的烟了。
老宋对买主说,您既然真喜欢这件东西,我就经心给您留着,不卖给别人,这期间我得跟货主商量,看人家到底卖不卖。要卖是卖多少;这么着吧,您明儿来,我一准给您个准话儿。广东人说他明天一早就来,带现钱来,又嘱咐这个小碗无论如何不能摆在外头,得给他留着。老宋一一答应,总算打发走了买主。老宋回头对金瑞说,金爷您也看见了,货在我这儿不愁卖不出去,您这个近代仿制的假定窑,让二先生这么一过手就是两千五,明天我再往高了要,那小子也肯掏,那位整个儿是个还没开眼的“博傻”。金瑞说,我看出来了,您的二先生是个托儿。老宋说,也不完全是托儿,二先生的眼力没人能比,到底人家是专家,搞了一辈子陶瓷研究的,光书就出过好几本儿。
发财说,爹,咱那碗要不就搁宋老师这儿?
老宋说,金爷,您要信得过我就放这儿,我尽着价儿要,要下来,您拿三,我拿四,至于那个三……老宋再没往下说,不言而喻,谁都知道是给二先生的了。发财说,我们这头儿少了点儿,别忘了,东西可是我们的。老宋说,您这东西可是个五毛钱不值的赝品哪!今天是你们爷儿俩在这儿坐着,里里外外都让你们看见了,我才说给你们分三,要搁别人,我十块钱收购,就已经是出了大价儿了,要那样我赚的是七!发财心里的小九九一转,想三千的三也是一千块了,一个要扔的小碗,让人捣鼓两下就能赚一千,还行,就说,爹,我看咱们就全都交给宋老师得了。老宋说,我祖父跟您家老爷子也是世交了,我肯定亏不了您哪!
金瑞站起身,从老宋手里拿过小碗说,既然是个假的,卖也没多大意思,我想,还是拿回去盖咸菜坛子吧。老宋听了说,别价,那可是糟蹋了。发财也说,爹,您别犯迷糊。平时您老稀里糊涂的,这会儿您得醒醒,您不能眼瞅着钱从手底下溜过去。金瑞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睡醒?发财说,您看看您干的事儿!金瑞说。我干什么了?这碗是我爸爸给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算。老宋说,您爷儿俩别争。回去商量商量也行,我也不是非要挣您这份儿钱,我这儿的买卖多着呢。发财说,这还有什么商量的,明摆着的嘛,早知道您这样,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
金瑞把碗装到黑兜里,对老宋说,谢谢您了,这半天您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改天我请您上家里喝茶。老宋说,东西是您的,您再好好儿掂量掂量,要是卖,您就来找我,要是不卖也常来走动走动,有什么好货别忘了照顾我。老宋话是这样说,那张脸分明已经变了色儿,煞白,这使金瑞想到了刚才听到的“雨过天青”这个很独特的词。
金瑞出了“荟古斋”,却并不急着回家,背着手在潘家园转了几个圈,发财在后头跟着倒显得十分被动。发财说,爹,您既然不卖,咱也别转了,回去吧,没劲!金瑞也不说话,还是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地看过去,后来在一个卖杂物的小贩那儿花五块钱买了个放大镜,才对发财说,回家!
回家的路上。发财把车开得一蹿一蹿的,几次差点儿把金瑞的脑袋撞到挡风玻璃上。金瑞说,你甭跟我来这套,你就认得前段家河刘改民家的糙碗,你懂什么!发财一踩油门,汽车猛的一声吼,代替了发财的愤怒。金瑞说,你小子没发现,那个姓宋的一边儿说咱们的碗是假的,一边儿紧攥着不撒手,生怕跑了似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那个二先生要用放大镜看碗沿儿,姓宋的推说放大镜找不着了,就没让他看,我想这里头准藏着什么怕人知道的机巧,什么叶家哥俩的仿制,那都是说给我听的鬼话,其实他们俩都明白,这个碗是真的。发财说,就算是真的,人家也没给咱们按假的卖,也没亏了咱们。金瑞说,这个碗到底是怎么个物件,我心里得有底,我不能为了眼前的一千块钱就把十万丢了。发财说,一个小碗,还十万呢,您做梦去吧!金瑞说,你别说。我还就真爱做梦。
据王玉兰说,金瑞从潘家园回来以后一改往日的慵散性情,变得勤奋好学起来,弄来个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一头扎到书堆里,整天看书。我问看什么书,王玉兰说是陶瓷书,说不单看书,还去找过专家,去烧窑的地方转悠,一天到晚忙得鬼吹火似的。我说,钻研陶瓷比睡觉好,你就由着他去吧。王玉兰说,一个碗还拿放大镜瞅,细致得不行。我问金瑞看出了什么结果没有。王玉兰说,有了放大镜,咋能看不出来?啥都看出来了。
真还不敢小瞧了金瑞,他竟然辨认出了那不起眼的小碗是个了不得的器物。
金瑞借助放大镜,终于弄清了碗沿上的两个字是“枢府”。搞清这两个字的过程是金瑞苦苦钻研的过程,那是个很奇妙很引人人胜的过程,是金瑞以前从没体味过的兴奋和幸福。“枢府”是唐代的一级行政机构,宋以后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改枢府为枢密院,元以武力为重,“枢府”权位就更高。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将有“枢府”铭的卵白釉作为“枢密院”的定烧器,特点为小底足,厚胎,素釉失透,色青白,铭文“枢府”两字印在器物内壁口边沿下,“枢”和“府”地位相对。因为元代不过一百年,故而烧制数量极为有限,有铭文者就更寥寥无几。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后人将这类瓷统称“枢府瓷”,后代虽都有烧制,但样式已改,釉也不润,那有数的元代“枢府瓷”,便成了绝品。
金瑞弄清了小碗的来龙去脉,心里如同九月的蓝天,清亮、透彻,思路亦清晰无比。元代的枢府瓷比宋代的土定虽然晚了二百来年,但无论从质量,还是从历史价值上看,土定都是与枢府无法相比的。金瑞想,他的父亲拿着它去要饭,恐怕也只是看中了它的破旧,它的暗淡无光,看中了它与叫花子身份相称的外形,而绝不知道它的稀罕背景和连城价值。当然,也不乏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父亲知道这个碗的底细和珍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韬光养晦,匿影藏形,使之能够真正存留下来。金瑞想,真要是这样,他父亲的心思真是深沉得不能再深了,真要这样,他又该如何评价他那位放浪形骸、佯狂避世的父亲,又该如何体会他的真心呢?金瑞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所谓多走几步,风光无限,他突然觉得世界变得很复杂,生活变得很凝重,他惊奇长期以来自己充耳不闻的昏沉和得过且过的浮漂,在漫长的五十余年生涯中,竟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一问题,作为儿子,他是非常非常地不孝了。
发财的思路还在潘家园老宋那儿,给老宋递了话,老宋说要真是枢府瓷,可以开价三千,但必须是真的,有专家鉴定书。依着发财和王玉兰的意思,三千足可以了,跟白捡的一样。金瑞却有金瑞的想法,他想,这个小碗之所以能留到今天,自有留到今天的道理,决不是为潘家园那样的地方准备的,是奇珍就要上到奇珍的档次,正经的应该上到国家级的买卖市场。拿到国家级的拍卖行去拍卖,那价格就不是三千了,几万、十几万都能炒上去。金瑞把这话跟发财说了,发财这才明白了爹的心思,就跟金瑞突然佩服了他阿玛的深沉一样。发财也突然佩服起他爸爸的精深韬略来,到底是大宅门儿出来的,从思路上就比他这后段家河黄土里钻出来的高了一筹。
金瑞经过别人介绍,和北京一家有名、有信誉的大拍卖公司--惠德拍卖公司接上了头,将小碗拿去让人看了,提出拍卖的底价不能低于十万,保险金额三十万。拍卖公司说必须有鉴定证明书,并且是权威的鉴定证明书,还要经过公证处的公证;又说,这个鉴定人可以由物主自己找,也可以由拍卖公司代找,鉴定费用则全由物主出。金瑞问鉴定这个小碗得多少钱,公司说根据物品的价值而定。金瑞回来算了一下账,就说是十万吧,鉴定费提成十分之一就是一万,卖出去十万了给他一万没说的,要是卖不出去,人家也是不会给你白鉴定的,那里外里不是还得往外搭?跟王玉兰一说,王玉兰也认为是这么个理儿,说太划不来。当时王玉兰的脑子不知怎么一转,就想到了金瑞的三大爷。我们家的老三舜錤在文物部门工作,是资深的文物鉴定专家,让他给鉴定一下当是没太大问题,到底是自家的嫡亲三大爷啊,这手到擒来的事儿对专家来说真是算不得什么的。
发财也说娘的主意好,当下就让金瑞拿着碗去找三大爷。
金瑞却很犹豫,他不知道三大爷肯不肯帮这个忙。他明白,发财和他娘是以农村人的思路来考虑这一切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同宗同姓血脉相连,有事当然是互相帮衬,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要不怎么叫亲戚?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宅门儿里的亲戚关系,不了解那笑脸背后的烟雾之深。这个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他的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不是亲情,而是冷漠,这是金瑞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不能说清的一种情愫,也是他在京城随时感觉到孤立无助的茫然和清冷的原因。是的,在金家,他永远找不到“世间最难得者亲兄弟”的认同,他永远是一个人,连他的梦境也是一个人踽踽独行。亲朋无一字,欲言无予和,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孤单是不是就是当年他父亲的感觉呢……
金瑞的迟疑被发财认为是优柔寡断,是谨小慎微,他觉得怎么着现在他也姓了爱新觉罗,从户口、从法律上他也是金家的一分子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替他父亲做主,这是用不着含糊的事实。于是,他背了金瑞,拿了小碗,来到亚运村请教他的三爷爷金舜錤。
我前面说过,我们家的这位老三在金家弟兄之中是个脾气很各色的人,不苟言笑,冷气逼人,在单位里、在兄弟姐妹中都颇没有人缘,难得有谁去登他的门。发财不知深浅地去了,保姆就让他在门厅里等。保姆说,金先生在午睡,三点以前不会客。发财说他是金先生的侄孙,是亲戚。保姆说甭说侄孙,就是亲孙也得等,金先生的觉是雷打不动的,搅了金先生的觉,那就是天塌下来了。
发财听了只好在一进门的地方等,那保姆连客厅也没让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