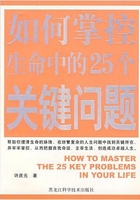接下来便是我的忙,忙着剪辑,忙着后期配音,我没有时间再想到金瑞,想到北京城里我众多的亲戚们。离京的前夕,我在摄影场地又见到王玉兰,她正化装成义和团的模样夹在众人之中,见我路过,一把将我拉住,说是找了我好几天了。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是为金瑞的事。我问金瑞怎么了,是不是又犯了病?王玉兰说要是犯病就好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闹腾,搅得家里吃不好睡不好。我问金瑞究竟在干什么,王玉兰说在打官司。我问跟谁打,王玉兰说跟三大爷金舜錤打。我问是不是三大爷把他告了,王玉兰说是他把人家三大爷告了。我问为什么,王玉兰说,他让三大爷赔偿三十万。我听了吓一跳,问什么东西值这么些钱,王玉兰说,就是那个碗,小白碗。我问哪个小白碗,王玉兰说,就是扣腌菜坛子的那个小白碗……
有些事情一旦脱离了它的运行轨迹就变得很离奇,变得不可恩议,变得让人听起来有点儿离谱。这样的事情大约也只有在金家才能演义得出来吧。在那深沉的背景下,在那摸不清源头的干枯河床里,随着时间的流逝,难保不裸露出几个出人意料的故事,让匆匆而过的人们驻足、审视,为之一惊。
还应该从我那天去看望金瑞说起。
我走后,那对夫妻为那些浆水菜的辩论一直在延续,这似乎成为了他们那几天的争论中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话题论一论也是一场愉快。大有大的话题,比如巴以战争的态势;小有小的话题,比如腌浆水菜的必要。大话题有大打,用上了坦克和炸弹;小话题有小打,这就使那坛子浆水菜连汤带水飞出了屋外--按事件的比例来说,其威力也不亚于一个中型炸弹。坛子碎成了几片,多年的陈汤,浓而酸冽,渗进当年“细雨”亭下的池塘遗址,一窝酸芹菜如同残败的荷梗,在院落里散出了“穷秋九月荷叶黄”的诗意。王玉兰于万分悲痛中,将那些散落在院中的菜连同那个摔不烂的糙碗敛起,拿到水池边清洗,想的是敛起的菜或许还能吃最后一顿陕西浆水面。菜洗净了,碗也洗净了,王玉兰坐在桌前将碗用抹布有一搭没一搭地擦拭。现出真面目的碗白得发污,并没透出多少细致和珍贵来,这使王玉兰更加思念外面那个已经破成几瓣的菜坛子,这个碗作为盖坛的器皿是再合适没有了。擦拭中,王玉兰感到碗沿内侧有两处瑕疵,以为是没泡下去的脏迹,使劲抹了几下,才发现那瑕是凹进去的,隐隐约约像两个字,两个字并不挨着,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显得有些怪模怪样。
王玉兰把碗拿给金瑞看,让金瑞辨认,金瑞迷迷糊糊地说,爱是什么是什么,你管它呢!王玉兰说,这大概是两个记号,你忘了,前段家河刘改民屋里烧的碗就打记号。改民是在碗底打上一个三角,十里八里的一看那三角就知道是改民做的,错不了。金瑞说,这个记号也是改民那样的工匠打上去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个世界,除了我以外,谁都有点儿名利思想。王玉兰说,这个做碗的人也怪,他怎的偏偏在碗沿儿上打记号,也不怕硌嘴?金瑞说,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王玉兰不知怎么的,对碗上那两个符号一直很上心,没事她就抱着碗琢磨。金瑞见了说。你跟真的似的,能看出个屁!王玉兰说,能看出个屁来也不错,我就怕连屁也看不出来。金瑞说,你就是看出来是谁做的又怎么样?你也不能找他去。王玉兰说是不能怎么样。她就是觉得碗上这记号的位置太怪,由不得她想知道是谁干的这笨活儿,比改民还笨。金瑞说,你也是吃饱了撑的,有那工夫躺那儿养养神儿不好吗?
王玉兰不甘心,拿着碗让胡同口开小饭铺的孙大爷看,王玉兰想,孙大爷是卖饭的,小铺里碗多,他那些碗里也说不定有一两个记号打在碗边上的。但是孙大爷看了半天,也跟她一样,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认出两个字其中一个是个“府”字。孙大爷说,一定是哪个府里用的碗,看这糙模样也是下人用的,不是上台面儿的东西,不值钱。
王玉兰是个有心计的人,她回来以后就让金瑞找行家看看这个碗,说,说不定是个文物。金瑞说,你也知道什么叫文物?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咱们家,除了我以外,没有一样是文物。王玉兰说,碗上这边这个字是个“府”字,人家孙大爷都认出来了,是“府”就说明有年头儿了,有皇上那会儿才有府。这个碗八成儿是有来头儿的。金瑞说,这是我爸爸要饭用的碗,当然有来头儿。王玉兰还在没完没了,她说,究竟是什么府呢?还是应该搞清楚啊,姑爸爸上次来就死盯着这碗看,说不定她已经看出了什么,不是还让你把碗好好收着吗?经王玉兰一提醒,金瑞也想起来了,他把碗从王玉兰手里要过来,又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终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王玉兰说应该找专家看看。金瑞说他不认识什么专家。王玉兰说不妨让发财托托人。金瑞说,就那个伪觉罗?蜜?傻×一个,还不如我呢!
嘴说伪觉罗?蜜是傻X,但在王玉兰的鼓动下,金瑞还是跟伪觉罗?蜜去了北京有名的文物旧货市场潘家园。金瑞的大驾所以能起动,全凭了发财那辆客货两用的半大“丰田”,让金瑞自个儿挤车去,打死他也不会干。
潘家园的市场逢周六、日开市,列肆一片,人群熙攘,有天不亮就赶来的,图的是能憋着俏货;有到夕阳西下才正经在市场上转悠的,为的是能捡点儿收摊前的洋落儿。日中之时,市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万千人拥在一个大场子里,有男有女,有中有西,人有三六九等,话有地北天南,热热闹闹似开了锅一般。摊贩们两溜儿摆开,摊位上铺子里,商彝周鼎、秦镜汉玉、晋书唐画、宋瓷明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晃人眼目,让人痴迷。有贩主席像章、主席语录、红卫袖章、草绿军装的,有贩旧饼干筒、旧水烟袋、旧马蹄表、旧相片的,有贩粮票、布票、邮票、工业券的,还有贩玻璃项链、塑料手镯、人造玛瑙、仿真象牙的……俯察品类之盛,物件之杂,实难一一说得清。金帛珠玉,异宝奇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给。卖主漫天要价,买主就地还钱,乍看好像真买真卖,细看则是在慢慢切磋交流,不能排除不少人不是为买货,是为开眼、为长学问而来的。
金瑞紧跟着儿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天很热,市场的大棚里很闷,脸上油汗直冒,嗡嗡的人声使得他浑身发软,脑袋发闷,眼睛一阵阵冒金星。依着他的本意。是想一切交给儿子去办,自己找了个凉快地儿歇着,但儿子非得拽上他,说这样的事得他出面才压得住阵,就凭他家的背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现在已经挤进来了,要再挤出去就得费同样的劲儿,没办法,金瑞只好亦步亦趋地追着发财的花绸衫,半步不敢落下。他的心里真是后悔极了,后悔听了王玉兰娘儿俩的撺掇。赶来凑这个热闹,本来在家待得好好儿的,这是何苦!金瑞手里提着黑人造革提兜,拉链坏了,兜口半张着,一望便知里头没有什么值钱东西。这样的兜在北京已经不多见了,搁在卖水烟袋什么的摊儿上说不定也能当古董卖出去。黑兜里头搁着那个白碗,出门时王玉兰把它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了,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多包几层也显得咱们的东西珍贵。但金瑞把那些报纸都扯了下来,他嫌沉。说光一个碗就够他提的了,还要鼓鼓囊囊地加上那些纸,白费劲儿,他已经有日子没干这么重的活儿了。王玉兰想说什么,终是没说,她对她的男人了解得太透彻了,她没有办法,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就跟当年我父亲对老五没一点儿办法一样,她是彻底服了。小碗在黑兜里随着金瑞的步子一下一下地晃,爷儿俩在车上就商量好了,倘若这个破碗真是件东西,能值个一二百的,出手也就算了,卖了碗顺便上建工市场买点灰,借着好天把几间北房抹抹,那房一下雨就漏得厉害。要是一分不值也就一分不值了,随手一丢也就丢了,用不着再往家拿。
凭着儿子手里的纸条,爷儿俩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叫做“荟古斋”的小铺子,较之外面的小摊相比,这个铺子多少还算正规一些,一间门面,打横一个玻璃柜台,三面墙是三个大博古架。玻璃柜台里摆着汉玉佩件、象牙雕刻、绣品软彩、绝代古瓷等精致小件,博古架上则是钟鼎錞爵、秦砖汉瓦、唐的三彩俑、明的宣德炉,一派的古色古香。掌柜的姓宋,精瘦。脸发青发黄,没有表情,也不抬眼看人,听伪觉罗?蜜说明了来意,半天不吭声,只是用一块绸子使劲儿擦一个小罐儿。金瑞想找个地方坐下,转了俩圈儿,没找见椅子,也没地方靠,就势挨着架子蹲了,他实在是累得很了。掌柜的说了,这位您留神哪,您旁边这个陶罐可是陕西成阳汉墓才出土的,昨儿刚收来,两千多年的东西了,您别让它毁在我的铺子里。金瑞一听,赶紧站起来了,不敢轻易举手投足,生怕再碰了什么“两千年”。
发财借机会递烟,叫了几声“宋老师”才把盖坛子的碗递过去,让人家“帮着看看”。掌柜的老宋漫不经心地接过碗。掂了掂,弹了弹,又用手指抹着碗边转了一圈,直摇头。金瑞看老宋这架势不像鉴定古董,倒像是在瓷器铺里挑碗。就有些看不起他。老宋问金瑞的儿子究竟让他看什么。儿子说看看是哪个朝代的东西,值不值钱。老宋说,这还用看。清末民初的客货,明摆着的。金瑞问什么是客货。老宋爱答不理地说,都告诉您了我们吃什么呀!金瑞赔着笑脸说,我是真不懂啊,自家的一个小碗,上头有俩字儿,觉着新鲜,求您门里人给看看,要是真算得上文物。就势儿就搁您这儿了,搁我们家也没有用。老宋听说有字,从兜里摸出个放大镜,对着碗沿照了半天,末了放下镜子也没说什么。金瑞问,您看出是俩什么字儿了?老宋说,您看出什么字了?金瑞说,其中一个是个“府”字,那个看不大清楚。老宋说,我可连“府”字也没看出来。
发财不甘心地追着问,宋老师,您说这客货是不是从海外来的瓷器?老宋说,还海外呢,是咱北京地道的土产,明白告诉您吧,专供内廷宫里用的瓷叫官窑,老百姓用的叫客窑,官窑出的瓷器就是新的,就是年代不远的也值钱,客窑的东西,就是您撂它三百年也大子儿不值。就您这碗,甭说官场,连饭庄里头都不敢用。发财说,敢情,八成儿是我爷爷从哪个卖炒肝的摊儿上顺手顺来的。老宋问他爷爷是谁,发财不想说。吭叽了半天说,解放前就死了,反正您也不认识。老宋说那不见得,说他曾祖父最早是翰林院的庶吉士,跟林则徐是一个品级,到了他祖父就专搞古玩买卖了,琉璃厂的“荟古斋”就是他们家的铺子,老北京只要是有名有姓的人家儿,没有他们家不知道的。金瑞儿子说,我们姓爱新觉罗。老宋说,这么说是旗人了,那您怎么称呼呢?发财说,单一个字,宓。老宋低头思忖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这辈分是怎么排的呢,奕、载、溥、毓……启……没有“宓”呀,您这辈分再大也大不过咸丰去呀!金瑞说,什么觉罗?蜜,都是小孩子家赶时髦的胡诌!看得出来,我今天是遇上真人了,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实话实说,我们家姓金,在东四九条住,我父亲叫金舜锫,这个碗就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老宋点头说,怪不得,这就对了……”打您爷儿俩一进来,我就觉着不凡,果不其然,是金舜锫金五爷的后人,我这岁数虽然没赶上瞻仰您家老爷子的风采,那名声可是早就听说过了。
老宋一改刚才的冷淡,变得热情又多话,也不知从哪里拽出个凳子,拉着扯着让金瑞坐。金瑞巴不得歇着,也没推辞就坐下了。老宋抚着那个旧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金家在北京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儿……金瑞说,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几间破房,还是落实政策以后发还的。发财的心思还在碗上,他问,宋老师,您看这碗……老宋说,要是你们金家的东西,我还真不敢掉以轻心,得好好看看。说完就把柜上的一个小灯打开,把碗拿到灯底下仔细翻转了好一会儿说,粗看像是宋代定州民窑烧制的土釉,细看便看出了后人的仿造痕迹,这个碗早不过光绪二十五年,晚不过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这五十年之间的事儿。发财说,这么说这个碗值不了多少钱。老宋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这得看搁谁那儿,你撂外头地摊儿上,一块钱买俩,你放我这小玻璃柜里,当真的宋瓷卖,不带含糊的,出手就是一千。发财说,您不是说是仿造的吗?老宋笑而不答,拿眼睛扫金瑞。金瑞虽然人爱睡觉却并不糊涂,早已窥出老宋的心思,反倒变作了老宋初时的模样,沉着脸不说话了。
老宋见金瑞不表态,便说,说白了,干我们这行的,有真金不怕火炼的本事,也有炫玉贾石的机巧,要全是真的,天下的文物商人得喝西北风去!卖主儿有卖主儿的行路。关键是看买主儿识不识货,您买了西贝(赝品)只能自认倒霉,别处都有打击假冒伪劣的,惟独文物市场没有,您用真价儿买了假货,是您自己没长眼,没本事,犯不上跟卖主儿较劲儿,您越较劲儿,越丢人,所以,这倒腾古董的压根儿就没有退货这一说。出手了就是出手了,就是赚了,出不了手就在这儿搁着,十年八年,东西还是东西。飞不了也坏不了,干文物买卖就有这点儿好处,用我们的话说是“三年不开市,开市顶三年”。跟您说吧,我们收到俏货不容易,能找到有钱的买主儿也不容易……
正说着,从门口踱进来一个人,高个儿,虚胖,说话带点儿假嗓儿。老宋管进来的人叫二先生。二先生看见老宋手里的小碗,接过来把玩了一会儿说,像是土定。但釉色不对,土釉是老象牙白,白里泛黄,这个碗是死白,瓷也粗糙,像是仿制的。老宋说,二先生不愧是行家,一搭眼就看出来了,我刚才看了还有点儿犯蒙。二先生听了老宋的话,越发得意,卖弄地说,宋代五大名窑,柴、汝、哥、官、定,这定窑就在河北,离北京最近,所以北京定窑的东西相比较就多。另外,这种器皿出于定州民窑,数百年烧制又不曾中断。所以后代仿造甚多,真赝难辨。老宋说,当年我祖父在琉璃厂的铺子里就有不少土定,因大多不是宋代真物,价格都很低,那些东西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二先生说,民国二十年,北京东城老君堂叶麟祥、叶麟祉哥儿俩从日本留学回来。提倡陶瓷救国,办过一个“大华陶瓷厂”,用新法儿烧制了一批很不错的瓷器,也搞出了一批仿古瓷。可以达到乱真地步,其中不乏定窑土釉。
二先生说到这儿,突然打住了话头,用手摸着碗沿像是在寻找什么。二先生对老宋说,你这儿有放大镜吗?老宋翻了半天说,刚儿还在这儿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这时有人来请二先生,说那边有件“雨过天青”的美人觚,想让先生过去看看。二先生刚放下碗,立时就从外头蹿进来一个广东口音的买主,打听小碗的价钱,说不论多少,也要把这个碗买了去。老宋只说这碗不是他的,他不能卖。那买主还不依不饶地死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