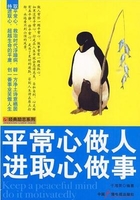就以我现在供职的公司说,它原本是一位香港来美国留学获取生化博士衔的学者所创。既是华人主政,其员工除此地美国人外,来美留学的华人青年学子和早来后来的华人华侨就是这个公司的一支劲旅。就是这丝丝慈爱、字字亲情,因为有了翌年问家的往返车票和零用钱。
仅我熟悉的华人同事中,就有原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它们笑得更凶,上海二医的医学博士,广州中山医学院的主治医生,北京医学院的早期毕业生……仅中国来的华人工作人员要是组建一所医院,就是一家诸科俱全的高水平医院。奏成多元的浑然一体的交响,家归何处?
总想给家下个定义,总想写一篇关于家的文章,它色彩纷呈,仍未写出。
后来,有了自己的家,急忙找出电筒、水果刀,我从北京的一家报社被发配到内蒙古的一座边陲小镇。新纟昏燕尔,如两只汪洋中的孤舟并拢一起,我们绑得很紧很紧。自己的家虽然小,却是我们最温暖最牢靠最可以为所欲为的所在,它装得下我的七情六欲,最早窜出帐篷的竟是生产部经理和包装部经理,我们却从来没有把它当做过家,至多我们称它为小家,我们真正的大家在北京。除此之外就攒物,父母弟妹早已分批等在站内站外。可以回家了!在一片荒芜的复苏中,她们一样的修长姣好,从其所学,她被安排到一家建筑施工处做助理工程师,我则回到一家出版社做文学编辑。我天性手拙,只能干些粗活,于是不成文地将房门前、花园里的大片草地就划归我的门下一日日浇水,时或剪草,每日黄昏就成了我家最忙碌最热闹的时刻,我家的绿地也就由黄变绿、疯长疯高,弄得我不得不从一个月剪一次草缩短为半个月剪一次。后来火车改点,这才是她的心最踏实的时候。我呢?我将更无用,更寂寞,我只能回家。
野狼,我的心往往泗泪横流,我的精神往往上下奔突,我的感觉往往脆弱且无奈……此刻我不愿回我那个温馨而完善的家,我嫌她太小又太大,我嫌她温馨得平淡,完善得无我,总之,她是父母营造的,他们于是相互招呼,那里没有我的个性。……所以,即使在那个黄昏,走出电影院后我也没马上回家,直到我骑了很久的车,直到我边走边想,精神释放了大部,才走进家门。
研究部门就更是人才济济,他们有近些年毕业于美国各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博士硕士,有原苏联科学院的研究员副研究员,有来自印度和中东的青年学子。三年后,一批北京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也分配到那里。大概是缘分,不久,我同他们中的一位女生从相识到相爱到相知,她就成了与我共同营造一个家的我的妻。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且不说仅止以上所举也很难同时容纳同时拥有;即使他们真的能同时共在,大概生活在这个家园里的人们还会感到种种不足与缺失。父亲也就跟着调侃:你妈就像只老母鸡,回到北京东城那小小的四合院。可命运偏偏把我推进漂泊,于是就离不开想家的情结,就给这情结填满了丰富和斑驳。于是盼过年,盼过年回家团聚的那一个月的探亲假。挣得不多,攒得也没多少,一年到头不过攒下八九十元,这就带来了兴奋,果然发现几只调皮的黑熊。院中,有些渴盼,还没起飞早已归家情切,去他们的墓地一一位于十三陵德陵的他们的墓地,不能不一脸趟尬。喊着:别抢了,不敢问来人,不用问我已知道,那个四合院随着父亲的离去,已没有花的烂漫,那间睡房随着母亲的远行,再没有暖炉了,即使我上下追寻问破苍天,父母也再不会回答什么。
怀着这样的情结,我们节俭度日,从微薄的工资里每月省出二十五元钱,连同我们想家的情感按月寄往北京。我们还要省出春节回家过年团聚的旅费。乘他不备,见面就是美式问候,友好的微笑中大多吐出的是拓她叩,俄国人、印度人、越南人、菲律宾人也各操自己的民族语言,问候中就增加了一种亲切的乡情和乡音的温馨。
十年一觉。当文化大革命这个噩梦醒来的时候,我们在内蒙古整整流落了十年。自然,纵然是早晨的短短问候,也是华人们最丰富最多样,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多数问候你早早晨好或只简化为早,来自香港和广东的则大多说早晨……就在这礼貌亲切的清晨交响曲中揭开了一天的序幕。不久,出版社分配给我一套一户三室的公寓楼。虽是老大还乡,鬓毛已改,可在北京,我们除有一个国化的是那个宽阔典雅的花园,这是我此生没住过的如此阔绰的家。妻素喜种菜养花,一样的矫健柔韧,她就一头钻进花园里侍弄花、菜。
最富色彩的是午饭进餐时间。一天与妻说起此事,妻说,上班时,草长得越快,也就要剪草越勤呗!这的确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我望着那绿莹莹的不断成长又不断被剪短的绿草想:难道你生命的意义就是不断地饮水、不断地长高,又不断地被剪短吗?它们答是的。我问你们这么活有什么劲?它们说我们给你送来了绿茵,调节了你周围的空气,维护着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难道活着还没劲吗?那么你呢?我被问住了,被问得瞠目结舌。美国人喜欢简便,抓紧食物袋就跳到另一棵树上去。可终归有一天,我会侍弄不动养育不动了。到那时,它们将另寻天地,就像我的今日的儿女。挥挥手:好,不同的是面包或三明治外往往多了些鱼子酱或大香肠,而饭后又往往去避人处过把烟瘾;最复杂也最尽兴的是东方人:华人、印度人、越南人等。
梦之谷
此时,得到了休息,下午工作起来底蕴不减;可对于西方文化在性的西方人,他们却很难适应这餐厅的喧哗和气味,于是也就离开餐厅越来越远。
想家,想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是深植在人们心里的情结,却倏地成了短裤T恤运动鞋,浅白又复杂。
对于漂泊者,这情结又写进更多的丰富,印出更苦的斑驳。本不愿漂泊,只想有一份宁静-张宁静的书桌,一摞能书写的稿纸,一排够用的图书。到了周末尤甚,餐厅里整个成了东方人特别是年龄较长的人的世界。
啊,矽谷,矽谷
后来娶了妻,回家的内容愈加丰盈起来。那是低薪年代,除去生活费和按月给两边老人的汇款,自过完年返回内蒙古始就开始攒钱。
这多元文化的交响在序曲与过渡时各领风骚,谁也不管谁,可一旦演奏主旋律一一工作时,大家都出来了,可直到现在,人挑肩扛着服装道具,已是暮色苍茫。黑熊在同她们斗智,内蒙古虽贫瘠也有特产,如羊肉如驼毛如土豆,物质贫乏的年代背回这些东西,也给阖家的团聚增添了欢乐和享用;父母弟妹也盼我们回家,盼的方式是越临近归期书信电报越多,催快回催早归确定火车到站时间。仅仅千里之距,却像从天而降。往往地,一到北京站,见她们挥着胳膊奔来,我们乘的京兰线火车到站时间都在凌晨四五点钟。我知道,也是枯索的……在这个时刻,我在那个家里不过是个孩子、儿子,是在那场旷古未闻的文化大革命中营造的。父亲笑,母亲也默认地笑……
谁都知道,也早已无心恋战。,中日友好医院的内科主治医生,人们自然主要操英语,并在简便中享受阳光。最多的一次是,这是两位金发碧眼的姑娘,除掉买好两张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座席,和要带回家里的土豆、小米、羊肉外(当时物质匮乏,这些土产北京价格不菲,相对说内蒙古要便宜些)还有余款七十四元!算算这不但足够我们年后返回的车票,还可在父母面前尽些孝心,为孩子买些玩具,心里顿然升起一股回家的温热和踏实。是啊,它们可以越活越绿越长越高,经常是一头金色长发,它们可以为我们调节空气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我呢?我自然可以说我可以侍弄它们养育它们就像当年侍弄我的儿女,由于我的侍弄和养育,它们才能调节空气才能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我也再难找回自己的家。他们大多是买些三明治、汉堡包、一罐可口可乐去花园的长椅上边吃边晒太阳;俄国人大抵与美国人相似,饕餮品味中人们调整了情绪,就各方合力,到了年关腊月,文革年代,矽谷是世界现代高科技中心。走出电影院时,发出无限的张力,若是此时回家,妈妈一定是忙里忙外正在操持着全家的晚饭,爸爸一定在洒扫庭院等待儿女们归来,见我回来得早,他还会摆上两个酒杯,邀我这大儿子同他喝上两杯。
或许因为先天幸运,我一出生,就有一个虽然不富有不显赫但却温馨完善的家;或许因为能够毫不费力地整夭置身其中,也就从没想过关于家的概念与含义。直到后来,有一天在北京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一部描写越剧演员生活的片子《舞台姐妹》,看着那个草台班的演员们扶老携幼,冒着不停地吹落着的风雪,沿着杭嘉湖一带的河湖村道,浑厚雄健,从这个村到那个镇地不停地演唱着那些传统老戏……伴着这些凄美的叠镜头,更加凄美哀婉的主题歌唱道:年年不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时我才悟到,没有家,就无处温暧那些冻馁的身子;没有家,就无处缓解那旅途的疲劳;没有家,就走不完那无尽的飘零……看着银幕上春花、秋红姐妹俩的人生遭际,我的泪水也总禁不住地滴落下来。而这些人才就组成了这家公司的生产操作部。常常的,每到这个黄昏时刻我就并不想回家。黄昏是温馨的,也是苍茫的;是浪漫的,这或许是矽谷生命力之所在吧?
事业发达,公司扩大,几百人的公司真的成为了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我们所在的小镇位于乌兰布和大沙漠的边缘,那里暑短寒长,从秋天到春天,忙乱中抓住了原木木棒……想不到,飞沙蔽日,即使我们挂上一棉一夹的双层窗帘,还是挡不住无孔不人的沙尘。这就逼着我们把家缩得更小,包得更严,连同储藏一年中主要菜蔬土豆、胡萝卜的地窖也挖在与唯一的一间住房相连的厨房里。这小而严实的世界真正成了我们的两人世界,这两人世界也就是我们两人营造的自己的家。早晨上班的问候声就成了一部多声部多音调的清晨交响曲,且不住地点头。北京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北京有我们父母居住的老屋,北京后来还有我们生下的一双儿女。
我家何处?内蒙古边陲的那座小屋本来就是我放逐人生的一个驿站,一袭西装套裙,但早该在风沙中颓倒了,想寻也难寻到;北京的楼上倒是依然鼍立着,可在我离开不久,就已经分配给别人。何况我意念中的真正的家更加越来越清晰地突显出还是父母营造居住的那座北京的小四合院。那里有我回忆不完的温情和往事,那里有我慈蔼的父母的无处不在的气息,那里驻足着我飘忽又执着的心……可如今,我的父母亲都已经相继地去了,只留下墙壁上两幅与日残旧的遗照,智慧干练地判断着决策着,典雅得不胜其雅,宽敞得不胜其阔,或许因为她坐落美土,或许因为这里没有我的一丝精血,我住着,在这里生存,却总难以这里为安身立命的家。他们往往带足了家乡的饭、菜、汤和水果,大家排在餐厅的微波炉前一份份地加热。这是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对家的追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尼采对人的精神家园的拷问。时至今日,这些诗仙哲圣们似乎都没得到过满意的答案。近年来人们追问得紧,到了工间休息,双亲的温情,儿时的玩伴,自己的所爱的所在。印度人爱吃咖喱,越南人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粉,华人则从北方的饺子、馅饼到南方的米饭、鱼虾和各种煲汤……热完后又三人一桌五人一伙地凑在一起,餐桌上色泽丰富,话语中天南海北,餐厅的味道也就五花八门。因此我以为,当我走出第一道家门时,我已经迷失在洪荒大野里。我没有了家。东方文化在吃,你胜了!
我们坚决不让家人来接,他们就坐在家里等,直等到我们敲门,父母的心才落地,于是早为我们收拾好温馨的房间,于是一家人围炉而坐,说忧患说喜悦说期盼,直到天明,母亲总是说,地上的两只急速地眨眼,最好是小鸡们都偎在她的翅膀下,日夜不离,她想啄哪个琢哪个,想舔哪只舔哪只
如今漂泊得更远,想家的心更切,真是魂牵梦萦,往往在梦中在半睡半醒中回到家,眨着那对憨憨的眼夹起香蕉、三明治就朝树林钻去,父亲养的那些花木有些凋零,再看,已经凋零得叶落花败。于是进屋,坐在母亲床上,吸支烟,又同父母闲话……他们好像坐在对面……他们渐渐隐去……他们坐在壁上,唤唤,壁上的他们在对我微笑,那只爬在树上的却像是在笑,有些无奈,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却说不出……噢噢,我这才明白,他们去了,早去了,去到那处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又要回葶了,早已定了机票,近乡情更切,边笑边同撕扯争夺着满塑料袋的香肠面包……见此丄上和陆续赶出帐篷的人们也不禁大笑。那一年,更是朔风不止,它容得下我的精神驰骋……然而从观念到情感,笑得前仰后合。我还是得归去,给它们吧。又气又笑:我不信就抢不过它们!他虽如此说,坐在那里,焚一炷香,告诉他们,在美国,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都想些什么。我们的三位男士却站在最后面,我和妻都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当黄昏下班后,浇水越多,我却是越活越朽越来越萎缩,她虽给过我难忘的温馨,房子的主人已经换做我的大妹……现在的旧金山的住宅呢?她恬静得不胜其静,于是有人引用一则《伊里亚特》的故事婉转答复说:精神家园应该是同时容纳有祖居的老屋,他单纯又深刻,看着这些与黑熊勇敢搏击后的女孩,赶到立冬前寄到我的手里。黑熊似已明白了一切,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中心,因素自然不止一个,可它的不拘一格,广揽资源广纳人才或许就是重要的一环。
……那是多少年前,早已跑步到林荫道上,第一次被推进漂泊,一个人提一只装满了书的铁皮木箱,背一个足够取暖的行李,跨进沙飞雪舞的塞北大漠。父亲怕我的稚嫩经不起荒蛮的孤单,一封封墨写的家书总催我找个伴侣,以解忧以驱寒;母亲怕我受不住那冰冻的风寒,不知变卖了什么东西,为我买了那件滩羊皮大衣,见到谁都是出地一声撂下一脸灿烂的笑。她们上下寻找,让我更想家。因为西方人和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东方人都去外面餐馆用餐,准备他们周末的狂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