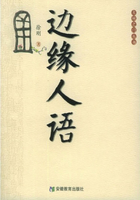胡然问:“不是要参政议政吗?”
“嗨,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你这人太憨!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是从哪个星球上来的?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吗?”胡然说:“好,到时候只带耳朵不带嘴就是了。”
王伦笑道:“这我就放心了。”又用开导的语气说:“当然,做政协委员,不能一句话都不说,那人家会说你不积极。可以拣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话题,慷慨激昂地说它一顿,九分拥护,一分批评,要像鸡毛;掸子那样扫得人家浑身舒服,你这个政协委员就算是当合格了。”
胡然心中暗想:那你让肖副市长的外甥媳妇去不就得了。几天后政协会议开始,果然记住了党组书记的话,沉默是金。过了两天,大家都发过一轮甚至两轮言了,胡然还是没有发言。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一边启发诱导,一边用热情的充满了笑意的眼睛看着胡然。于是一双双诚恳期待的目光便投向了作家。胡然把持不住了。他觉得再不发言就对不起大家的一片好意了,也太有负于“政协委员”这个崇高的名号了。讲些什么呢?他想起了农民。他是农家出身,又经常下乡,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好,就谈农民收入吧。市政府工作报告上说,去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二千八百元,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便质疑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无人回答。
胡然说:“我的老家就在远郊农村,对这个问题还有点发言权的。咱们郊县农村,每人平均还不到一亩地,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二三分地。就以每人一亩而论,平均产粮一千斤,这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一斤小麦六毛钱,一千斤六百元。还要扣去化肥、水费、电费、机耕费,且不算投入的大量劳力。当然,每家农户都有一点农副产品,人口多的还有在外打工的收入。但是无论如何,农村人均收入不会超过八百元。也就是说,农民的实际收入,只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零头。”
会场静得出奇。委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听着。
胡然说得高兴了,忘记了党组书记的叮嘱,又接着唾沫四溅地讲下去:“如果说,上面还只是一个大概推算的话,那么我的老家的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前年年终的时候,我老家所在的那个乡全年总产值两千五百万元。往上报的时候,乡长和书记商量了一下,对会计说:两千五百万报上去肯定通不过。咱们就翻上一番,报五千万吧。各乡都这么干,我们不干过不了关。结果就报了五千万。原以为弄虚作假会受批评,谁知县上一看根本就嫌少。县委书记亲自跑到乡上来,不训斥,不骂人,态度十分谦和,见了乡长村长双手一抱就作揖:帮个忙!帮个忙!最后又翻了一番,成了一亿元,这才万事大吉了。”
讲到这里,胡然有点愤怒了:“古城的第一个亿元乡就是这么来的!最后,县委书记由于政绩突出,提拔到别的地区当副专员去了。只可怜那些农民,从此每年按一亿元的总数,分解到各家各户收统筹提留和税款,真是不堪重负啊!”
胡然高声大气地说着,忽然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头。抬头一看,书记、市长、部长、局长们全都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一张张胖脸上露出愤怒、不悦甚至好奇的神情:好像在看一只从月球上跑来的怪物。作家的脑子里忽然一阵空白,眼前出现了一片雾气,视线变得模糊了。只觉得一张张狞厉的面孔向自己扑来……他出了一身汗。他变得口吃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清话,不知是怎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大家和他疏远了。领导见了他脖子一扭就走过去。吃饭时人们都不愿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他暗暗地感到了说真话的“份量”。从此他便学乖了。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多过一句嘴。开会时总是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他慢慢地也就悟了出来:人家让他来开会,并不是要他发什么宏论,主要是要他这个人,要“作家”这个身份。他来参加会,坐在那里,以壮声势,就足够了。他的任务只是举举拳头,画画圈儿,说几句大家都在说的冠冕堂皇的话。即使要提意见,那也有个“度”,他根本掌握不了这个“度”。于是他不再思考,不再发言,只是吃好,玩好,休息好。白天山吃海喝,满嘴流油,晚上看戏跳舞,唱卡拉OK,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至于会上讲的什么,说的什么,他既不认真去听,也不认真去想。半个月会议开了些什么内容,他竟说不上来。
奇怪!这样一来,大家又对他好起来了,关系又融洽了。委员们老远里见到他就喊:“作家!作家!”领导见了面也和他亲热地打招呼,甚至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作家,你来开会,可不能只带一双耳朵哟!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看法,大胆地提出来,知无不言嘛!”
尤其好笑的是,有时回机关,身边总是一大堆人,热切地问他一连串的问题,似乎期待着这次会议能解决许多问题,给大家带来多少好处。就连两地分居这样的问题都要问有没有出台新的政策,他只好含糊地答应着:“有希望,有希望。”心里却说:“等着去吧!”他想起了前些年在一些县乡选举时,干部们对农民代表说的话:“吃了四菜一汤,圈圈可要画圆些。”心中不禁一阵苦笑。
十分凑巧,胡然开会期间和市人事局的唐局长共住一个房间。这位局长是个外表憨厚拙讷,内心却十分精明的中年人。发言时永远是那几句话:“这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工作报告,全面地、准确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市一年来的工作……”再讨论别的报告,依然是这几句话,只不过把词儿前后颠倒一下,重新加以组合,变成“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总结了……”然后便掏出本子,认真地记着领导的发言。胡然感到纳闷:这样一些千篇一律的报纸语言,到底有什么好记的?值得做出如此谦虚恭敬的样子来记吗?
有一次唐局长正好坐在他的身边,凝神聚气地记着市长的讲话。出于好奇,胡然凑过脸去,却见人事局长在本子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公原来在练习硬笔书法!胡然暗自佩服:这位老兄算是把人活明白了。由此对“当官是一门艺术”的道理似乎也明白了三分。
一起住了几天,人混熟了,胡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杨小霞的调动问题。唐局长似乎没有听见,脸上毫无表情。晚上睡觉时,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当作家的,家里一定有好书吧?”
“局长想看什么书?”
“《金瓶梅》有吧?”
“……有。”
“我说的是原汁原味的《金瓶梅》。删节本我看过,没意思。”胡然稍一犹豫就答应了。作协资料室有一套内部分配购买的原本《金瓶梅词话》,他准备给人事局长借来。
“还有一本书,叫什么夫人的情人,听说也蛮刺激的。”
“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吗?”
“对,对,就是这本书。让咱学习学习嘛!”
“好!我明天一并给你带来。”
第二天上午,胡然趁开大会的空儿溜回机关,费了半天口舌,从李玲那里借出了《金瓶梅词话》,又回家将自己珍藏的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取上,兴冲冲地奉献给人事局长。
从此唐局长便进入紧张的“学习”状态。每天晚上必看的香港武打电视剧也不看了,一书在手,废寝忘食。往往看到深夜三四点钟,甚至看到天明,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彻夜不息的灯光弄得胡然无法休息,只得用被子蒙了头睡觉。
终于“学习”完了两部文学名着,人事局长笑眯眯地问胡然:“你说的那个杨小霞,是你什么人?”
“我外甥。”
“你是哪里人?”
“古城人。”
局长笑道:“你的外甥怎么在那么远的山区?”
胡然脸一红,不知如何回答。
局长说:“既然是作家的外甥,那我问一下。”说着拿起大哥大,拨通了调配处长的电话:“老范吗?那个,那个,杨小霞……怎么,还没有研究?唔……抓紧办一下。是的,是的,要抓紧。”转过脸来,对胡然粲然一笑:“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
“不是还要上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