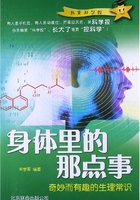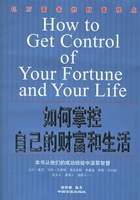一个留着血迹的蛋壳,蛋被孵化了。
第二天蛋壳不见了
使者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我,并没大吃一惊。他揉揉眼睛,问:“你没死?”
“我好好的。”我拍拍胸脯。
“你怎么爬上来的?”使者打量着我,表示怀疑。
“秘密。任何人也别想知道。”那个洞可能成为我和小柯离开这里的备用通道,所以保密。
“那你的衣服哪儿去了,看上去缺点什么。”使者用一只手捂上眼睛,另一只手伸到床下拽出一件灰衣扔给我。他不习惯看见不穿灰衣的人,这是不是太夸张。
我想我还得穿上它,为了让公民们能接受我。为防止穿上灰衣后忘掉小柯,我穿上它之前心里先默念着:我找到小柯了,找到了。我俩一起离开,沿着河流往下游走……
我确信记住了才穿上灰衣。果然还记得一清二楚:小柯找到了,一起往下游走。
从那天起,我一睡觉就悄悄脱下灰衣,醒时再穿上。这个办法奏效了,我没像从前那样变得不可思议,只是偶尔才想要掐死点什么,只是有一点点想,也不那么强烈了,完全可以克制。
我回到灰城,也没有引起其他公民多大的惊奇,就像我刚来时一样。
我回来后马上又去了厨房,打饭正坐在一个破椅子上打盹儿,手里拎着饭勺,垂着。我拿起一块像山药的东西,狼吞虎咽地嚼起来,也许是嚼的声音太大了,把打饭弄醒了。他见我吃东西,一下跳了起来。“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不想吃了你才能吃。”打饭说着把嘴巴凑过来,在我手里的山药上咬了一口,“现在我不想吃了,可以归你了。”我瞧瞧他,直想笑,继续吃这块“山药”。
在车库旁我遇见那个瘦瘦的男孩了。没错,是小柯。小柯蹲在那里,用一根树枝刺地上的蚂蚁。天都亮了,该是睡觉的时候了,但他没去睡,这些蚂蚁吸引了他。这没错,小柯从前就喜欢观察蚂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过,他从不伤害它们。
我朝他招招手:“嘿,你叫小柯,还记得吗?”
小柯抬头瞥了我一下,根本没在意我说什么,继续用小树枝刺地上的蚂蚁。我凑近些,见一只蚂蚁被他刺得翻了几个跟头,但活动了一下筋骨,仍能继续前进。小柯用更大的力气向它刺去,它被刺中了,粘在棍子尖上,其实整个身体都破碎了,只有一条细腿还在动。
“它死定了……”小柯呢喃着,沉浸在这个残忍的游戏里。他流出了口水。
我也流出了口水,刚才我也禁不住沉浸其中了。我提醒自己:残忍,太残忍……
小柯的树枝瞄向另一只倒霉的蚂蚁了。
我掐了自己一下,不再看它,我说:“小柯,我是你表哥,要与你去南美丛林的那个……”
小柯说:“表哥,什么是表哥……”小柯的树枝落空了两次。他又沉浸在游戏中了。
我没有完全放弃,说:“那做个朋友得了。”
我向他伸出手,我想试试灰城的观念在小柯头脑里顽固到了什么程度。
“朋友……朋友是干什么的?”小柯对这个词很陌生。
“互相帮助,离开这里。”我脱口而出。
“可耻!”小柯腾地站起来,走开了。他径直向楼上跑去。看来,他去睡觉了。
我茫然地望着灰城四周的丛林,心里无比压抑。首领拎着网回来了,他捕到了几只绿色的鸟。
首领歪着脑袋,奇怪地瞧着我:“你功夫不错。打饭也下去过一回,他发现粮食了。我用脚踢他,也没踢下去,他抓住吊粮食的绳子爬上来了。那一回不好玩。”
首领说完,用手指弹了一下鸟头,上楼“消遣”去了。
我又有了要扭断鸟脖子的念头,身不由己地跟在首领身后,也上楼了。
走到房间门口时我终于“醒”了过来,拐向自己的房间,进去躺在地板上。使者睡着了,不时哭上两声。我躺着,睡了一会儿又醒了。我想起那枚被我弄丢的鸟蛋了。在灰城,经常吃的是一种植物的块茎和打饭从鼠洞里搞上来的粮食,偶尔也能吃到鸟肉,蛋是很难吃到的。我太想尝尝蛋是什么滋味了。
我爬起来,下楼。
其实到丛林中找那条河,即使是在白天也不容易。
我得用独轮小车带路。推上小车,它不动。我就说:“小车小车,陷了陷了。”它很听话,带上我左拐右拐,很快就走在丛林中的小路上了。它被我骗了。
这一路上,我看到许多长得怪模怪样的植物。有一种像马蹄莲,却高得惊人,有三四米高,叶子比雨伞还大。总之,所有的草长得都像树那么高。那种两次袭击过我的植物长得确实像蛇,许多条叶子不停地张牙舞爪,等待猎物到来。我想起一个成语“守株待兔”,用在它身上正合适。我有了防备,小心地从它旁边挤过去,它居然没发现我。这是一片奇怪的丛林。
走了一会儿,头顶的绿荫稀少了,阳光更多地渗露下来。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了。
我先蹲在岸边用河水洗了洗脸,然后脱掉灰衣,把它挂在树枝上,我又把上半身简单地洗了一遍,这是为了清醒头脑。一缕阳光透过树叶照在我的脑门上,我内心产生一种爱与祥和。
我淌着水向上游寻找那个隐匿在草丛中的洞口。那枚鸟蛋应该在洞口附近。不久,我就看见河滩了,河水在这里浅了下来,分成几股细流。河滩边上有一簇草木特别繁茂,黑幽幽的。我原来的那件灰衣服挂在一丛灌木上。没错,我找到了洞口,它就在这里。
下一步,再找大鸟蛋就不难了。我把搜索范围就确定在这片河滩上,这一带林木低矮,阳光灿烂地照耀河滩,照耀我。我不放过河滩上任何一簇草丛和石堆,我用脚尖踢一丛草时被一只大型的昆虫吓得浑身直抖。我叫不出它的名字,它举起螳螂才有的绿色刀臂向我挥了挥,朝我吐了一口绿色的浆液,走了,不慌不忙地。我呆立在那里,直到它在另一簇草丛中不见了踪影。小柯会喜欢这种动物吗?也不会的。它大得超出了常规。
我不放心,怕它再从那簇草丛中爬出来,就找了一块石头向那儿投去,它没有惊慌失措地从那里面跑出来。我猜被我打中了,但我并不想去看它被石头砸扁的样子。就在这时候我看见那枚蛋。它是灰白色的,躺在那簇草丛的边缘。我马上绕过去,又拾起一块石头投过去,确认那个大昆虫已死,才走过去拾起那枚大鸟蛋。
它已经裂开了,难道被我摔破了?再一看,里面是空的,没有一点蛋清和蛋黄。假如是我昨晚摔破的,周围应该有蛋清和蛋黄。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又有新发现--蛋壳里面印着一丝血迹。
它被温暖的河滩孵化了。
周围的宁静变成了不祥的预兆。我扔了蛋壳,恨不能让双手也变成腿,飞也似的离开这片河滩。我不敢在这一带停留,披上灰衣,推上独轮小车,跑回灰城。
我把独轮小车停在院子里时,公民们还在睡觉。躺在地板上,我才发觉自己已经疲劳到了一定程度,但就是不能入睡。囤着那么多粮食老鼠却几乎绝迹的大鼠洞、抓人的植物、巨型昆虫、孵化的大鸟蛋(我已怀疑它根本不是鸟的蛋)、午夜塌陷的墙、一个个冷漠的公民……我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我正置身于无法摆脱的恐怖之中。我在哪儿?我怀疑我到了另一个年代。
我必须把河滩附近可能出现的危险告诉这里的公民们。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觉得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特别的世界里,我要帮他们走出来,不只是带出小柯。所幸我已经摆脱那个“世界”了,我是清醒的。我能做到的他们就可能做到。他们在睡眠时会哭、会流泪,说明他们内心深处还藏着善良,只有身体睡着时,它才偷偷溜出来。我要做的是设法让它大大方方地溜出来,光明正大地出来唱歌跳舞。
我推醒首领,他果然很不高兴。
“有件事我得说一下,跟每个公民都得说一下,先跟你说吧。”
首领打了个哈欠:“你干扰我了,作为惩罚,两天不分给你鸟脖子,你别想消遣了。”
“我们有危险。”我说。
首领说:“危险,天天都有,就想说这个吗?”
我说:“这是大事,跟围墙不是一回事。”
首领说:“看看你那种讨厌的表情,一点也不像个灰城公民!”
我想三两句就把这件事讲清楚,可是没有简便的办法:“是别的危险,就在河滩那一带,夜里去河边采石头得小心点。”
首领说:“是怕掉到深水里吗?河底的石头每天都往上长,河水从来都不深。”
“不是。一枚蛋在河滩上孵化了,它不是鸟蛋,应该是一种体形很大的动物的蛋。”
“好啊,抓住它,扭断它的脖子,吃掉,这事打饭能办好。”首领把站在门口的打饭叫进来。打饭路过这里,正看着我和首领谈话,打饭说:“没问题。”然后做了一个啃骨头的动作。
“蛋有拳头那么大,鸟蛋没那么大。”我努力回忆着它的大小。我对自己的揣测更加深信不疑。
“那是一只大鸟下的蛋。大鸟下的蛋孵出大鸟,可以扭大脖子玩,过瘾。我得用更大力气。”首领打了个哈欠,对我讲的话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打饭趁他不注意,把他床下一只断了脖子的鸟拎走了。
“鸟可不会把蛋产在一个洞里,只有缺心眼的鸟才那么干!”
我怏怏地走开了,感到很窝囊。不被人理解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找到小柯,打算把刚才的话再跟他讲一遍,可是还没开口就没信心了,小柯也不能相信河滩上有危险。他们都不善于与别人交流,只是按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从来不接受别人。
小柯已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也没有必要跟使者讲了。
他们在这片丛林中也许没遇见过其他危险,豹子们知道这里住着一群人类,一定早就迁走了。他们整天面对的就是那面不停止塌陷的围墙,也就是他们全部的“危险”。
我一气之下竟很快睡着了。我刚睡着,一条大鳄鱼就从一枚巨大的卵石里钻出来,身上带着血丝,它刚张开大嘴我就受不了啦,呼地从床上坐起来。午夜“漫长”的钟声正在敲响,楼里已有了响动--灰城又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
“陷了!陷了!”
接着,独轮小车们相继出发了。我连滚带爬下楼去。
河滩那边没有一点声响,零零碎碎闪着银光。那些银光似乎在慢慢走动,面积越来越大。
我拉了小柯一下:“快走啊!不是装满了吗?”
“没装满。”小柯一点也不着急。
等到小柯的车走了,我又催使者和首领,很快使者和首领也走了。他们都走了。我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没出事。也就在这时我才觉察出这里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暗自叫苦不迭,慌里慌张地推上小车,钻进丛林。在救了别人以后,最好也别牺牲自己。
往返几次,事实证明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也没有为此事同我辩论。我真怕被问得哑口无言,不过,谁也没提这事。他们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其实这也是一种“潇洒”。
我踏踏实实睡了一觉,后来那只大鳄鱼又咧着大嘴跑到我的梦里来了,没办法,不能睡了。
太阳在中天贴着,大约是中午了。我推上独轮小车,悄悄摸近河滩。
蛋壳也已经不见了。确实不见了,我找得很仔细。这再明显不过了,这里有问题,绝对有蹊跷的故事。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动物,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踪迹,才把蛋壳收了回去。有智慧的敌人不更可怕吗?
我也“心满意足”了,可以“放心”回去了。我冷汗淋漓,却不敢狂奔,蹑手蹑脚地离开了河滩,生怕惊动“它”。它多半是藏匿在洞里呢。一想到我曾经在那个洞里爬了半宿,我就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居然没跟它撞上。
我以一个标准灰城公民的神态站在首领面前:“今晚采石头别离岸边太远,蛋壳也已经不见了……”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不得不再次向他们提出警告。
首领平淡地望着我,不知他接受了没有,但我必须说出来。我站在小柯床前,耐心说了一遍。小柯翻了个身,继续睡觉。接着我挨个找了灰城所有的公民,把那些话重复讲给他们听,他们都无动于衷。我佩服他们的忍耐力,更佩服自己的忍耐力。
打饭算是好的,跟我多说了一些话,这是我的情报送出后产生反响最大的一次。
打饭说我从洞里回来后搅乱了他的日子,弄得他连饭都吃不好……就这些。
不过,我从那些无动于衷的目光中却发现有一种不友好的情绪在积聚。我感到不太妙。
还是回去睡觉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