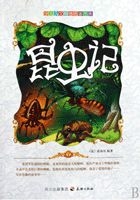有关蛇一样的叶子、洞穴和奇怪的蛋
上半夜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睡着。黑夜包裹着这幢别墅,风一丝一丝在林中钻来钻去,有时还钻到楼里来,把楼里钻得充满各种声响。我抱起毛毯,蜷在墙角,努力不让自己发抖。这个时刻,我特别想杀点什么,鸟、老鼠,随便什么都行,而这个念头本身又使夜晚更加恐怖,我担心自己要变成妖精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楼里有了响动,是起床时发出的声音。我挪到窗前,发现月亮总算从丛林中挣扎出来了,挂在高一点的地方,脸显然是被荆棘划破了。院子里出现几条灰影--他们已经起床了,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灰城新的一天真正从午夜以后开始。
挂在走廊里的大钟突然“发作”起来,“当--当--”这个机械钟发出冷冷的笑声。使者从床上爬起来,大概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就径直朝门口走去。这个动作很机械,也很准确。我怀疑使者是像妖精一样飘出去的。
马上就要开始了。
果然,钟声刚停,楼下就传来轰隆隆的响声。
“陷了!陷了!”
独轮小车开始唱--吱呀吱呀,其中还夹杂着哈欠。
我从墙角站起来,扔掉毛毯,一步一步摸下楼。有个灰影从我身边擦过,一点声响也没有,快速地“飘”下楼去。到现在,除了那个首领、打饭和使者跟我有交流,其他所有“公民”都未关注过我,我也没仔细观察过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机会。白天他们主要是躲在灰暗的楼里睡觉,到了后半夜才出来砌墙。原来,想做个好强盗也需要勤奋。
围墙果然陷下去一截,明显地矮了,南面干脆倒塌了一段。这一切借着从枝叶间透出的月光就能看得到,但灰城的公民们在围墙下工作似乎并不借助月光,他们全凭熟练。一个像使者的公民正把一块石头从小车上搬下来,一转身又砌到墙上。只几个来回,小车上的石头就用光了,他推上小车又要出发了。
我说:“给我一辆车。”我很想加入到砌墙的队伍中去。其实到现在也没人明确要求我干这个,连首领也没亲口这样对我说起过,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加入进去了。
“到车库去拿。”这是首领的声音。我也看不清那些忙乱的灰影中哪个是首领。
推开车库的铁门,它吱吱嘎嘎响个没完,紧接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险些把我“扑”倒。我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摸,摸了半天才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我试着一推,走了,是一辆小车。我就要了这辆小车,跟在一个影子后面,他好像是首领。我得采一车石头去,这是全新体验。
丛林中的路我一点儿不熟,刚进丛林,车就翻了,这种一个轮子的小车实在不好推。这时我听见前面像首领的影子自言自语:“小车小车,墙陷了……”刚说完他就加快了速度,转眼就拐进丛林深处。这回我听出来了,他是首领。
我惊呆了,莫非这小车真有魔力,就学着首领刚才的口气:“小车小车,墙陷了……”嘿,小车马上有了动力,竟带着我朝某个方向走去了。它已对这条路很熟悉。
那条河卧在丛林稀疏的一段,远远就听见河水流动的声响,再走近些,能看见它流动的银光了。有的小车已经装满了往回走呢。默默地不说话,只有小车在吱呀吱呀地响。首领比我快些,已经在河里搬石头了。
我的小车自动停在岸边。我把裤脚挽起来,下到河里,河水凉丝丝的快没到膝盖了,脚下又硬又滑的就是石头。这时,又有一辆小车停在岸边,一个瘦瘦的影子在河水中晃动,离我只有几步远。河水的银光闪到他脸上。我再次感到这模样有点熟悉,好像与我的过去有关。可是我没法细想。我对自己的过去越来越模糊了。
我们在河中采石破坏了河水流动的韵律,波光惊慌失措地闪烁,好像要出什么大事了,有条鱼就从我的两腿旁凉凉地滑过去了。
我把小车很快装满了石头,可以回去砌墙了。独轮小车带我走上小路。首领走在前面。
“它有魔力。”我说。
“你穿的衣服也有魔力,它能帮你慢慢变成像样的灰城人。”
哦,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灰衣,尽管我什么也看不清。难道我对灰城的适应与它有关?
丛林中的小路狭窄,我几乎被两旁的植物夹住了,但独轮小车固执地带我前行。这时,一些细长的叶子张牙舞爪地向我伸过来,每抓一次我都抖个不停,我怀疑它们是蛇。抓过几次我心里有了数,它们并不动真格的,碰碰就缩回去了。这是一些喜欢开玩笑的神秘植物。
危险往往在你刚刚放松警惕的时刻到来,一条更细更长的叶子抓住我不放了。我努力地让自己明白:不是蛇,是一种植物,但它更牢固地抓住我,我的胳膊又疼又痒,身上生起一层疙瘩。我说:“能不能不闹?我没时间,我要去砌墙。”可它不听我解释,还是固执地缠住我,这犟脾气简直像我的一个亲戚。
我的一条胳膊完全被它缠住了,并被它用力往丛林里扯。我的头发一根一根站得直直的准备做早操。我彻底不自信了,也不想再欺骗自己,我说:“首领,蛇……”
首领在前面回头看了我一下,继续走,只说:“不是。”哦,他不帮我是为了做一个“正派”的灰城公民,我不该拉他“下水”。
“蛇”的拉力越来越大,我赶紧松开小车把手,腾出另一只手去撕扯它,我摸到了冰凉的皮肤。我一出手,惹恼了这种植物,马上又有几条“蛇”参加进来,我赶紧把这只还算自由的手撤回来。我心想要完蛋了,连写份遗书的机会都没有。
我想是一个变成植物模样的蛇在袭击我。它实质上就是蛇!
我没完全放弃,另一只手努力伸向小车,整个身子也尽量向小车这边用力,终于抓到一块石头。我用全身的力气向蛇砸去,只砸了一下它就有了松动。我又砸了一下,它竟彻底放开了我,我抽出又酸又痛的胳膊,等着与它决战,但它没有任何想法了,在那里静静立着。这说明它不是蛇,是一种食肉植物,一种欺软怕硬的植物。
我不敢久留,继续赶路,再没遇见别的麻烦。
路越走越宽,丛林让开了通道,也能看见灰城的淡影了,它像一头蹲在丛林中的大灰象。公民们在砌墙,不声不响地。只有石头与墙、石头与车相碰撞发出的声响。我也不想与任何人谈刚才的历险(要是在平时,我刚出丛林就要开始讲了)。我搬下一块水淋淋的石头,学着别人的样子,把它砌在上面。这一点也不难,他们就是这么砌的。其实就是把石头一块一块摞起来,摞到一定高度,墙就砌完了。我紧接着把第二块、第三块石头砌上去,它就高了。我刚把第五块石头砌上去,使者尖叫一声:“老鼠!”
首领沉稳地说:“抓住,掐死它。”
这场面昨天晚上也发生过,他们的生活重复得像用复印机复印出来的一样。
我一低头,这个小黑球向我滚来了。那个瘦瘦的男孩抢先追过来。小黑球挤过铁门,往车库那边滚去了。我扔了石头,大叫一声追上去,赶在了瘦男孩前面。我要掐死什么的欲念又产生了,刚才忙于采石砌墙,这个念头暂时藏起来了。我一头钻进车库,可刚挪了几步,就一脚踩空了,身体迅速下坠,心脏却按相反方向往喉咙这边来。我的意识几乎一片空白,只希望下坠早点结束。
砰!停止了。我的心脏狂跳了两下,又落回到原来的位置,在原来的位置跳个不停。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意外。这时头顶上传来了说话声,勉强听得清楚。
“掉下去了。”
“老鼠掉下去了?怎么这么响,砰的一下?”
“不是老鼠,是一个公民,新来的那个。”
“太好了,比掐老鼠还过瘾!”
“哈哈……”
我听见上面发出一阵干枯的笑声。简直不是笑,是乌鸦叫。
我断定自己是落到了一个深坑里。原来,车库里还有一个深坑。这是防备政府军进攻的陷阱吧?怎么给我用上了?我再也不想去追那个小耗子了,朝上面喊:“拉我上去!最好给我根绳子!我是自己人。”
喊声在坑里荡来荡去很恐怖,我没想到我的声音如此恐怖。上面根本就没有反应。这时我的视觉已适应了这里的光线,上面形成一个灰蒙蒙的圆形洞,那里就是洞口,刚才我就是从那里“飞”下来的,而我降落的地方是洞底。我计算不出这其间的距离。我像书中那个悲惨的青蛙一样,可以“坐井观天”了。
“让他喊吧,把舌头喊得粉碎!”
我听不清这个声音是谁的,就想飞出去掐断他的脖子,再一脚把他踹下来,坐在现在我坐的地方。
“拉我上去!首领--使者--打饭--”
我把知道的三个名字轮番喊出来,他们并不答应,但他们都在场。都在,又都不言语,可见是在静静欣赏我的痛苦。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恶毒的行径了!大概是刚才重重的一摔让我清醒了,我对灰城的“规则”恨到了骨髓里。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大概陆续离开了--没兴趣“欣赏”了,就走了!大概是打饭临走时说:“粮食我早就运走了,你还下去干吗呢?”
这洞原来就是打饭当年发现粮食时挖开的鼠洞。我想我与打饭的遭遇相似,他当年也来过这地方,就做最后的努力向打饭求救。我从没这样哀求过别人,从没像小羊羔一样跟人说话,自尊已经丢得一干二净了,连骨头都没剩。
“打饭,你还记得这里的味道吗?”
“不记得了。”打饭说。
“味道不好,我想呕吐。”
“随便吐吧,里边没粮食。”打饭说。
“我想求你给我一根绳子。”我说出本意。
“你想让我良心受到谴责吗?你真不仁义!”打饭气愤地走开了,肯定不在洞口了,因为他再不搭话了。
我发誓不再求人也不再生气。平静一会儿后我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积攒力气。我想憋足劲儿顺着洞壁爬上去。我准备好了就双手抠住洞壁,向上一蹿,可是当我长舒了一口气后发现自己又滑到了洞底。洞壁太陡了。我重新坐下来,大口喘着粗气。上面传来砌墙的种种声响,令我气愤至极。我用不同的姿势又试了几次,可是结果却完全一样。
按灰城的道德准则,他们不会来帮我了。我只有准备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做一个洞里的强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