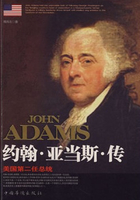牛德衡说:“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不易
懂管理,最后被人撞破了。牛德衡就不是牛德衡,牛德衡仰慕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女人,成就了这样的一番事业,如何了得!这时,他再次注意到了她下巴上的那粒黑痣。民间老百姓有种迷信的说法,说那叫“钱痣”,富贵的象征哪。这粒黑痣,在她脸上甚至显得很好看,使她变得“媚”起来。
“匡总,哎呀呀,真是不得了,女中豪杰啊。”牛德衡说。匡总很有身份地微笑了一下,表示自己对现在的成就并不十分在意,“哪里呀,很辛苦的。”牛德衡想:那是自然。可是,她虽然受了些辛苦,毕竟还是成就了一番事业,大事业,而自己吃的辛苦哪里在她之下?甚至远比她要辛苦。他都差点自杀掉。她有过吗?没有。由此可见,这个女人的能耐非同寻常。
“大姐看上去比我年轻”牛德衡说。那个女人心想:那是自然。牛德衡说:“也就好像只有三十三四岁的样子。”那个女人在肚里说:这个家伙,嘴巴倒甜。我怎么就一下成了三十三四了?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可事业这么成功,真是‘大姐大’,我叫得一点也没错。”牛德衡说,“叫你小姐,就是唐突了。”
作为董事长、总经理的这个女人,听了他这番话,就笑,很艺术地笑,非常矜持的笑。
“你做什么事啊?”她问。
牛德衡犹豫了一下,想:我也不能让她看轻了,反正就是胡说呗。如果她看得起我,以后从她身上捞点好处,也未可知。就说,“我也是自己做,当然,与大姐不能比。”
匡女人又笑了,说:“不好这么说的,每个人起点不一样,机会不一样。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做大的,做得比我还大。我这点算什么呀?还有人做得比我还要好呢。”
牛德衡想:这个女人真是谦虚。
“不过,在我这个行当里,我是做得比较好的。”她说。
“匡总做什么?”牛德衡问。
“什么都做,什么赚钱做什么。关键是项目要看准。”她说,“投资是一门学问。我们匡氏集团总部是在新加坡。匡氏是一个家庭集团。我祖父创下的产业。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祖父一下就捐了十架飞机。”
牛德衡在心里对这个女人,就更加地敬重了。他想起了过去那一次他在车上向那一帮农民胡说海吹的情景。那一帮农民们对他是多么的敬重啊。现在,他则成了那群农民中的一个了。当然,人家这个匡总可是真的,货真价实啊,他想。
“我这次到北京要和一家投资公司洽谈,共同开发一个大项目。一共要投资三千万美元。”她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听得很有兴趣,就继续说,“现在,有一种合作方式是非常好的,就是共同投资。这样,风险要小一些。独家承担风险是现代投资的大忌。客观上,当然利润也要少一些。可是,现代商业,是不能打没有把握之仗的。而且,虽说是共同投资,但实际主动权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牛德衡连连点头。听得出来,匡娉妮就不是匡娉妮了,会经营。
“你以后有什么好的项目,我们匡氏集团也可以进行投资。”她说。
牛德衡笑起来,“那当然好,太好了。”
“你到那边干什么?也是生意上的事?”她问。
牛德衡笑笑,说:“不能跟你比,也是合作上的事。一点小生意。总共只有几十万,烦。”说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累啊,真累。有时候想想这么点小生意,累成这样,得不偿失啊。”
她听了也笑了起来,说:“那你没得怨,又要赚钱,又要享受,那是没有的好事。”
牛德衡深为赞同,连连点头,煞有介事,好像自己真的赚了多少的钱。
一路上,他们面对面,相谈甚欢。牛德衡高兴地看到,这个匡氏集团的女老总,和他谈得非常投缘,而且,好像对他挺有好感。他们甚至谈到了家庭的一些情况。牛德衡告诉她,自己已经离婚多年了,有一个孩子跟着前妻过。而他之所以离婚,并不是他的负心,而是她主动离他而去。这些年自己所以没娶,也绝不是自己不想娶,或是没人愿意嫁给他,却是他实在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甚至还编出一个非常动听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他的公司里,办公室的女秘书,已经暗恋了他好些年了。女秘书非常年轻,漂亮,谈过几个男朋友,但她都嫌他们肤浅。他一直以为这个女秘书不错,可他根本就没有往那上面去想。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副总告诉他:她一直暗恋着他,又不敢表白。在公司里,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去年我们出差去河南一个地方,结果在半道上出了车祸。我那辆新奥迪从半山腰上翻了下去。我当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以为这肯定是完了。后来在医院里醒过来,看到身边围满了人。但就是没有看到司机和女秘书。副总告诉我:她死了。临死的时候还一直紧紧地抱着我。如果不是她舍身忘我地抱着我,我一定死了。是她,用身体护住了我。”
牛德衡说到动情处,眼泪就下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就被自己感动了。
“后来,很长时间,我在心里就把她当成了我的女人。虽然,我们并没有结婚。甚至我们连一句亲密的话都没有说过。我们的手都没有拉过。但我觉得她所做的,远比一个妻子所能做的,要多。她作了一个连妻子也未必就肯牺牲的东西。她为了我,把命都给了呀。”牛德衡说,“可惜我认识到她好处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匡总两手白胖的手,在桌上绞着,做惋惜状,说:“世界上从来都是多情女子无情汉哪,你这样,也还算是还对得起她的好处。你这样也还是要找一个,男人不成家怎么能行?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一定还是成家好。可我们在心里也很明白。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女子,还不是图我手上的这些钱?她们动不动就是买多少多少东西,让你请她们吃饭,坐车子兜风,没有真情实感的。”心里却想:我这样子,谁会看上我?要是有人看上我,那也倒是一件好事。连城郊结合部大街两边那些洗头屋里低贱的女子,都看不上我。
他已经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连女人身上什么味都快忘光了。他一门心思,想的只是钱。钱,钱,钱,还是钱!饱暖思淫欲啊,此话不假。好些年前,在海南,他光顾过几次,后来没了钱,就再也不去了。嫖一次的花费,够他活好两个星期。生存到底是第一位的,它压迫并战胜了性欲。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清教徒。
“好姑娘还是有的,关键是你要发现她们。”匡总说,“……而且,事实上,你还是找一个年龄差距不大的,比较好。这样的女人,毕竟生活经验丰富,又懂得珍惜家庭,又会疼男人。年轻姑娘哪里懂。”
牛德衡在她的目光下,感觉自己的那张老脸居然有些热……
报纸连载后不久,一个出版社出版就决定出它的单行本。负责编辑我这本书的女编辑曾经对我下面的一段有过不同意见,她认为我写得有点直露了。她在电话里笑着说:“你不觉得他们上床太快了吗?”
“这符合他们的心理啊。你看,牛德衡是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而且他想:碰上这么个女人,成熟、丰满,不仅有风韵,而且还有钱,自己假如能‘傍’上,不是天上掉馅饼?这年头,不仅女人‘傍大款’,也有男人‘傍’富婆的。从这个匡娉妮来说,她也以为自己是遇上了一个好男人。很自然的事。”我知道,事实上罗萌萌(女编辑)并不是真心在取笑我,她只是在找一个借口和我调笑。
我们早就是熟悉的。
好几年前就认识了,在一次笔会上,我们甚至差点就发生了那种关系。但那次很不巧,我想。,这件事早晚一定还会发生的。
表面上,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罗萌萌经常说完我其实不具备一个作家的浪漫气质。我想:也许是对的吧。
“这个匡娉妮应该再矜持一些,可能更符合她开始时候的表现。”她又说。
我笑起来,说:“像你那样的矜持,非让人急死不可。”
她在电话那边也哧哧笑起来,轻声说:“去你的,少来。我这是在办公室里。”
我说:“又不会被别人听到。”
她在电话那边没有吱声。
我说:“难道你们不喜欢这一段?事实上,这对你们图书销售也有好处。读者总是希望能迅速地看到一些能够刺激他们的东西。有点情色好。这是文学里面回避不了的东西。一本长篇,开头要是写得太平了,他就没有兴趣再往下读。”
她笑起来,“你承认你是个情色小说作家?”
我叫起来,说:“这里面有色情描写吗?这点东西,根本就不能算是色情。”
“我说你是情色,没有说你色情。”她纠正说。
可我感觉她内心里的想法是一样的。“金圣叹批注《西厢》里的一折,那里面有一段性爱描写,被人指责为淫秽,他说‘这种男欢女爱的事,家家都有,哪里有什么淫秽?其实,这并不是写作者不健康啊,而是看的人心里有鬼’。”我说。
“你不就是说我不健康吗?”她说。
我笑起来,说:“开个玩笑,你不要生气。”顿了顿,又问,“你什么时候过来?我请你去西霞湖,最近在郊县还发现了一个紫竹山,有山有水,与世隔绝,据说非常好。我请你去玩。”她说:“不去了,省得我这种不健康的人,把你也感染得病了。”
“生气了?”我想,她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哪。
她笑起来,说:“哪里呀。我怎么走得开?以后再去吧。”
我说:“好,那我等你。”
牛德衡裹着浴巾出来的时候,看到匡总已经躺在床上了。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在梦境里一样。牛德衡想:有了这个女人,只怕自己今后真的就有靠山了。她一个那么大的产业,分一些给他做做,就把他撑死了。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可是,她怎么就会看上了他?
在淋浴间的镜子前,他反复端详自己。嗯,眼睛还可以,虽然小了些,可是贼亮得很;鼻梁也行,够挺;只是嘴唇薄了些,看上去整个形象有些尖刻、穷酸。毕竟是老了,他在镜前这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头上已经秃得非常厉害了,眼角也全是鱼尾纹。低头往下看,胸脯扁平,中间长了几根稀稀拉拉的黑毛,再往下,双腿可以说是瘦骨嶙峋。不雅不雅,他赶紧用浴巾把下面围了起来。
看到他出来了,躺在床上的匡总主动在床上把身子挪了一下,宽大洁白的床单,立即明显空出了一个位置。牛德衡揭开薄被,看到她已经是只有一条内裤了,胸前的乳房果然非常丰满。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躺进去,她就一把将他下面围着的浴巾扯了下来。
牛德衡兴奋得很,虽然面对的只是一个早已失去青春的中年女人,但她却是非常的成熟、风骚。他感觉自己就像吃了春药一样,勇猛异常。她在他身下,就像是一团面。而他骑在这团面上,有一种卓越的成功感。是啊,她可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非凡的女人,此刻,却在他的身下,如一个巨大的面团。她在下面扭动着,呻吟着,那声音像是痛苦异常。他知道那其实是快乐兴奋的声音。在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她的双臂紧紧地箍着他,箍着他的腰,然后一直移到他本来就很瘦削的屁股。她的五指都快掐到他屁股的肉里去了……
当他燃上一支烟,平静地躺在那里的时候,匡总则笑眯眯地看着他,“满意了吗?”她问。牛德衡抚了一下她的头发,说:“真好。”匡总作撒娇状,在被子里扭了一下屁股,说:“你不要搪塞我,我是认真的呢。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对待过别的男人。”牛德衡自然明白她所想表白的意思,安慰她说:“我是真心喜欢你。我觉得你身上的风韵非凡,与众不同。你有一种成熟女人的美。”她说:“可我老了呀。”他说:“你不老,我才老了。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多么有味道吗?男人,要的就是女人的味道。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事实上倒未必觉得年轻姑娘好。那些年轻姑娘懂什么呀?”
“我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多合作噢。”匡总说。
牛德衡当然是巴不得她如此说,“好好,那真的是太好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只管说。我的那个是个小公司,和你的比不得。”
“小公司也是可以做大的,慢慢来,不能急。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她说。
他连连地点头,表示同意。
……
这一段原先在报纸上连载时是没有的。事实上我非常不喜欢报纸连载小说,它们往往只需要情节,而不需要其余。而一部真正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它除了情节的骨架之外,更多的是血和肉。报纸却只要骨架。连载出来的效果往往也就是骷髅效果。
也许一篇故事更适合报纸连载,而不是什么文学作品。我写了这么多部长篇,也就是这一部才得到连载。我想:报纸的编辑可能是看中了它的“掘金题材”。那么,这一段真的有“情色”之嫌?不,它只是有趣。
我喜欢。要是没有这一段,这个女人的确很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