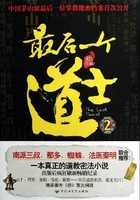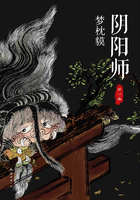那人大着胆子又道:“那海大人是如何参透这画的?”
海瑞扬起了手中的两本书,道:“就是陆大人放在桌案上的两本书。”他走到百姓面前,将书一展,道:“上面一本叫做《迷情记》,下面一本乃是《对韵》,乍一看并无联系,可深究起来却是大有文章。”
“《对韵》一书在《迷情记》底下,是为‘谜底’,陆大人也就是告诉我,这几幅画的谜底就是这本《对韵》。只要在此书中找寻,就一定会参透。”
他来到第一幅画前,道:“大家请看,这第一幅画画的是什么?”由于大堂中灯火辉煌,那屏风放得又近,所以可以清楚得看清上面的每一笔。有人叫道:“是山。”“那边上是什么?一块玉么?”“是吧,是碎玉……”海瑞一摆手,道:“对了,是一座山,还有一块玉。碎玉。而这幅画要说的是一个典故,那就是玉碎昆山。”
大家点头,又有人道:“那与此案有何关系?”海瑞扬了扬手中那本对韵,道:“这幅画的谜底就在此书中,如果对对子的话,这玉碎昆山可对什么呢?”众人沉默片刻,一个胆小的秀才仗着胆子叫了一小声:“金生丽水。”
海瑞一拍手,叫道:“是了!就是这句‘金生丽水’。陆大人是在向我说,丽水县出了与金银有关的案子。”
众人恍然大悟,齐声喝彩,那秀才被边上的人看得脸直发红,却也挺直了胸膛,微显得有些得意。
海瑞又道:“可既是出了这样的案子,那些银子又是被谁盗走的呢?陆大人在第二幅画中便告诉了我们。大家看这第二幅画。”大家看了一下,有人叫道:“那是一个人在哭,还抱着一块石头哩。”“那人的双脚都断了。”方才那秀才有了胆量,大声道:“这画我知道,是卞和献玉的故事。”海瑞点头道:“正是,而这‘卞和三献玉’的典故,对的正是‘杨震四知金’。而杨震指的是谁呢?大家可能早已猜出,是主薄杨真。正是他偷走了那些银子。”
堂下一阵纷乱,大家议论起来,海瑞等到声音小了,才道:“既是杨真偷走了银子,那他又将脏银放在何处呢?陆大人也早已探知,这第三幅画就说的是库银的下落。”
大家立时不说话了,连那潘华也都怔怔的看着那第三幅画。
那幅画画的是三个僧人,一老僧打坐,一僧独立,一僧用手抚擦一面镜台。这次那秀才看了半天,也没能猜出那画的意思,不由得很是尴尬,低下了头。海瑞看了他一眼,心知这秀才读书并不太多,便道:“这幅画上的典故,说得是僧慧能悟禅的故事,也就是那首著名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由来无一物,何处落尘埃。’化成对句便是这《对韵》书中的一句‘慧僧抚玉镜,’而它的下句乃是‘潘妃步金莲。’”
他向着潘华淡淡一笑:“潘县丞,现在你应当明白了吧?”潘华的脸孔有些发僵,但还是咬牙道:“小人不明白。”
海瑞走了两步,扬声道:“齐东昏候幸宠潘妃,凿金为莲花,贴于地面,使潘妃行走其上,名曰‘步步生莲。’而你正好也是姓潘,你家中的地面是不是也用金做成的呢?”
潘华的脸一下子白了。海瑞喝道:“左右,立刻去潘华家中,仔细查看地面,看究竟有些什么物事。”潘华看着几名干办应声而出,他的全身都抖动起来。冷汗如雨。不发一言。
海瑞长出一口气,道:“现在,就让我将这案子从头到尾讲一遍,有什么疏漏之处,潘县丞再补充一二。”
他环视四外,见众百姓伸长了脖子,瞪大了双眼,屏住了呼吸,仿佛怕漏了他的每一个字。
海瑞喜欢这样的场景,虽然他已经历过很多次,但每次遇到这样的场面,都会让他神机泉涌,精神亢奋。
他平静一下思路,才缓缓道:“丽水县人民丰裕,市面繁华,但在我看来,县衙里却涌动着一股看不到的暗流,而且这股暗流已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就连县令陆大人也身处其中而无可奈何。因为这里从县丞主薄班头,到每一个衙役,都不是他的心腹,他已被架于空中,全无一点实际权力,甚至于连他发出的每一封公文都会被人监视偷看。而潘华才是这县衙里真正的县令。他指使杨真从府库中偷出银子,藏于家中地下,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以中饱私囊,又可以送陆光韶一个罪名,将他治罪,而最近朝中气象一新,圣上任人唯贤,丽水县治县有方,其中县丞起的作用自是举足轻重,上面一定会量才而用,将潘华升为县令。而且你也一定在应天府打好了关节,那日看你与鲁柯的神情,就知你二人曾是见过,并且还不算陌生。到时刘大人也说不定会举荐你。”
他看着地上发抖的潘华,道:“而我未到之前,你已向应天府举报陆光韶有私盗库银的罪状,那天你第一次见我进衙,误将我等认做应天府来人,所以才喊出一句‘你们来……’,那表明你一早就盼着他们。可后来你又对我说从未举报过陆大人,从那时起,我便对你有了怀疑。另外,那信差的行踪也是你透露给陈山的,陈山的班头一职是你保举的,他为了报恩,于是就同意了。你之所以要杀那信差,是因为你看过了他送给我的信,知道我要来,由此才动了杀机。你身为县丞,随便以一个理由就可以拆开信封,看过里面的公文,信差是不会怀疑的。那信差新来不久,与你并不是一路,所以你指使陈山也将他杀了。而你却错了一点,不该用拇指封那火漆,也就是从这一点,我知道陆光韶是被谋杀的。”
“至于你杀杨真,可能是他不再想受你指使,也可能是他向陆光韶透露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与兰香交往甚密,有可能对她讲出此事,所以你一不作,二不休,将她也一起杀死,又让一个女子假扮兰香来哄骗我,好让我相信杨真与陆光韶勾结,盗窃库银,而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但那个女子却误将玉步摇说成是玉搔头,露出了破绽。而且还有一点,那女子的身段做派,像是一个戏子,而你以前也曾在戏班客串,与很多女戏相熟,由此,我最终将目标锁定了你。”
便在此时,一名干办跑进大堂,手中拿着一块方砖,向海瑞面前一送,道:“回大人,潘华家中地面有一半果是用银铸方砖铺就,外表涂了青漆。现在已将潘家封锁,余人在那边看守,等候大人发令。”海瑞接过银砖,脸上露出了笑容,道:“潘县丞,现在你还不招么?”潘华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镇定,脸色死灰,口中喃喃道:“我……我……”
哪知那陈山突然大叫道:“你不要乱说话,你只偷了银子,却没有杀陆大人,那陆大人是我杀的。”潘华霍然回头,盯着陈山,半天才一字字道:“你给我闭嘴,这些人全都是我杀的,全都是,你只不过是个随从而已。”
陈山大吼一声:“哥哥!”这下子,堂上堂下的人全都怔住了。他们有很多人虽然知道两人关系密切,却也不知他们竟是兄弟。
海瑞看着陈山,不禁叹息道:“原来你们是亲兄弟,怪不得你会为他遮掩。虽说法不外乎人情,但天理昭然,谁杀人都要抵命。潘华投毒杀死陆光韶是不争的事实,而你陈山,先将杨真活活闷死,再用毒箭杀死兰香,前天夜里,你得到潘华信息,知道那信差会连夜回城,因为那是一份紧急公文,而我那时正好让你去知会四城,不要放人出入,因为那时我并没有怀疑你。而出城杀人的恰恰正是你陈山。你借着知会四城的机会,来到那陡坡边,将一条绳子横在官道中央,一头绑住竖在路边的一条铁棍,另一头缠在一棵大树上,等到信差骑马来时,将他马脚绊住,以致信差跌死。”
陈山用眼睛盯着海瑞,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为何要来?你若不到,一切便不是这样子。”
海瑞道:“国法如山,就算我不来,你们也难逃公理。”陈山大叫:“你自以为断案如神,可你知不知道,那陆光韶……”海瑞厉声喝道:“住嘴!死到临头,还敢诬蔑国家官吏,左右,给我拖下去!”
那陈山还要叫喊,一名干办用一枚铁胡桃塞进他嘴里,三个人将他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下去。
就在这时,潘华突然发出一阵凄惨的大笑,他笑得好悲哀,也好无奈:“世上难道真的有公理么?如果真有公理,我又何必四方流浪,讨饭乞食,如猪似狗,而有的人做过很多坏事,却还不是一样活着锦衣玉食,死后风光大葬。你说,这世上的公理何在?公道何存?”
海瑞正色道:“在我看来,为官者守正爱民,执政者为国谋利,商贾公平买卖,农夫用心田园,妇人相夫教子,百姓守法尽忠,便为公道。”
潘华冷笑:“可惜,这些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痴人说梦……痴人说梦……”他又冷笑几声,突然抬头问道:“是什么让你肯定我杀了陆光韶?难道他将我画上去不成?”
海瑞点点头,道:“他死时的晚上在做画时,可能已感觉到自己中了毒,所以在这最后一幅画中,指明了是你。”
众人看去,见那画上画的是一个宴会场面,几人坐在短几后面,一人正跪在前面,手中举着一盘鱼。周围有不少执戟武士。只见献鱼之人神情异常,面露杀机。
潘华瞪大双眼,一字字道:“鱼藏剑?”
海瑞道:“不错,这正是专诸鱼肠刺王僚的故事,这幅画看起来也不如前几幅工整,是因为当时陆光韶已来不及想《对韵》上的典故了,所以就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我,是为他送东西的人杀死了他。而近几天给他送东西的,就只有你。”
潘华看着那画,突然发出一连串的不知是哭是笑的声响:“陆光韶呀陆光韶,我虽然杀了你,但还是输给了你,因为你只有一点比我强,那就是你认识海瑞这样的人物。”
海瑞傲然直立,对潘华道:“你还有何话说?”潘华半晌无言,最后他抬起头,对着海瑞轻轻说了一句话,也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死后请将我兄弟埋在一起。”
海瑞看着干办将潘华带下,众人称赞着散去,叹息一声,独自一人坐在堂上,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宇,突然觉得世事竟是如此无奈,如此萧条。
十一
阳光又一次升起,虽然威力已小得很,但还是给了人很多温暖的感觉。
海瑞站在县衙堂前,看着天空一片白云飘过,若有所思。海禄凑近道:“老爷,这几天我们还不起程么?”海瑞道:“先不忙,现在县中无主,我要不在此弹压一时,恐怕出事,反正公文已送上去,朝庭不日便会派新的知县来。”
海禄欲言又止,海瑞看到,便问:“有什么话,只管讲来。”海禄道:“是关于此案的一些细小之处,我尚不大明白。”海瑞道:“哪里?”海禄道:“我第一不明白的,就是那杨真是如何将库银盗走的。那府库守得极严,出入都要盘查,那么多银子,绝对无法带出的。况且他就算与潘华合谋,那也只有两把钥匙。”海瑞道:“那钥匙已不是什么问题,杨真身为主薄,随时有理由可以入府库查点。陆光韶也不会怀疑。问题在于,他是如何将银子带出的。”
海禄道:“这就是我第一个不明白之处。”海瑞笑了笑,道:“其实我若一说,你就会觉得简单得很,杨真就是将银子藏于身上,骗过守门之人的。”海禄道:“那他是藏于身上何处呢?总不会吃到肚子里吧。”
海瑞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他屋子里看到的竹板?”海禄道:“记得。”海瑞道:“那竹板并不是防身的,也不是用来支帐子补窗子,而是用来固定假肢的。”
海禄瞪大了眼睛:“假肢?老爷是说杨真身上有假肢,是个残废?”海瑞点点头,道:“他被斩下的那条腿安有假肢,潘华因为不想让我知道,所以才砍下了他的腿,那晚不是有人看到林子里面有鬼火升腾么?想必是陈山将那假肢烧了。而那只手臂,因为少了一小块指甲,所以他们索性也将它砍去,又假借那个传说,掩人耳目。”
海禄道:“怪不得杨真平日行动缓慢,而且在大雨中也不快跑,他平日不露身体,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是个残废。”
海瑞道:“他那截假肢必定中空,去府库时先将铅条塞入,然后到库中将银子换过,依旧带出,所以外面是搜不出来的。然而由于里面塞入金属,假肢太重,所以他才用这些竹板加固。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海禄叫起来:“真的是这样!经老爷一讲,此事竟是极为简单。”
海瑞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疑惑?”海禄道:“就是那白玉屏风,是谁将那些画作呈现在老爷眼前的?守门干办说没有人进去过,难道真的是陆大人灵魂所为?”
海瑞哈哈大笑:“哪有什么灵魂所为,那只不过是陆光韶的一个小小把戏。你可看到他桌上那只木碗?”海禄道:“看到了,那又说明什么?”海瑞道:“这只木碗可是大有文章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水。”海禄道:“那些水不是洗笔用的么?有什么稀奇?”海瑞摇头道:“不,不是那么简单。那些水绝不是洗笔用的,你还记不记得,潘华与那仵作说陆光韶在死后手里还握着一枝笔,但那支笔上却没有墨迹?”
海禄道:“记得呀。”海瑞道:“机关就在这里。陆光韶笔上无墨,说明他死前并没有在做画,而是在用手中的笔向白玉板上涂抹着木碗中的水。而那碗水却不是普通的水。它的腐性极强,而且只能腐化玉石,而不能腐化木器。所以他用木碗装水而不用瓷碗。我头一次看到那玉屏风时,下面便落了一些粉末,我当时并没注意,后来想到可能是屏风上落下的,而又如何会有玉粉下落呢?直到你碰洒了那木碗,洒出一些水在地面上,我第二天去看时,发现那些水已渗入大理石地面,表面也有了一层粉末,这样我才明白,陆光韶就是用这个方法引起我注意的。”海禄道:“可他用的那种水是如何来的?”
海瑞笑道:“你如何忘记了?他父亲就是当地很有名气的雕刻家,想必是他配制出了这种奇水,才有可能让陆光韶为自己报了仇。”
海禄如听天书一般,半天才把那种惊奇的神色收回,不住的点头称赞。可海瑞的脸色却没有一点喜悦,相反,倒有些不快。海禄看出来,问道:“老爷在几天之中,就断了这样一件大案,为何怏怏不快?”
海瑞看了他一眼,目光中似有难言之隐。海禄又追问了一句,海瑞看看四下无人,才轻轻叹道:“我如何会快乐?这件案子还没完呢。”
海禄吓了一跳:“没完?凶手落了网,失盗的银子也找回来了,怎么说还没完?”海瑞道:“我问你,陆光韶是如何知道银子下落的?”
海禄一怔,想了想才道:“可能是他暗中查到的吧。”海瑞冷哼一声:“他若查到那些银子,为何不上报应天府?这样可以反客为主,将潘华等绳之以法,自己也免了杀身之祸,他为何不这样做?”海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海瑞叹息道:“想要解释也不算难,只有一种原因。”他盯着海禄,缓缓道:“那就是,陆光韶或许也是他们一伙的。”海禄的舌头伸出来,并天缩不回去。海瑞叹息道:“我也只是猜测,陆光韶在县衙中既已没有实权,当然是因为有把柄握在潘华手里,所以一切政令都是潘华做主。而盗窃库银之事,陆光韶很可能早已知晓,却不敢声张。也不敢上报,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潘华监视之下,只要有一点不小心,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潘华所说杨真进入府库后第二日,陆光韶也会进入一次,看来并没有说谎,他是去看看杨真一次盗取多少官银。做到心中有数。而这潘华平日的唯唯喏喏,谨小慎微,无疑都是装出来的,让人觉得县衙里仍旧是陆光韶做主。此人说来虽心计深沉,手段毒辣,却也不失为一个有能力的人,丽水县治理有法,倒有一大半是亏了他。”
海禄道:“可潘华为何要这样做呢?”海瑞道:“我猜想,可能有一半原因是潘华能力过人,而仕途不顺,心中积怨,另一方面,就是他与陆光韶之间的私人恩怨。他的四处流浪,衣食无着,可能也是因为陆光韶,后来想必是抓住了陆光韶什么把柄,所以他才会升为县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