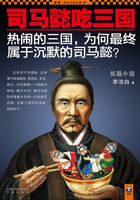101
清江古渡,暮色苍茫。
一抹夕阳照在高耸入云的火烧坪悬崖峭壁之上,明晃晃的返照出山河的孤傲和苍凉。河谷里江风凌厉,水流奔涌喘急,雪浪翻腾。两岸山壁陡立,怪石嶙峋,各有一条人工开凿出石板路,连接南北盐道。盐道西北通夷陵,东南通都镇湾能达湖南桑植,唐宋时代是通往夜郎的一条驿路。
这古渡名叫西沙渡,就是雍正年间,天门高士谭一豫为长阳司铎时,经常来此抱琴唱南曲的地方。土家诗人彭秋谭为此还写了一首《竹枝词》:“闻讯溪南七里硚,西沙渡口抱琴招。何人得似谭夫子,一曲平沙酒一瓢。”
如今唱南曲的高士不见人影,那只乌黑的木船却依旧横在野渡之上,一个赤膊着黝黑上身的船驾佬站在船尾划桡,船头还有一个年轻壮汉撑着长长的竹竿。不时有行人来过河,他便唉乃声声将渡船摇过来摆过去。
这船驾佬是个标准的山野夯汉,日晒夜露、风浪里滚得像一头大黑猩猩,却最是个苦中作乐的快活人,喜欢唱歌大喊、日白谈经。那都是从过客口里听来的,他也不知根苗,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喊叫嚷嚷图个解乏、消解冷清。当时他一边划桡,一边用嘶哑苍凉的声音,高喊着一首古老的歌谣:
什么时黑暗与混沌?
什么时天黑地不清?
什么时盘古来出世?
盘古又怎把天地分?
太阳月亮何时出?
何时又有满天星?
怎么会有风云起?
怎么会有雷雨淋?
......
102
这船驾佬也无正经名姓,世人只管叫唤他“乌驴子”,时年五十多岁,撑竿的壮汉是他的儿子。这乌驴子打了一辈子光棍,哪来这么大个儿子,说起来也叫人哭笑不得。
原来这渡河的男女老少,既有富贵宝眷、也有贫贱夫妻,还有旷男怨女、鳏寡孤独。偶尔碰到独行的寡妇剩女、又值早晚空旷,这汉子就故意赤条条地支篙摇橹。大山的女人也不乏嬉笑怒骂、敢作敢为、不怕摊灾的。有的跑上去就揪他的鸡巴,两人就在甲板上干起事来,往往浪打船翻也不顾。女人系上裤子,也就一走了之。
一个夏日的傍晚,天空乌云翻滚,山间风起树摇,眼看就要“跑暴”了,岸边却风风火火走来一位俏婆娘。
乌驴子一看,正是那招徕河最出名的俏寡妇张大秀,今天居然一人来过河。乌驴子早就想干她,没想到今日突然遭遇上了。他连忙把渡船拢岸,笑嘻嘻地迎她上船,然后一篙子把船撑到河中,丢下篙子就扑上去抱住她干起事来。
顷刻间干柴烈焰,一团风火就在甲板上翻滚起来。他们从船上滚到河里,又变成两条蛟龙绞在一起。一阵翻江倒海之后,乌驴子又爬上船来,将那婆娘倒提在手抖了三抖,拖上来摊放在甲板上,掰开两腿,跪在她面前。
张大秀尖声大叫、喊妈唤娘,乌驴子更是狼一般呜呜嗥叫。
两人正颠狂,却突然电闪雷鸣,狂风骤雨。一个金钩子闪射来、随即霹雳一声炸雷,把他们两个都打麻了,渡船便载着他们在金蛇狂舞中颠簸。
半响,两人醒来,犟了好一阵才挣脱。渡船已经流了一里多路,乌驴子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靠了岸。他哈哈大笑道:
“这回搞得好,你生了儿子就叫雷子啊。”
张大秀爬起身来应道:“老娘偏要生个雷公,也会打雷扯闪!”
她连裤子都懒得穿,抓起衣服,光着身子就钻进了狂风暴雨里。
这就是大山里赤条条的土家汉子,这就大山里风风火火的婆娘。他们像天柱山一样雄壮,他们像清江河一样奔放。他们扯起嗓子喊太阳,他们打起金钩勾月亮。他们的形象曾经被巴人刻成神秘的岩画,男人一根磐石巨柱,女人则画作两座山峰一道峡谷。他们孕育出土家人火辣辣的激情,成就大山里英雄豪杰和风情万种。
103
这乌驴子就想这样赤条条的无牵无挂的快活一辈子,他心里不曾挂记谁,也认为这世界上没有谁挂记自己。
没想到某年某日,突然有一个小伙子跳上船来,闷声嗡气地朝他喊道:“爹,我来跟你帮忙!”
乌驴子平生第一次听见有人喊“爹”,大为惊疑道:
“这可不能随便乱喊的,你是谁家的娃子?哪个叫你来的?”
“我妈。”
“你妈呢?”
“昨天死了。”
“你叫什么?”
“雷子。”
乌驴子好像想起了什么,又问:
“多大了?”
“十八。”
乌驴子望着这跟自己一个长相的娃子,想起了那次狂风暴雨,再没说什么,就收留下来,从此两爷子一起驾船。无论是兵荒马乱还是平安岁月,他们都守着这清江古渡过日子。
水边日月、渡口春秋,乌驴子渡过世上各色行人,见闻过人间许多奇事,常常一边撑船、一边说笑话喊山歌,在青山夕阳中嘻笑怒骂古今的王者和凡人。
104
这一日傍晚,过渡的人已渐稀疏。过河打柴的樵夫挑着柴火回去了,垂钓的渔翁也收起杆子回了家,乌驴子忙活了一天,也感觉累了,就想把船靠岸歇息。
可就在这时,他瞧见下游上来了一串大货船,每条船上都用蓬布扎得严实,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船前头都有二十几条赤裸的汉子拉纤,哪些汉子不像一般的纤夫,一个个体壮腰圆、行动十分敏捷。船尾掌舵的也不像一般的艄公,个个腿臂很白净,都把长辫子盘在脖子上,看样子凶得很。他们也不叫号子,只由领头的纤夫低声喊着:“一!二!一!”,好像当兵的下操一样,拉着一艘艘货船往上游移动。乌驴子数着共有七条,都一一经过了渡口。
他哪里知道,这其实是夷陵中军守备韩岳按照总兵冶大雄的命令,正带着一营官兵乔装打扮、骗过关隘盘查,秘密向都镇土司挺进,要去捉拿田坤如。这乌驴子只是有些纳闷,便朝他们骂道:
“这些牛日的,非要摸到都镇湾去过夜,就靠在这里几好。”
他最希望有上下的船只泊在这里过夜。这渡口白天倒热闹,夜里就僻静难熬,两爷子歪在岸边岩屋里,除了听见水流老虎昂,连个鬼火都看不到。只有泊舟过夜,船工纤夫就会在河滩上烧一堆柴火,叫他过去日白谈经,讲什么盘古的妈是鳖古,向王的爹是老虎,皇帝是猴王变的,五百年前我们都是一家人,五百年后我们又会在一个锅里吃饭。往往一壶酒传着喝、一串鱼烤了吃,快活大半夜。今日真是奇怪,这么晚了还有货船上来,而且一来就是七条,不知道装的什么好货,非要摸到都镇湾区过夜?那乌驴子嘟嘟囔囔骂了一通,便一盘腿坐在甲板上,自言自语说:
“格老子的,今年子赶歌会的人好多啊!比乙亥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