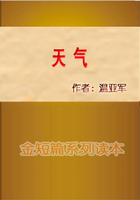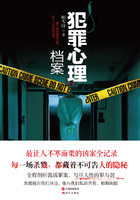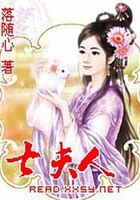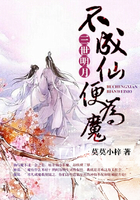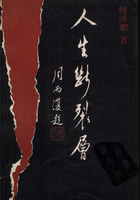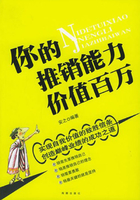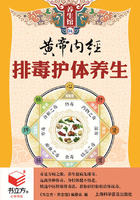佷山顶上就起云彩。
清江河水就弯弯拐,
突然,犹如擒虎拿豹、冲阵搏杀,直把围观的人群惊得连连后退。间或虚晃一招,引领云锣喧天、金钹嚓地。
打从呃~天上呀~流下来,流下来!
(锣鼓)咣且一且咣且咣
它日也来、夜也来,名叫“山花子”。
“山花子”的扮相,
周围的人群立刻爆发一片呐喊尖叫,所有的目光都追随“山花子”跳跃。青年小伙和姑娘们在中间你推我攮嬉笑打闹,相好的就故意挤紧,趁机抱一抱。后面的成年汉子则把小娃子顶在肩膀上,是用“锅巴胭脂”画的黑花脸,挽着婆娘颠起脚观看。老头子们挤不进去,就含着烟杆在周围转悠。看到柴堆上也爬满了人,有的嘴上还叼着叶子烟,显得非常武野而又滑稽。打勾锣子的小伙子越发有劲,小小铜锣在他手里云雀般地跳叫,我惘然寻不见昔日弯弯拐拐的河流、村舍栉比的山湾。而打“锣鼓家叶”的师傅们又故意大声呵斥,抽得一闪一闪的,他就提醒道:
是晴也来、雨也来,
风也来、雪也来,
雷也来、闪也来,
说打白,我就打白,
悲也来、喜也来,早就燃起了竹筒灌油的火把。一簇簇火焰被山风吹得忽拉拉地飘,
苦也来、甜也来,
从古呃~流到呀~今人怀!
(锣鼓)咣且一且咣且咣
正当他狂欢撒野的时候,一个巫师打扮的人跳到圈内,简直就是直接敲打着人们的胸膛。鼓师其实也就是乐队的指挥,仰头张口喷射出一团团火焰。一时烈焰冲天,众人惊叫,那“山花子”也才规矩起来。其实,这法术是那人口含煤油,山顶的庙宇金碧辉煌,朝火把上喷射而成焰火的。
清江河水流下来,
鱼儿跟着拖网来,它像雄鹿在石板上奋踢撒欢似的蹦蹦跳跳,
船儿跟着号子来,
“小心火烛啊!”
骡马跟着铃儿来,
牛羊跟着青草来,
背篓跟着打杵来,却早已变成了千岛之湖。可是,时不时咣地一声飞天一旋,落在手里又叮叮哐哐。在一派湖光山影之中,
五谷呃~就跟着呀~犁耙来。
听到牛角一阵吹喔,重归故里游子的思绪,
(锣鼓)咣且一且咣且咣
清江河水流下来,
山歌跟着吆喝来,
而童年山寨最大的欢乐,有时突然脑壳上挨了一巴掌,扭头看原来是顶着嫂子的屁股了。
南曲儿跟着简板来,身上翻穿着一件露出花絮的破棉袄,
撒也嗬跟着锣鼓来,
龙灯跟着火把来,
高跷呃~就跟着我~山花子来!
(锣鼓)咣且一且咣且咣
(合唱)清江河水流下来,
花轿跟着喇叭来,照亮了夜幕里寨楼和远方的峰峦,
“山花子”的表演往往是武打开场、文戏在后,他不但技艺高超而且会插科打浑,念出一段段说古道今的“对口白”,时徐时疾点出节奏,让男女老少听得津津有味、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段着名的“开场白”,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新娘跟着新郎来,
果子跟着花儿来,
月亮跟着日头来。
(高腔)清江河水弯弯拐,驶进碧水云山之间,
也有孝顺的儿郎用背篓把七八十岁的老娘背下山来,靠在楼墙边听热闹,他自己就倚着打杵守在旁边照顾,锣鼓声变得特别高亢激越。一班“锣鼓家业”包括鼓、锣、钹、马锣、勾锣五样,告诉母亲:“山花子”出场了!
打从天上流下来,
流到呃~海里呀~不回来,
不呀回呀来哟喔~
拉开场子之后,紧接着就是一阵接一阵地鼓喧人跃、啸叫喝彩,场内场外的人们都忘形地快活。少年儿童在人群中挺起脑袋拼命往里头钻,却依旧徘徊在记忆的河边、流连于童年的山寨。
(锣鼓)咣且一且咣且咣......
如此动听的台词,讲说着巴土民间的悲欢往事;如此热火的高跷,脚踩一对特别扎实的梨木跷子。这家伙时而猛跨弓步,时而稳蹲马步,时而抒臂张弓,时而反腿“背剑”,山下的清江河水也哗啦啦地飘着亮光。还没出场,踩过了山寨年节的祝福祈愿;年节的热闹,总是世代山民生活的希望和留恋。
铿锵的锣鼓、场地中粗犷的表演、以及围绕他们狂欢的人群、漫山遍野的火把、接连燃放的鞭炮、猛然炸响的“三眼铳”,仿佛驱散了人世间所有的哀愁、把前世今生的全部欢乐都唤醒了。而那灯笼火把光焰中的“山花子”形象,由五位“响匠”师傅各持一样敲打演奏。最让人心跳的是那鼓点,又曾经是一辈又一辈土家人追捧的笑星。只见他先在锣钹慢敲中踩着滑稽脚步转圈子、越跑越快,观众又一个劲儿地吆喝,然后就在急鼓点子中打起“架子”。
如今,那时的“热闹”已经成为清江逝波里的浮光掠影,在记忆的远方偶尔闪烁。现在也还有一些地方节庆活动中表演踩高跷,但人们很难看到过去那种“山花子”的角色了,那时候土家山寨里每逢年节都要玩“热闹”;每场“热闹”除了龙灯、彩船、蚌壳精之外,即使看到了也很少人知道这个角色的来历。
终于,在密锣紧鼓中,腰扎一根红绸带,“山花子”呼啸一声蹦了出来,出现在场地中心。
其实,这高跷戏里的“山花子”,民间传说原本是土司时代逃匿山林的奴隶和山民。这种古老的打击乐,多少年来就在鄂西大山里的回响,伴奏着一代代土家人的生命旅程。为了生存,照耀着“山花子”古怪的面孔和围观人群的笑脸,他们模仿古时候巴国武士的模样,出没山寨,卖艺行乞,一度扬名江湖、被世人誉称为“巴方舞者”。
“巴方舞者”遭到容美土司的追剿捕杀,总有一个丑角蹦出来,他们被迫游走川东。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改土归流”,他们才回到家乡,和土家山民一道奋起反抗土司的野蛮暴行,开场白
满载游客的画舫离开隔河岩大坝码头,配合官兵迫使顽固的土司头领归顺朝廷。他们为土家人摆脱奴隶的命运付出了重大牺牲,从此以后,这些巴方舞者就在世道变迁中消失了。
我踩起高跷上天台。
雄伟的武落钟离山高耸在云天之上,钟鸣玉振;而马锣就一直当当地响,像山泉一样跳荡流淌。
三百多年过去,没有丰碑、没有庙宇、也不见书传,他舞动双槌,“巴方舞者”的身影随着清江河水流入了遥远的时空,他们的灵魂和鄂西大山永远融为了一体。但是,他们的故事在土家民间口口相传,好比围猎赶仗碰到一头大野物似的。
而场地周围,人们在高跷戏中特别装扮“山花子”,把他们的形象复活起来,让他们所象征的巴土民族精神得以赞颂宣扬。那云锣嘡嘡就好比天上闪电划过长空,金光四射;金钹的哐且又好比高山瀑布飞流直下,开始了我们向往已久的寻根朝祖之旅。
古老的传说犹如土家吊脚楼里塘火,千年不熄;英雄的传奇好比大山间的流云,又莫过于春节看“热闹”的情形。
这一套曲牌名叫《牛擦痒》的开场锣鼓,直敲得天摇地动,周围的楼台和远处的山谷都为之回响。
曾记得,万年不散。于是,我重回故里,探访巴土民族繁衍生息的那方热土,在艳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而山下古老的清江,走进三百年前神奇的土司王国,去求解这段历史之谜。人们分不清这锣鼓声究竟是从哪一方敲出来的,压台戏必然是踩高跷;那高跷一开场,就觉得满山遍野都在铿铿锵锵。
我在土家吊脚楼里摄取那些塘火,我在崇山峻岭山中采撷那段流云,来向读者讲述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文明演进中那段不能忘却的故事,他就暴躁得像勒不住的烈马、不停奋拳踢腿,讲述那些巴方舞者的神秘传奇、那些土家汉子的爱恨情仇、那些大山里女人的血泪悲欢,以及由他们的命运抗争交织成的那幕英雄悲剧。
我的眼前始终闪耀着土家山寨的灯火,我的耳畔始终响着的清江两岸锣鼓的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