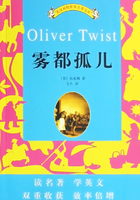话说到这,杜小手见牢里同蹲的这几位没人理他,接着道:“这有嘛了?再过一回热堂,我咬死了嘛也不说,就能出去了。这几天正好腰腿疼,在这里养养也挺好的。”杜小手是犯的偷窃,挨了五十下手板,这样的犯人进来,主要是打手板,用不着动水动火的大刑。市面上的贼人,都和衙门里面勾连着,平日里金银酒肉的没少孝敬,就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能得以照应,银钱使到了,板子上自然高举轻落,打出来也好看。平日里不肯孝敬银钱的,打时在你手下垫块木头,准叫你骨断筋折。但有一点,就是过堂的时候不能乱咬乱攀,审案的问一句:“同党还有谁?”你只管咬死了回:“没人”。大家都方便,挺过三堂热刑后放人。要是敢应声说:“还有谁谁谁。”那不等你把名字说全了,就能把你活活打死,因为你这是断了别人的财路。
旁边有早进来几年的穿街虎,冷哼一声笑道:“别做梦啦,你偷的是谁家?老城里的哈家,那是上三旗的皇亲!他们家健在的老爷子还顶着‘镇国将军’的封号呢。你偷他们家,你就等着把这牢底坐穿吧。”
杜小手撇了撇嘴,他知道人家说的有理,却还是不甘心地“哼”一声道:“什么镇国将军,这都什么年头了,革命党坐天下,他们家那什么将军早就不值钱了。”
穿街虎见他还嘴硬到底地抬杠,不耐烦地一脚踹过去道:“呸你个臭贼,人家就是没势力了,家里总有钱吧?顶不济人家使钱买你的命,一百两够不够?一包药就能把你弄死在这儿,还做梦呢!”这话彻底打掉了杜小手的心气儿,他长叹一声,蹲到角落里再无半句废话。
而此时此刻,家里丢了东西的苦主哈家七爷,正在小白楼一带没事人似的逛街呢。七爷这边头戴礼帽,身穿丝绸短马褂,手里头轻摇折扇,鼻梁上还戴着一副无框圆边墨镜。这身打扮着实惹人注意,宝德祥了高的伙计远远看见七爷,忙掸了衣裳跑过来,工工整整一个大千:“请七爷的安。”
哈七爷扫他一眼,脚下不停,眼神继续在两边橱窗里游走:“起来吧。”
“嘿七爷,这边不是紧挨着租界么,洋人多。我们家掌柜呢,就在前边开了个西餐的分号,这不刚开张,连洋人吃饭的规矩都摸不着呢。这今儿老天爷有眼,让您得空往这边遛弯来了,您是出过洋见过世面的人物啊,您赏脸进来坐坐吧,教教我们西洋人吃饭的规矩。有医治的秘方,就是花钱给狱卒买来生鸡蛋在手上托着,用鸡蛋将手掌上的毒火吸收出来,不然这毒火被憋了回去,轻者双手残废,重者十指连心,毒火顺着血脉进了心肺,那就是华佗来了也拽不回这条命。”
哈七爷笑了笑:“我说你这嘴,比你们后厨做的那道菜‘它似蜜’还甜呢。行啊,五个手指头与小水萝卜相仿。手上挨了刑,七爷我这还就有个好为人师的毛病,走着,我跟你看看去。”
几位伙计高接远迎地将哈七爷请上二楼单间,摆上刀叉菜肴,捧来一瓶红酒。哈七爷坐在正座上倒转扇子朝桌上一点道:“掌柜,头一样你这杯子就不对啊。”
旁边站着的掌柜马上招呼伙计:“这没眼力见的,还不赶紧换杯子去!”
伙计挠挠头,回到后厨用托盘端上来一大堆高矮胖瘦不一的玻璃杯来:“七爷,都在这呢,您看着哪个好使您就使吧。”
七爷一乐,展开扇子道:“小子,想考你七爷啊,今天七爷就让你长点本事。”哈七爷左手拢住袖口,右手将这些杯子一一摆在桌前,“这小方杯是喝威士忌的;这矮脚的球杯是喝白兰地的;这个高脚细腰窄口的是喝香槟的;这高脚的漏斗杯是喝鸡尾酒的;这小杯圆肚子的是喝甜酒的;这大肚子单边上带耳朵把的是喝啤酒的;这薄的是喝葡萄酒的,这最后一个是喝水的。哎不是咱这凉白开啊,是人家那矿泉水,洋文叫‘mineral water’。”
这番话当当当说得掌柜连同围观的伙计们两眼发直,小伙计苦着嘴道:“掌柜,这洋人吃饭规矩太多了,这一个杯子就能整出这些花样来,这可真不好伺候啊。”旁边有人附和道:“是呀,咱伺候不好他,洋人们摔盘子骂街不给钱是小事,要没吃好饭一怒之下再从大沽口杀上来可怎么办?”
这话逗得哈七爷哈哈大笑:“人家洋人讲文明,才不会像咱们爷们儿这样遇事摔盘子砸碗的,人家会一口不吃,给钱就走,这叫教养。但人家打这以后不但再不来你这儿了,还会告诉亲戚朋友别来你这了。”
哈七爷看着满脸苦笑的掌柜,起身拍拍他肩膀,边下楼边道:“我看啊,你也不必想给洋人做西餐挣钱,这是受累不落好的事,人家家里头随便做点牛排、沙拉什么的都比你这正宗。你就接茬炒中国菜卖给他们就行,当初咱李中堂办洋务的时候,一盘子宫保鸡丁吃的八国公使满嘴流油,他们哪见过这个啊。咱老祖宗爆炒腰花的时候,他们还就会烤肉串子吃呢。”
哈七爷说着走到楼下,临出门时摸出块大洋往柜上一扔道:“赏你的。”
那玩意儿一响一个窟窿,两响两个血坑。就是当年老佛爷手底下几万精锐,高墙雄城都没挡住的洋玩意儿。十几条洋枪围着我,我栽了不冤。”
七爷这边刚出门没走几步,后面急匆匆刹住一辆洋车,上面跳下来一个红面高瘦、身穿棉布马褂的年青人:“七弟,可算把你找着了!”
哈七爷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结拜兄弟肖秉义。
“七弟,人家吐口了,答应让给咱。不过……就是要价高了点。”
哈七爷问道:“要多少?”
“三百两银子,少一分不让。”
哈七爷点点头:“高是高了点,行啊,只要是真的就行。”
肖秉义忙点头道:“真的,绝对真的,明朝仇十洲的扇面,我看过的东西你还不信么?七弟你给句话,慕容无言
杜小手蹲在大牢里,要不要。”
哈七爷点头道:“要,麻烦哥哥您领这主家带东西上我家去,让管事的支钱给他。就说是我说的,让管事的多支十两银子给人家,既然咱爷们儿是夺人所好,那干脆大大方方的,让人家心里也高兴,以后咱还当朋友走着。”
肖秉义答应一声,上车就走,哈七爷忽然想起一事来,嘱咐道:“让管事的收好了,可别再让贼给偷了去。”
话出心动,哈七爷站在原处想了想,自己笑笑,伸手拦下了一辆人力车:“去府台衙门的监房,爷要去探监。”
这时候的天津监狱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延续了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兴建的名字,叫做“天津罪犯习艺所”,是近代中国第一座新式监狱。在十年之后才正式更名为“直隶第一监狱”。而杜小手因为刚刚过堂,还未移送至此,因此还蹲在天津府台的监房里。
监房管事的见哈七爷饶有兴趣地亲自来了,揣摩着这位爷难道是想要过过审案的瘾?便找了一间僻静的屋子,引哈七爷过去等,这样万一搞出些什么动静来,也掩盖得过去。
这边杜小手扛着铁链进屋,一眼看见哈七爷撇着大嘴坐在桌子后面,“哼”一声站在他对面,也不言语只等他问话。哈七爷眼皮一挑道:“怎么着?栽在我手里还不服么?”
杜小手犹自嘴硬:“怎么叫栽在你手里了,我是栽在那洋枪手里了,与你没有半点的关系。”
七爷冷笑:“枪把子攥在下人们手里呢,我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
杜小手道:“你这人好没道理,若是我拿了你家金山、盗了你家银山,你一枪打我一个对穿,我绝无二话。可我从你家屋脊上路过,本无骚扰之意。你没来由的用洋枪对我,这是……这分明是挟持,可见你们这些八旗人家往日里如何的嚣张。”
七爷忍不住站起来手指杜小手道:“你还说挟持,你还路过,你路过干吗用石头子扔我后脑勺?说到底还是你先出的手!”
杜小手恨道:“你这人真是蛮横,你大半夜的在院子里穿着洋装拉锯,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七爷呸一声道:“什么锯啊,那是小提琴,是西洋乐器,我那是望月生情,拉了一段曲子。再说了,就算我搅着别人睡觉,也用不着你出头啊?”
杜小手连连摇头:“乐器我见得多了,就算没见过你这外国锯,可你弄出来的那叫人声吗?木匠铺里伙计弄的都比你好听。我趴在屋脊后面听得浑身发冷,你就是没完没了。不出手提醒你,天都亮了,现在这双手如发糕般肿起来老高,我还怎么干活啊?”
两人你来我往矫情了半天,说得各自口干舌燥。哈七爷瞥见杜小手那两只肿成紫菜饽饽的手,叹口气道:“算啦,堂也过了。你也挨了板子,七爷我发发善心,撤了案子,保你出去。”
杜小手一愣:“你真要撤了案子,放我出去?”
哈七爷笑道:“你又不是杀人越货的强盗,不过是靠手艺养活自己的下五门而已。七爷我家大业大,就算真丢了点什么,那也不算什么。行了,你走吧。”杜小手抱拳正色道:“不论如何,七爷您让我少挨了两回板子,这份好意杜某日后必将报答。不过要说明的是,杜某不是下五门的偷儿,杜某乃是有师承的高买!”
苍茫暮色下,七爷赶回家门口,跳下人力车,门房里的老管家先迎了出来:“七少爷回来了。”
哈七爷边往里走边道:“我先去给阿玛请安,今儿下午有事么?”
老管家伸出手掌一件件地说:“您那义兄肖秉义来过,说您要买一个扇面,支了三百一十两银子走。宝鼎斋的薛老板说有新物件到了,请您有空时过去看看。商会的刘爷派人送过信来,说后天晚上他和有个英吉利来的大买办请你吃饭,到时他派车过来接您。还有……还有冠廷芳冠老板来过,说今晚在天仙茶园有她的攒底《穆柯寨》,请您有空过去。”
他腿快,老管家腿慢,哈七爷停下来回头应道:“义兄那事我知道,钱从我账上走。
别人在这时候,都会嘶嘶地吸着凉气,蹲在监牢狱一角老老实实转动鸡蛋疗伤,杜小手却还嘴硬着:“我这不栽面,我不是折在他手里,我是折在洋枪手里。薛老板那等哪天我闲了溜到他那再说。商会的那饭局是他们想跟人家做生意,知道我留过洋,请我过去给他装门面呢,不理他,爷没空伺候他。冠老板那……”哈七爷挠挠头,摸出怀表来看了看,“我这进去给阿玛请安,怕是一时半会出不来,再吃了饭换了衣裳,也赶不上。这样,你派人送俩大花篮过去,咱人不去,人情得去啊。”
吩咐完这些事,哈七爷撩了长衫下摆,急步往内院走。进得小院,轻推开外屋的门,蹑手蹑脚进去,正要跟当班的丫环问问,里屋传来一声咳嗽:“老七吧?滚进来。”
哈七爷笑着挑帘进屋:“阿玛,您这精神劲儿可是一天好似一天了,以前是我趴您耳朵边说话,您都跟我打岔。现在是我人还没进屋呢,您就听见我来啦。”
老爷子半倚在靠枕上,皮肤都被淤血涨成了黑紫色,板着的脸难得露出一丝笑容,伸手指了指床前的凳子:“唉,天天雷打不动地早晚都来请安的,也就是你了。这凳子每天也就是留着给你坐,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进来就知道要钱。”
哈七爷笑嘻嘻地坐下:“阿玛您宽心,哥哥们外边忙着正事呢,我这不整天闲着么。再说了,我来也是经常找您要钱的,只不过我要了钱都是来花在您身上。您瞧这是嘛?”说着七爷从兜里摸出一个锦盒来递给老爷子。
锦盒打开,里面盛着一个极薄的鼻烟壶,难得的是这鼻烟壶内外有画,外面画的是侍女,内壁画的却是山水,灯下映照内壁的画便透过来,好似这侍女立在蒙眬的山水中一般。
“我知道您好这个,特地找了来孝敬您,您喜欢就留下,等好了以后慢慢玩。”老爷子点头笑笑,脸上的刻板表情一时间冰消雪融,他将这鼻烟壶拿在手里摩挲了好半天,却放进盒子还给哈七爷:“花了你不少钱吧?拿回去吧,等我走了,这宝贝还不知被谁搜罗去呢。”
哈七爷将鼻烟壶硬塞进老爷子的枕头下面,嗔怪道:“瞧您说的,您老人家是南极仙翁转世,万寿无疆,金玉满堂。”
这句话听在老爷子耳朵里,他并没有像往日般微微一笑,而是眼望哈七爷长叹一声。哈七爷明白老父亲的心事,起身倒了杯热茶捧过来笑道:“阿玛您不用说了,等您的病一好,第二天我就出去找事做去。不过我也得说您两句,您真该宽宽心,这朝代更替乃是气数,人力难以挽回,您替那些个酒囊饭袋操心,气病了都没人知道。您何苦自己看不厌眼前这点事呢?”
这话说中了老爷子的心病,他喘了几下,强忍住咳嗽道:“你不懂,我是不甘心,不甘心啊。祖宗打下来的二百年江山啊……咳咳。”
七爷忙扶住老爷子,伸手在他胸前安抚顺气:“阿玛您看开点。这真是气数,再说了您也管不了那些个。您看看最后这几个辅政大臣有一个像样的么。头一个说庆王,他们家里的下人、厨佣都不发饷钱,去他那甭管什么事都得给门包,一份门包分两半,一半下人们分,一半归庆王。您说哪朝哪代有这么敛财的辅政王爷?再说摄政的醇王那多横啊,三朝老臣张之洞能让他六个字就给气吐血死了。咱爷们儿就是想使劲,能扛得住他三言两语么?”(注:张之洞之死据说因在是面奏醇王珍恤民情时,醇王答“怕什么,手托着生鸡蛋疗伤。刚刚过的热堂,有兵在”。张之洞恨此勒兵观变、自绝于民的亡国之言,而当堂吐血。)
老爷子只是长叹,再无言语。半晌过后,老爷子目视哈七爷道:“下人们有粗俗话说‘九犬出一獒’,我养了你们兄妹八个,只有你还有些做事的脑子,所以我送你出洋、供你留学,将来你可不要愧对我才好。”
哈七爷默默点头。过了片刻,老爷子哼一声:“今天不溜出去看戏了?”
哈七爷脸一红,笑道:“我得先伺候好您不是,等阿玛您好利索了,我再踏踏实实地看戏。”
老爷子双目中眼神一闪,正色道:“看戏可以,但想要娶戏子进门,绝对不行。”这句话正戳在哈七爷心里最疼的地方,不由得他眼神一暗,不自觉地将头偏向一侧。“别忘你上三旗的身份,那下九流的戏子别说娶进来,养在外面当小的都不行!你要是敢这么做了,我就是到了下面也饶不了你。”
哈七爷心中苦怨却不能言表,只好闭了嘴,用鼻子出了长长的一口气。父子两人就这般无话对坐着,灯光下竟没来由有了些清冷的感觉。
老爷子似乎察觉到了哈七爷的不快,他对这个小儿子是又恨又爱,他也明白子大不由父,哈七爷虽然顽劣,却很少做出格的事,更难得是有孝心,对他、对额娘的话向来是从不说二话。这上面比他这些兄长、姐姐已经强出很多了。想到其他几个子女,老爷子忍不住一阵心烦,想了想低声对哈七爷道:“你去把我书桌上的密码盒子拿过来。”
这是一个紫檀木的漆盒,四角包着银边,把口的是三位数的西洋棘轮密码锁。老爷子接过盒子,停了手问道:“你知道这密码是多少么?”
哈七爷愣了,他拧眉琢磨了片刻,试探道:“六零四?”
这回轮到老爷子发愣了:“你怎么知道的?”
哈七爷得意地一笑:“这么重要的盒子,一定会用重要的日子做密码。六月初四么,正是您老当年年轻时袭爵时的日子。”
老爷子有些吃惊地看着哈七爷,好半天之后才赞许地点点头,打开盒子,摸出一个锦盒递给他:“我也不能白要你的鼻烟壶,赏件东西给你吧。”
哈七爷好奇地接过来打开看,却是一个黄铜的扳指儿。扳指儿乃是射箭专用,满人骑射出身,戴扳指儿常见。扳指儿材质以前多用兽骨,入关后因身份的提升而武备放松,遂有金、玉、象牙材质的扳指儿出现。而老爷子拿出来的这个扳指儿非金非玉,而是普通的黄铜打磨成,上面刻海浪纹卷边,中刻饕餮面纹,隐有些许苍凉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