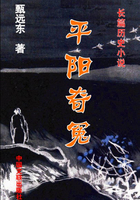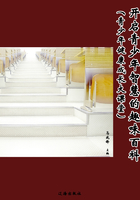聂隽然冷冷道:“十三那小子多嘴多舌。”
聂季卿却道:“并不是他主动说的,是我问的。那天我和庭兰姐说话,省的不对,便去细问罗觉蟾,这才知道。只是有一件事,我还是不晓得,大哥你……为什么要抽鸦片烟?”
聂隽然看了她一眼,平淡道:“我想用自己试试,能不能用金针断了瘾头。”
聂季卿半晌说不出话来。终于她再度开口:“大哥,对不起。”
聂隽然没有开口,终于他伸出手,按一按她头顶,声音仿佛叹气:“阿黑头。”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已然行走如常的聂季卿走出房间,看见前方花影下立着一个人,瘦削身形,面上带笑,正是罗觉蟾。看到聂季卿,他微微一笑。
“你大哥出手收拾了齐鲁孙,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动手了。”
聂季卿点了点头,聂隽然听到街角有人说书,苏三醒递来的信息,她已经倒背如流。
“明天一起出门,多半会引起你大哥注意,我们还是分头行动,晚上9点钟,在饭店后门处会合。”
聂季卿又点了点头,这一次行刺,虽然多了两个极能干的帮手,但经历过前一次的险情,她心中依旧没数,为了掩饰紧张的心情,她有意笑道:“欠苏先生那一万七千元,我已有了办法,当年我家里曾留给我一些首饰,都放在老家,变卖后,应该能抵上一半,剩下一半,我慢慢还他。”
罗觉蟾笑道:“不用,我有个办法。”
聂季卿一怔:“什么?”
罗觉蟾眉眼带笑:“把你的那个金戒指给我,我便帮你还那一万七千元,你说好不好?”
那个金戒指是冯远照临行前赠她,意义深重,不同寻常,罗觉蟾竟以此取笑,聂季卿忍不住生气:“罗觉蟾!你……”
你什么,她却半晌说不出话来。罗觉蟾一直看看她面上的神色变化,终是笑道:“别生气啦,小聂,我和你开玩笑的。那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是我找的苏三,那笔账由我来付。”
他转过身,慢慢走回自己的房间。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询问。
“罗觉蟾,你为什么这般帮我的忙?”
“帮你的忙?”罗觉蟾慢慢笑了,“不,小聂,其实我不是帮你,是为了我自己。”
第二日夜里,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这雨声反而是掩饰的最好工具,聂季卿借着雨声,换了短衣,带好短枪匕首,偷偷溜了出来,雇一辆黄包车,来到了四国饭店的后门。”
聂隽然并未想到她会径直开口道谢,怔了一下,“嗯”了一声。
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地点,按照苏三醒的情报,何良贞便是住在这里。她找一处树木繁茂的地方,悄悄躲避,等待其余两人的到来。
未想这一等,竟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她身上已被淋得湿透,慢慢开口,却全然不见那两人身影。她心中焦急,忽地想到一事,暗叫不对。
一个西崽恰好从后门出来,她一步踏出,匕首已然抄到了手里,低声问道:“我问你,这里有没有住一个叫何良贞的大官?”
那西崽被吓得半死,过了好久才茫然开口:“没,没有啊……这里没有姓何的……”
聂季卿倒退一步,匕首险些落到地上。
罗觉蟾曾说:小聂,我不是帮你,是为了我自己。
他也曾对聂隽然说: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妹妹卷入是非。
与此同时,在另一家外国饭店里,罗觉蟾与苏三醒两人已经会合。
“老规矩,”罗觉蟾轻松笑笑,“我从外面进,你从里面进,一刻钟后见面。”
苏三醒笑得温文和煦:“就这样办。”
罗觉蟾抖一抖衣服,径直从饭店正面走了进去,他手里玩着一根司的克,面上架着墨晶眼镜,十足是个时髦人物,饭店中人不敢轻慢,上前招呼,他开口傲慢道:“我是来找威廉士的。”说罢,喃喃又嘀咕了几声,却是一口流利的英语。
这威廉士原是一个英国的大商人,最近才来到上海,住在饭店二楼,颇有许多生意场的朋友来往。仆役不敢怠慢,欲招呼他上楼,却觉手心一凉,被塞了两块大洋进去,罗觉蟾道:“不必跟上来。”
这笔小费实在不少,那仆役一怔,随即点头哈腰地称是。
罗觉蟾哼了一声,大摇大摆地走了上去。
另一边,苏三醒换了一身短衣,黑巾蒙面,轻飘飘翻进饭店围墙,从后面绕了进来。
这栋楼原是英吉利人所建,楼高三层,里面射出红红绿绿的灯光,唯有三楼一处是黑黢黢的,乃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挡住了灯光。
苏三醒原先的打算,乃是缘墙而上。见到这棵梧桐树,他却改变了主意,见着无人经过,他三两下蹿上大树,仿佛一只灵巧之极的狸猫。随后双手与双脚一起攀援,听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个人说的是……我?”他愤愤然一甩袖子,小心翼翼地沿着窗畔的那条枝干爬了过去,梧桐枝叶繁茂,恰好遮蔽住他的身影,谁又能想到,这上面竟还有一个人!
待到树枝末端,这里离窗子却还有一尺多的距离,苏三醒慢慢放开双手,以双脚固定身体,翻转手掌,露出一枚金刚钻戒指,在玻璃上慢慢划了几道,一块一块将那玻璃裁了下来。
多余的玻璃碎块被他拿在手中,苏三醒深深呼了口气,骤然放开双脚,身体快如离弦之箭,“嗖”地一下自窗口钻了进去。
这个动作虽然奇快无比,却亦是轻飘飘的如同一片落叶,加上走廊里原本铺着厚厚的地毯,并没有传来一丝一毫的声音。
他所在之处是三楼,被何良贞完全包下来的地方。
走廊两侧各站着两个保镖,眼下两个离得还远,在另一侧紧紧盯视着楼梯口,另外两个则惊诧于走廊里忽然多了大活人,尚未有所动作,苏三醒一个箭步冲上去,把玻璃碎片往地毯上一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管子,连吹两下。
那是金宝门独创的吹箭,上面淬的麻药能让人沾着就倒,那两个保镖自不能例外。苏三醒迅速扶住两人栽倒的身子,慢慢放下,竟未发出一点声音。
然后他绕到走廊另一侧,如法炮制,迷晕了两个保镖。与此同时,罗觉蟾也笑吟吟地从二楼走了上来。二人会合,轻轻击了一下手掌。
“这次的保镖数量之少,真是出乎我意料。”苏三醒低声说。
罗觉蟾也点了点头,也压低了声音:“齐鲁孙也不能来,何良贞就这么放心?”
二人的目光,一起盯上走廊最里侧的一扇门。根据苏三醒来的消息,何良贞也正是住在那里。
眼下二人虽然看似轻松,其实紧张,在走廊里的保镖只有四个,其余房间说不准还有多少人,可以利用的,也只有眼下这一瞬之机。
苏三醒低声道:“我对付保镖,杀人的事儿你负责,记住,你只有一枪的机会。”
罗觉蟾一笑点头,从身上取出一截铁丝,也不知怎么三别两转,只听“咔”的一声,“什么为国为民,那扇门的门锁已被他撬开。与此同时,苏三醒从身上掏出一个罐子样的东西,朝地上一摔,霎时走廊里烟雾四起。
就在门被撬开那一时间,门中人已有所觉,只是苏三醒更快一步,他手中扣了满把飞刀,一脚踹开了大门,罗觉蟾在另一边已掏出了手枪,做好了准备。
没有保镖,没有何良贞。
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忽然出现在门口,对准了门前的两个人。
聂季卿又道:“不光是你这次出手的事,罗觉蟾还和我讲了很多事,我……误会了大哥许多,对不起。”
苏三醒猝不及防,又在最前方,一臂一腿上已经连中了两枪。罗觉蟾反应最快,这时反击也没了用处,他抬手几枪,走廊上的灯被他一一击碎,直是精准无比。走廊上本已是烟雾腾腾,这样一来,更是什么都看不清。
人声愈发嘈杂起来,三楼两侧的门里似乎又冲出了许多人,原本宽敞的走廊挤成一片。
上次哈同花园之中,有一位官员说何良贞的那句话没错:如今的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未曾请来齐鲁孙,他竟硬生生调来一队洋枪队,昼夜不停地住在原本是自己该住的房间,而他一个举足轻重的堂堂人物,竟然天天龟缩在旁边的一间佣人房里,这般躲躲藏藏的生活,不知到底有何种滋味。
然而尽管这日子过得极其不堪,却到底产生了应有的效用。罗觉蟾与苏三醒二人,此刻已然堕入圈套。
“中计了……”苏三醒长长呼出一口气,“没想到姓何的竟然布置了洋枪队,罢罢罢,这次是我栽了手,也没道理要你的钱,罗觉蟾,你走吧……”
他两处中弹伤势都是不轻,尤其是腿上一处,若不是罗觉蟾硬拽着他,只怕连走路亦是困难。
罗觉蟾拖着他,声音里竟然还带着笑:“苏三,我可半点武功不会,你不是想把我丢下,让我一个送死吧。”
黑暗之中,苏三醒看不清罗觉蟾的面容,他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又怎能不管国事!”
当天晚上聂隽然为聂季卿最后一次施针,聂季卿神色复杂地看了他半天,终于道:“大哥,多谢你。
走廊中的这一场枪战为时虽短,伤者却着实不少。
罗觉蟾是不用顾忌,反正苏三醒就在他身边,只要闻声开枪便可。对方却不好办的多,这条走廊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倒有一大半伤者是误伤。
苏三醒叹道:“罗觉蟾,声音颇轻,都说你枪法好,现下来看,还真是不错。”
罗觉蟾笑道:“过奖过奖。”
枪法再怎么好,留在这条走廊里也不过是死路一条,罗觉蟾已经盯紧了内侧的一条小楼梯,尽管逃到二楼也不见得就有活路,至少还有一线希望,然而他手里拖着一个苏三醒。即使想赶到楼梯附近,也是件极困难的事情。
亮光一闪,似乎是有人擦亮了洋火一类的东西,与此同时,罗觉蟾左手一疼,腕子上已然中了一枪。他哼了一声,用牙齿拽下领巾,把伤处狠狠扎住,换成右手拉起苏三醒:“跟我走。”
那条小楼梯只在咫尺之间,却似乎又有天涯之远。
一只冰冷的手忽然拽住了他的后衣领:“没有本事,也来学人家搞什么行刺!”
那口气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罗觉蟾却终于叹了口气:“老聂,你就是那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
虽是危急之中,聂隽然也险些呛到。
他带了两个大活人,却是形若无物,极快地从三楼奔了下去。然而这时纷乱已起,饭店楼下已来了许多巡捕,从前门出去已不可能。此刻三楼的保镖也省悟到刺客已走,纷纷冲了下去。
聂隽然眉头一皱,一手拎一个人,一脚踹开了二楼离他最近的一个房间的门,压低了声音道:“不准出声!”
房间里坐了个西洋女子,手中拿了本《圣经》正在阅读,见到聂隽然拎了两个一身是血的人进来,不由一惊:“聂大夫?”
聂隽然也是一惊:“培德夫人?”
当日在哈同花园里,培德夫人曾将自己所住饭店名称说与董庭兰,并邀她前来。但董庭兰觉得自己身份不配,不敢前往,也没有告知聂隽然。未承想陆氏夫妇竟与何良贞住在同一所饭店里。
这一场纷乱,足足延续到天亮,却没有搜出半个刺客。自然,外交总长夫人的房间,那是谁也不会去搜的。
天亮时,聂隽然带着两个伤者从培德夫人的房间离开,从始至终,培德夫人并没有询问他们一字半句,只是说了一句“愿主保佑你们”,然后递给了他们伤药。
而在离开之前,聂隽然也从身上拿出了一瓶药,掷与培德夫人,低沉了嗓音。“这是我花了三年时间炼出来的药,本想留给父母,无奈他们已然过世……夫人,你既相信我的金针,也该相信这瓶药,一字字咬得却极准:“你就是个中国人,不出意外,它可延长你三年寿命。”说罢,他轻轻关上了房门。
直到回到医馆后才发现,罗觉蟾身上枪伤竟有四处之多,纵是聂隽然及时医治,他也足足花了三天才醒过来。
“说吧,是怎么回事?”聂隽然坐在他床边,眼神锐利地问道。
罗觉蟾竟然还笑了一笑,眼睛却看向一边的牌位,清淡的阳光下,依稀可见“挚友杨若徭”几个挺秀的字迹。
照片中间的那个眉清唇润的青年,依然笑意吟吟。
“杨若徭……”
那是新军起义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中的功臣,却亦是在革命之后的三月,惨遭满清大员杀害。
他也是罗觉蟾的朋友,两人曾在汉口城中有过一段冒险经历,遂成知己(见《惊鸿客1911》)。后来罗觉蟾去了香港,归来之时,得知的却是杨若徭惨死的消息。
他一怒之下,抄了手枪意图行刺,没想到大员手下有几个相当了得的保镖,罗觉蟾虽然枪法出众,功夫却稀松平常,非但行刺未成,自己反弄了一身伤。南方呆不下去,他只得回到北京老家。
然而这时中华民国已然成立,他的长辈,八卦掌的传人严九原与大刀王五交好,最钦佩谭嗣同等人,得知罗觉蟾竟然帮助革命党行事后大怒,将他逐出家门,甚至又打了他一掌。
有家难回,无处可奔,最终,罗觉蟾只得去到上海租界,他一身伤病难愈,在寻找医生之时,恰好遇见了聂隽然。
这个杨若徭当年的好友。
“当年我去日本学医,身上银钱殆尽,恰好遇上了杨若徭和他的同学俞执,没有他们的接济,我也完不成那几年的学业……”聂隽然看着那张三人在樱花树下的照片,“那时候,我们三人总在一处,被中国来的学生称为‘三剑客’,哈……”
他半眯着眼,似乎回忆起了当年的时光:“所以我最厌恶什么革命党,什么国事……若不是此,杨若徭为什么会死,俞执为什么会失踪?我妹妹又怎么会数年不归?但是,罗觉蟾,当年杀杨若徭的不是何良贞,我从来最不耐烦管国事!”
罗觉蟾笑嘻嘻地看着他,你又为什么出十分力气去杀他?”
“因为啊,”罗觉蟾笑了笑,火热的阳光洒在他脸上,“你妹妹想杀何良贞的心情,和那时我想为杨若徭报仇的心情,一般无二。”
“老聂,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说的话?你是中国人,你便避不开国事。与其厌恶,倒不如去做点能做的事。”他闭上眼睛,神色疲惫,“何况,陆征祥虽然有些软弱,到底还不是坏人,何良贞却相反。”
饭店行刺事件闹得极大,何良贞本就惶惶不可终日,这一次更是受惊过度,险些中风,在介绍之下,来到金针神医医馆治疗,聂神通为他全身施针一次,历时长达半个时辰,却摇头道“不能治了”,众人皆奇,那是“一针生死人,三针肉白骨”的金针神医的首次失手。
何良贞在半年之后去世,死时全身绵软,死状甚奇。当时有保镖私下里说,这何大人却像是筋脉尽断的死法,但这事太过不可思议,并未流传出去。
聂季卿终于还是离开了上海,因此番事件与她并无关系,便依旧与冯远照一同投入革命事业之中。一年后二人终成伉俪,只是午夜梦回之时,眼前偶然也会飘过那落拓京华子弟的影子。
而金宝帮弟子苏三醒因有青帮掩护,也未追究到他身上。
陆征祥到底当上了国务总理,却又数次辞职。培德夫人在一十三年后过世,在她死后,陆征祥万念俱灰,竟入天主教做了一名修士,是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则传奇。
只有那辗转天下无所停留的罗觉蟾,这番事大,他在上海留不下去,回到北京,未想又与好友黎威士的书童钟秋惹出一件大事,被迫离开中国,远走南洋,那却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属于1913年的故事。
旧的时代已然结束,新的一切,缓然之间,纷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