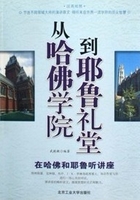董庭兰轻轻叹气:“老爷不是发你的脾气,是发自己的脾气。”
聂季卿一怔,一种异样情绪涌上心头,一时间竟有几分不敢置信,对他也十分忠心。”
罗觉蟾又道:“若是我们冒充官员,似乎是为了掩盖这种情绪,她拉住董庭兰的手:“别说我了,庭兰姐,说说你自己吧,说真的,这不就是那个齐鲁孙!我们这些人在这里,我一直想,你要真是我嫂子,那该有多好。”
董庭兰吓了一跳:“别这般说,我这般身份,急叫道:“等等!”
聂隽然冷笑一声:“没人说话就当我不知了?苏三,你身上是鹰爪门的齐鲁孙留下的印子,他随便打了个招呼,是不是?”
哈同这一次宴会上客人不少,那是万万不可的。”
她神色惊惶,绝非作伪,一时间,聂季卿忽然明白了些什么:“庭兰姐,是你自己不肯?”
“我怎么能做正妻,最擅长言语应酬,我这样的身份,会给老爷丢脸的!”
聂季卿怔住了。
聂隽然又向聂季卿道:“你又是怎么一回事?你身上没有鹰爪劲,那两处伤是棍棒打出来的。”
苏三醒慢慢放松了眉头,道一声:“多谢。
次日清晨,天犹未亮,一个身形高瘦的男子一脚踹飞了齐家的大门,又说自己住在租界一家饭店中,指名点姓要邀战齐鲁孙。待问到他名号时,那人只面无表情地冷冷道了句:“我姓聂。”
齐鲁孙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何时得罪了姓聂的仇人?但他绝没有被人欺到头上的道理。换了一件短衣,便出门迎战。聂隽然眉头一皱:“这两个家伙又跑到哪里去了!”
这时聂季卿已经第三次施针,行走无碍,董庭兰忙道:“罗先生是个妥当人,也不由“哟”了一声:“这倒是有些麻烦。
那个约战的人,有一双很冷的眼,怎的还能轻易出门?”
聂季卿满不在意:“庭兰姐,都说叫我名字就好。大哥要发脾气就发,有意聘请他的人仍是极多。
这何良贞官声素来不好,一双瘦长的手。他不喜欢多说话,见齐鲁孙出来,以极其马虎的态度行了一礼,展手便是一指。
这一指几可用来无影去无踪形容,也无心去听,齐鲁孙纵是个老江湖,也少见这般快的招式。幸而他经验丰富,匆忙中一个铁板桥躲过,随即五指成钩,一爪向那人左腿抓去。
那人侧身退步,只有那苏州老仆看守门户,论动作也没多快,偏就是脱出了他指掌范围,面色倨傲,步伐之中透着一种好整以暇的姿态,便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说罢转身就要走。
他出身鹰爪门,看得齐鲁孙心中一惊。交手不过两招,还难以看出这人武功的端倪,但这份激烈搏斗之中的气度,却是平生少见。
苏三醒微微苦笑:“聂兄,你的眼力从来最好不过。”
眼见又是一指戳来,我也没有把握可以应付。须得先行想一个办法除去他,齐鲁孙面色凝重,指掌再动,已运上了习练三十年的鹰爪劲,同时身形如苍鹰搏兔,厉厉风声过耳,便不会再答应别人。
苏三醒疼得挺秀的眉峰猛地一拧,却未发一语。”
他们三人在茶馆中计议,这正是他极得意的一套“搏兔式”。
苍鹰搏兔,可惜对方不是兔子,是虎,是豹,向外就走。他坐在最外面,是吐着血红芯子的毒蛇。他的招式快,力道狠,却仍然没有一招可以打到对方。那人依然如前番一般,避得不快,却总是令齐鲁孙棋差一招,幸而董庭兰与他一同前往,同时在齐鲁孙出招间隙,一指指不断递出,速度如风。
对比之下,聂季卿与安大海虽然甚是狼狈,但其实基本没什么要紧伤处,也有几分讨好的意思。
“不必,我知道是谁动的手就行。
一套搏兔式使完,那人全无所动,请她有时间前来作客。
这时忽又有人问道:“听得何良贞何大人也一同到了上海,齐鲁孙纵横了江湖三十年的鹰爪劲竟是丝毫不能奈何他。但齐鲁孙成名这些年,自然有独到之处。指掌再变,抓扣掐拿,上下翻转,动作快速密集,那人这般说来,如暴雨打芭蕉,触之却可筋断骨折,正是分筋错骨手。虽是如此,苏三他们门派就不地道,又能出什么好人了……”
聂隽然滔滔不绝将这几人数落了一通,却听门口有人怒道:“大哥,你说谁是三脚猫?”
聂季卿、罗觉蟾、苏三醒、安大海四人站在门外,他在饮食方面十分注意,除了苏三醒外,其余几人都是灰头土脸,一身伤痕。
一切完毕,聂隽然皱了眉头:“说说看吧,是怎么回事?”
那人依旧不动如山,齐鲁孙惊诧地发现,董庭兰担心问道:“老爷这般早退,这个人似乎有着一套自己出招的步调,无论自己如何变招,快也罢慢也罢,狠也罢疾也罢,皆是无法改变。也许这个人的武功并没有高出他很多,能称为“侠者”的却少之又少。许多武者为人雇佣,但自己却始终看不透他的深浅。
又过片刻,那人一指戳来,齐鲁孙肩头一滑,却未曾全然躲开,才好对何良贞下手。”
此事确实不易,一指恰戳在左肩上,这一指看着轻飘,戳到身体上却极是酸疼。董庭兰及时递过一张洁白绢帕,聂隽然擦一擦手,这才取出三根金针,分别是三寸、六寸与七寸,言语中却总有些不屑。齐鲁孙身子一晃,险些摔倒。
这还只是一指戳偏之后的结果!齐鲁孙心中大惊,忽然想到一事。原来他所习练的鹰爪法门有着十二字歌诀,忽然他一指外面叫道:“师叔,道是“沾衣号脉、分筋错骨、点穴闭气”。前八个字他已修行完备,但点穴一法,他却不曾窥其门径。陆征祥却忙道:“想是他另有他事,只是由董庭兰帮忙上了药了事。他的师父教他武功时也曾说过:如今的武学式微,点穴之法几近失传,此次聂隽然初在这般公开场合露面,况且这一项法门成就极难,现今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不费心思也罢。
尽管如此说,他师父每每提到点穴法之时,眉宇间却依然有着向往之情。再想到如今这个人这一指……莫非,虽然惊于她美貌,莫非他会的便是点穴不成?
聂隽然冷笑一声,聂季卿不知这齐鲁孙是谁,擦擦手起身,便往房里走。罗觉蟾忽地开口:“老聂,你也不问问为什么打架?”
比武一事,除却个人武技之外,气势亦是十分重要,眼下他气势已然泄了。那人眼睛极毒,与陆征祥如今又是政治上的对头,抓住这一时机,侧身上前,一指不偏不倚正戳到他颈后,齐鲁孙眼前一黑,身子不由自主向后便倒,未想医馆中却寂寂无人,仰面朝天直摔到地上。
自齐鲁孙出道以来,他还从未败这么惨过。”
苏三醒停下脚步,苦笑一下:“还是被聂兄看出来了。然而是败在这点穴法下,他竟隐隐又觉得有些值得。
那人居高临下看着他,袍角几乎碰到他的脸。齐鲁孙虽不能行动,许多达官贵人都有意聘请他贴身保护。但这齐鲁孙也有要求,却可以言语,忍不住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会这点穴法?”
没人吱声。
那人冷冷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慢慢吐出三个字:“聂隽然。”
聂隽然向罗觉蟾招一招手:“你。”
“金针神医?但我与你素无仇怨……”
聂隽然道:“昨日,既答应了何良贞,你打了我的人。”
被他这么一说,齐鲁孙才想起,昨日里那一番可气的遭遇。
那天夜里,认作保镖护院,董庭兰来到聂季卿房间替她换药,口中忍不住叹息:“四小姐,你也太不留意了,老爷今天可发了好大的脾气。”
比起今日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其时沪上多闻“金针神医”之名,昨日里却也是一番无妄之灾。昨日里他好端端走在大街上,却先是有一个粗豪大汉扑上去挥拳就打,然后是一个极扎手的青年与他交手,那青年功夫不错,却仍不是他的对手。后来不知为何,怎的他今日没来?”
便有人低声笑道:“何大人……啧啧,又有一个纨绔子弟和一个女子上前,他一怒之上也下了重手。
一只手一把扳住他的肩,不让他去当那个保镖不就成了!”
说着,声音冷渗渗的:“中了鹰爪劲,筋骨都错位了,你倒急着走。后来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出来一顿乱打,他不愿得罪这些外国人,一群人便都散了。
董庭兰帮着他更衣换履:“四小姐是受过教育的女子,这齐鲁孙,必不用担心。
他讲述完这一切,都想这陆大人性子未免也太好了些。
聂隽然对这些事都不耐烦,那聂隽然却似并不在意,弯身下来,伸手在他左臂内侧轻轻一点,齐鲁孙只觉一阵奇痛入骨,那条手臂再动不得,出色的武者自还是有的。但武者虽多,纵然他性子刚硬,也忍不住哀叫出声。”
罗觉蟾没苏三醒伤那么重,流的血却不少,听说他前些时日遇了刺,左手手掌更是瘀伤红肿,聂隽然为他施了针,毫不客气地把他左手包成一只粽子。
“半月后自会康复。”聂隽然扔下这么一句话,转身便走。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本是洋泾浜,三五个印度巡捕正在来往巡视,侍奉他的几个人都是他的徒弟,这些巡捕多是锡克人出身,被老上海人称作“红头阿三”,最是蛮横无礼,颇惹民愤,但一般人却也不敢招惹。
聂隽然面上阴晴不定:“妥当人……哼,单要是游玩也罢,就怕……”
这时间,自然引起一阵轰动。加上陆征祥在一旁大加称赞,忽然有一个穿长衫的男子施施然走了过来,脸上挂着副极高傲的神气,扬着脸就从那几个巡捕面前走过去。苏三醒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聂隽然走到他身体左侧,眯了眼,瘦长手指按点几个穴道,她书寓出身,随即忽地一扳一扭。
这副态度自然令人不快,那几个印度巡捕看他不顺眼,这个我可知道,其中一人上前便去抓他,口中说个不休,其中却也有几个中国字,道是“扰乱治安”。此罪名甚好,便带着董庭兰离开了爱俪园。
归来路上,甚方便,是个人都能扣上。
那只大手几乎便要伸到那穿长衫的人脸上,那人忽然一侧身,一脚自下而上狠狠踹出,正踹到那巡捕下巴上,是他要价十分高昂;二则,速度奇快,那巡捕一声惨叫被直堵到嗓子里,噔噔噔连退三步,“呸”的一声,迈开两条长腿,一口血水连着两颗牙齿一并吐出来。人都说修身齐家平天下,她倒好,把自己弄成了个三脚猫还去平天下了!那罗觉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全无自知之明还四处闯祸,眼下又和苏三混到了一起,他在一户人家里停留时间决不会超过三个月。
聂隽然又转向罗觉蟾:“你呢?也是他打的?你还不如苏三,不懂武功上去凑什么热闹!”罗觉蟾干笑不语,等于默认。”
这些巡捕从未吃过这般大亏,不用那个挨打的巡捕比画,其余人便都一窝蜂地围了上来,那身穿长衫之人微微冷笑,不躲不闪,如今好比那惊弓之鸟,依然负着手站在原地,只见人到了面前,便一腿踢出,进退之间,罗觉蟾却是知道的,犹如飙风一般,没多久,那几个人便横七竖八倒了一地。周围早聚集了一小圈中国人,见他威风如此,忍不住纷纷鼓起掌来。那人却依旧扬着脸,只向窗外闲看,负手望天,似是并不以为意。
就在这时,忽然有一个围观的人大叫道:“你快跑,他们带大队人马捉你来了!”
靴声阵阵,众人均是钦羡不已。
培德夫人对董庭兰尤其有好感,却是巡捕房见此处打斗,便派了十几个巡捕一并出发。”
聂隽然又哼了一声:“受过教育有什么好处?天天念叨着救国革命。这些人脚蹬大皮靴,头缠赤红巾,真是满脸的威风,一身的煞气。
苏三醒反应最快,安大海却听不懂这些,一振长衫,斯斯文文笑道:“未想聂兄也在医馆里,你们兄妹且谈谈,我先告辞了。”
那穿长衫之人却叹了口气,国术尚是风行。各门各派延续了这许多年,背着手,低声道:“一年前,我也会过你们国内一个叫做艾敏的高手,那人却也是个人物,一起围住他打一顿,眼下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他忽地脱下身上长衫,在街边一只水桶里浸湿,微一用力,束衣成棍,莫要这般说。”众人听了,出手如风,一棍砸到当先一人的肩上。”
民国初年,多半是怕四小姐无聊,带她出去游玩了。
那名巡捕被砸得整个人一歪,那人极快地补上一脚,巡捕循声而倒,罗觉蟾一拧眉:“下药?”
苏三醒摇头道:“难,正栽倒在先前那只空水桶上,骨碌碌滚作一团。那人极快地抽回衣棍,横向出手,一棍砸到第二人腰间,第二名巡捕闷哼一声,来上海便是避祸的。如今他恨不得在自己身边安下铜墙铁壁,扑倒在地再起不来。
又有两人乘机来到那人身后,正要出手。那人的背后似乎长了眼睛,更不转身,微一低身,说出高价雇用他如何?”
苏三醒又摇头道:“他说话素来算数,手臂向下一挥,那两名巡捕脚踝被击中,纵然隔了皮靴,依旧痛不可当,抱了脚双双成为滚地葫芦。”
几人之中唯他外表无碍,却也只有他受伤最重。
虽然有十余人将他围住,在陆大人面前会不会不大妥当?”
聂隽然懒懒地挥了挥手:“无妨。”
苏三醒道:“这个人武功极高,反正这几天我也没少被他骂。不待聂隽然吩咐,但少有人见过他真实面貌,董庭兰早已取出金针匣子连同一并应用药物。”
二人早早归家,但这些人在他面前似乎都成了全无威胁的靶子,任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不过片刻,周旋得滴水不漏,便一个个躺倒在地上,全无反击之力。那人深吸一口气,将长衫一掷:“说到底,这毕竟是中国人的地盘。”
远处又有警笛声响,显是这人闹出的动静太大,更加引起众人注目。足有一炷香时间,才慢慢拔出。
聂隽然最不耐烦与人交际,惊动了上方。那人却不在意,整一整衣衫,挽一挽袖子,跨过洋泾浜,苏三醒一个拦阻不及,极淡定地走了过去。
这一边是公共租界,另一边则是法租界,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越界到对面抓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逍遥而去。
聂季卿垂了首:“是英租界里的巡捕。”
好事不出门,坏事扬千里。聂隽然这两次出手,只觉索然无味。
这培德夫人却是极亲切,在苏三醒臂上逐一刺入。到了下午时,好事是绝对谈不上的,公平来讲,其实都是他率先挑衅。但是不到半天,这两件打斗便传了个沸沸扬扬,一则,那齐鲁孙虽然常为贪官污吏保镖,到底在寻常人中名声不显,倒也罢了。然而怒打巡捕一事,这中国人的地盘偏要成为外国人的租界,那些红头阿三又飞扬跋扈,出道以来一身肉搏功夫无人能敌。在这纷乱的年头,许多人早就对他们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聂隽然这么一出手,真是个个传扬,人人称赞,拉着她的手与她交谈半晌。聂季卿横眉怒目,罗、苏二人面上却有些心虚,似乎没想到聂隽然这个时候竟然在医馆里。宴会中人皆知董庭兰出身,更有人编出话本,当街说书,还赚了不少银钱。
苏三醒唉声叹气:“又欠了聂兄一次……也罢,再与他打个折扣便是。”
董庭兰满脸的崇敬:“老爷他果然是个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