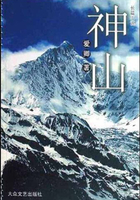文/金国栋
浩森原来不叫浩森,他是我表哥,五行缺金,于是他叫金鑫。现在他叫金浩森。
改了名字之后,浩森的生活轨道就大大地改变了,原来我们一起上树掏鸟蛋,现在我还上树,他会在树下大叫,保持住,保持住这个姿势!然后我就听到他的相机“卡擦”“卡擦”响起来。伴随着这样清脆声音,许多被树枝拦腰斩断的阳光一脸苍白地往下掉,里面夹着许多明晃晃的过去时光。我睁不开眼睛来。
等我拿着鸟蛋跳下来的时候,浩森端着机器凑了过来,他眉飞色舞地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蹲在树杈上的这个姿势,多寂寞啊!于是我就这样被浩森赋予了寂寞,其实我的寂寞并不是浩森拍出来的,而是原来他蹲在我旁边枝丫上,现在他没了,我当然寂寞了。浩森把我说的“是你制造了寂寞”当作是我对他的赞扬,美滋滋地“吧嗒”了一下嘴巴。
饿了?我问他。
我能吃下一头牛!浩森说。
于是我们便一起往家里走。
太阳坚挺了一日,也疲软了,这时候模模糊糊地涂在半山腰,像是打散了的蛋黄,没有脚,一点一点往下滑。炊烟倒是青翠的,袅袅升起,随风摇曳。
浩森展开双臂,脸上荡漾着欢愉的神情,痛痛快快地叫了一声,乡下真好啊。我没有接话,有一个场面此刻跳进脑子,在我们一同要升高三的时候,浩森提出退学,他那时候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关于未来,一脸茫然,关于退学,十分坚定,他说,我宁愿是去城里种田,也不愿意在乡下读书。那时候他的眼神是没有焦点的,或者说他聚焦在未来,我们都看不见。他娘让我劝他,但是我站在他面前,什么都说不出来。
现在也是,我缄默,浩森绕着我跳,一边还是夸张地手舞足蹈,你看看,多么蓝的天啊,PS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忧郁的,你看这绿油油的稻田,哪里去买这样的油漆啊。他的目光倏然抖动,越过我的头顶,看向前方,然后我听见他直直地叫了一声,啊。
我不用看,都知道他是看到谁了。
果然她叫了一声,吴波哥。我没有应她。她当然也知道我身边这个人是浩森,但是她也只是憋红了脸看着他。她的手上拿着镰刀,上头还粘着一些青草汁液,我闻到了生命辛辣的气息。
割猪草去呐?浩森似乎没有觉察我的窘迫,只是认真问她。没有想到,面对这样的明知故问,丽伟也认认真真地点头了。浩森从脖子上取下他的宝贝相机来,递给我,我有点搞不懂,难道是让我给他们拍一张合影吗?浩森说,你把这个小心拿回去,我帮丽伟割猪草去。
我没有说好还是不好,丽伟也没有表态,我们两个都成了一粒卒,在他面前,毫无主见。等我反应过来,他们已经走出去好远了。我端着相机,透过镜头看他们,我突然看到了寂寞,他们明明是两个人并肩同行啊,我竟然看到了寂寞,真是奇怪。然后我才发现镜头盖并没有打开,我只是看见了自己的眼睛在黑暗里的投影。我被浩森赋予寂寞,也被浩森的相机赋予寂寞。看来寂寞难逃。
那天吃完晚饭,我在院子里乘凉,在我打死第七只蚊子的时候,浩森才回来了。他劈头就问,相机呢?
在你的旅行箱里面放着呢。
饭呢?
在灶里热着呢。我妈骂了我一顿,说我没有照顾好你。
浩森没有搭理我,径直跑去吃饭了,我听到他的嘴巴发出巨大声响。这一次他从城里回来,吃饭都是小心翼翼的,我要是发出一点“吧嗒”声音,他还投来鄙夷目光。看来今天他真的是饿坏了。等他吃完饭,我就带他去村口洗澡。
真奇怪,浩森回来的那天,家里的这口井就泛黄水。他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去村口大庭广众之下洗澡,但是夏天不洗澡,总是令人难熬的,虽然我爸是一星期才跳河里去洗一次,但是浩森毕竟是在城里呆了两年了,在我,在他,都觉得他是应该有点城里脾气的。对此,浩森不断摇头,我走的时候,村里就说要装自然水,你看,到现在,还是没有自然水。你不知道原来井水是有多清,多甜呢。那现在怎么黄了呢?我没有回答。
我们都是穿着内裤,用水盆打水上来,从头往下倒,浩森一直很关心一个问题,那女人怎么办,女人也会来这里洗吗?他每次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便提起一桶水从他头上倒下去。浩森冷得打颤,像是猴子一般跳来跳去,一边的小孩子就哈哈大笑,我竟然也得意洋洋地,像是得胜的将军一般。
你看你,这思想啊,一说女人,你就觉得犯罪一样,你表面上越是回避女人,你心里其实越渴望,你都十八岁了,要是在旧社会,你现在是几个孩子的爹了……
但是浩今天森没有说下去,我的目光让他没有说下去,我的目光牵引着他的目光,从他的胸口慢慢往下走,走过肚皮,然后是肚脐,再往下一点点,然后我们一起停在那里,浩森重新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对接在半空中。农村的夏夜,特别清亮,它照亮了我们的身体,也照亮了我们的想法。
让我自己吃惊的是,我竟然在第一时间想到了丽伟。他们一起去割猪草了,走在蜿蜒的乡间小道,爬到苍翠的山坡上去。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浩森这时候凑了过来,小声问了一句,你喜欢她吗?
我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当然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口,要是说出口,总让人觉得我是嘴硬。其实我真的不喜欢丽伟,我也没有喜欢过其他人,我知道浩森说的这种喜欢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喜欢也没有喜欢过丽伟而因为今天的事情以后我也不会喜欢她,我发誓。
浩森说,那你难过什么?
那我难过什么?我看了看天空中皎洁的月亮,然后我拿起水桶,从头浇了下去,水很凉,像是月光那般凉。又好像有牙齿,在肌肤上小小噬了一口。有些痛。
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上床了。虽然是夏夜,但是山风犹劲,我听见风刮过村子的声音。浩森躺在我身边。听他的呼吸,他也还是没有睡着。
我觉得你的情绪变化得很奇怪。他说,一切都是好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她,为什么要难过,如果你要难过,为什么不是我带她去割猪草的时候难过,不是在我回来的时候难过给我看,偏偏是在洗澡的时候你难过了……浩森没有继续说下去,总的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十分善解人意的人,但是说话总也还是有分寸的。
我知道浩森在想什么,我拉过他的手,望下探去,他的手指一定告诉他了答案。
那你难过什么!浩森一下子坐了起来。
没什么,睡觉吧。我真的有点困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是一个粗糙的梦,或者说是一个偷工减料的梦,梦里没有什么场景,我出现在一块灰白的空地上,没有穿衣服,一丝不挂,但是不冷,我发现自己已经淘汰掉了身体对自然环境的感知能力。我光着脚走了几步,但是我迅速放弃了,没有一个参照物告诉我是否移动了。我没有留下脚印。没有影子,没有风声,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空空白白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我的眼睛能飞到十公里外看自己身体,估计也隐没在一片苍白了。
然后我就惊醒了,浩森已经起床了,窗口上有一只鸟在认真地看着我。我再看它,它就飞走了。我说,嘿,你有什么话语我说呢。空气中传来它的回答,咕咕咕。我的镰刀与背筐都不见了,我想,浩森应该是去割猪草了吧。
我应该是没有醒透,迷迷糊糊走到井边去打水,直到把水桶丢下去,我才反应过来这井水已经死了。但是水桶没管,它仍旧开始吃水,肚子一点点沉下去,绳子在我手心慢慢滑过。有一刹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出了问题,我肯定是出了问题,我与井都出了问题,只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像是井那般显而易见。有一只水桶抛进我的心里去,但是却只是在那里摇晃,无休止地摇晃。我的心满是干草,但还是有一泓清泉在底下的。我在找。
有人拍了我一下,一开始我以为是浩森,不过我穿着背心,肩膀感受到他的粗糙,知道那是我爹。
他们一早上又出去了。我爹的喉咙里总是含着一口痰。
我把水桶提了上来,将水重新倒回井里。
你别管这个。
我不管谁管,我是你爹。
你是我爹你也也管不着这个事。
我怎么管不了啊,你是他爹,我要抱孙子。
我本来脱口而出“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不过却被我生生停在舌尖了,我把水桶摔在地上,一言不发走回屋子里去了。
爹在后面吐了一口痰,特别清脆地说了一句,你以为那是种庄稼啊,不想要了就拔了?
等浩森回来,我们三个男人坐在一起吃早饭。我给浩森盛了半碗饭,他从城里回来,饭量也变小了。浩森说,早饭就应该是喝牛奶,吃面包的。当然,这话是私底下与我说的,我说过,浩森终于还是有一个有分寸的人。在我爹面前,他还是挺有礼貌的,那种城里式的礼貌。
其实在盛饭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今天会发生点什么,所以我听到我爹对浩森说你姨走前对你很好呐的时候也没有多大吃惊。
浩森认真歪着头想了一会,神情悲伤地点了点头。
我爹接着又说了一句,你姨走得太早了,都没来得及抱孙子啊。
那天浩森让我带他去看看我娘的坟。
这也不是扫墓的时节啊。我低声推辞了一句,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对于一个儿子来说,百般阻挠别人去探望自己死去的娘,总是不好的吧。我说,那我们买点纸钱什么去吧。浩森瞪了我一眼,虚情假意。我于是没有再争辩下去,包括我看见浩森带上了他的相机,我也没能说什么。
今天你爹有点怪。浩森说。我没有来得及接话,他又转到其他话题去了,你知道早上我去做什么了吗?我摇了摇头,我与丽丽去割猪草了,用城里话说,我们就是去约会了。我说哦。浩森说,我的手就是镰刀,一下子就割进她的内衣里去了,你真是不知道,她也没有反抗,就像是我们忠厚的田地一样,任由我们在上面操劳,一言不发的,丽伟也是,真滑……
浩森还在喋喋不休,我只是说了一句,表哥,到我娘跟前了。
但是浩森的注意力被其他东西吸引走了,他只是说,吴波,你先与你娘说说话,我去那边看看,那边是一片竹林,风景不错。我看到浩森手上照相机都忍不住抽动起鼻子来。
我说,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事情叫一声,我就呆在这里。
我坐在我娘的坟前,我想到了丽伟,想法是自己跳出来的,我主宰不了,我在想她的手,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她的手,但是她的手现在却完整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才明白过来自己先前为什么总不敢看她,她是会黏住你的目光的,至少她的手是这样的,上面还有一个酒窝,这时候挠在我心上,我突然觉得很悲伤,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惆怅,就为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美丽的事物存在,好像未来有什么样子的苦难在等待,我都不怕了。我感觉到脖子皮肤下已经隐匿多时的痛这时候重新鲜活起来,那时候就是这样一双美丽的手抓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血痕。有关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或者是我选择性地忘记了,总之,就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我回忆不起什么味道来。那些酒都是丽伟灌着我喝下的。她当然知道孤男寡女,独处一室,而那个男人还喝醉了的话,会发生什么。浩森说得不错,其实我是一个懦夫,当时我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还是把自己灌醉了。这是丽伟欠我们家的。
丽伟出生之前他们家已经有五个女孩了,所以丽伟生下来之后,她家里人很认真地打算把她丢到山上去。那时候我娘跟他们家走得近,就跟丽伟爸说,让我们家把丽伟养大,以后丽伟嫁给我家吴波就可以了。当然,在我家里住到第七个年头的时候,丽伟家里突然变卦了,是啊,孩子本来就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这块肉越长俊俏,日子也勉强能挨过去了,不就是再多一副碗筷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总之,七岁的丽伟就这样被带走了,这份恩情,他们老刘家一定记得。至于婚约,丽伟父母说的含含糊糊,咱们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不能包办孩子的婚姻大事。
我记得那天丽伟拉着我的手探到她胸部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为什么。丽伟说,婶对我很好。但是我不能嫁给你,我有喜欢的人了。
但是现在,你是我孩子他妈。这句话其实一直蹲在我的舌尖,今天,终于跳了出来。在我娘坟前,我对不存在的刘丽伟说了这句话,带着相当的敌意。浩森这时候意犹未尽地从竹林走了回来,竟然没有电了。他说。
丽伟是我的。我没头没脑地对他说了一句。
啊?他有点不相信自己耳朵的样子。
我向他走近了一步,丽伟是我的。
浩森这时候很不聪明地在脸上浮现出一丝痞气来,他笑了笑,吴波,你不要幼稚了。丽伟怎么会是你的呢?来,来,你看看,我刚刚拍的东西,你说寂寞不寂寞。浩森将相机递了过来,我接过了相机,然后我把举起了相机,用力地向浩森脑袋砸去,浩森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到现在为止,眼睛里都流露出来的都还是诧异神情,直到他的手摸到他脑壳上流淌下来的鲜血,他才慢慢开始害怕起来。
表弟,你在做什么!他这时候已经变得可怜兮兮。
但是接下来他就说不出话来了,我举着他的相机又一次砸了下去,浩森歪着嘴躺了下去,我重复着我的动作,一下又一下,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下体硬得很是厉害。我丢开了相机,只是用拳头,对着浩森一拳又一拳地往死里捶,我一点都不恨这个人,而且我还知道他是我的表哥,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做这些。我想,我是疯了吧。
我不知道浩森死了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活过来了,我沉睡了太长时间,现在我终于醒过来了,我都有点快不认识自己了,这个我被那个我压抑了太久太久。
我回到家里,爹坐在那里抽烟,我去井里大水,爹说,井不是出黄水吗?我说没有,澄清澄清的呢!真的很清,我都看见了自己的脸!带着一个惬意的微笑。
我的心发了黑,但我的手还是善的,浩森亦只是受了一点皮肉伤,再严重一点,最多是动了筋骨,总之,赶忙地,又活过来了,鲜活过来,且是活给我看,他带走了丽伟,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丽伟肚子里的秘密了。
临走前,他还特别来看我。
他以后得叫我爹。哦,城里人不兴这个,是叫爸爸。他用手摸摸我的脸,他的手很细嫩,像是女人的手。
别不说话啊。他又说,还笑了笑,其实说不上是你儿子,还是你兄弟呢。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婶走得早,咱叔又是那么健壮着,是谁也耐不住一颗赤诚的报恩的心啊。丽伟是好人啊,好人应该有好报的,你们也是好人,也得到了恩报,但是别弄成了报应呐。
滚。我咬着牙吼了一声,我听进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捣鼓那口井,什么时候又浑浊掉了。
浩森灿然一笑,甚至是在我的床沿坐下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关于摄影的。以前呢,我有一个单反相机,我买的第一个相机,我很宝贝它,后来在学校,学生会主席要问我借。我能不借呢,只得借了,后来还回来的时候,一看,镜头弄坏了,换一个镜头就好,但是我把整个机子都给仍了。后来我朋友告诉我,我太傻了,至少可以去买个二手货的么,不过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就不会了。
他说完就走了。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跳下床追出去的时候,我看见那辆拖拉机已经开走了老远,浩森立在那里,丽伟站在他身边,虽然隔着老远,但是我仍旧看到了她脸上幸福的模样,但愿。
爹走了过来,站在我身边的,爹说,咱儿子优秀,不怕没媳妇。
我腾地举起了手,爹仍旧笑着看着我,我终于是软了下来,摸掉了他纵横的老泪。
(选自《荏苒》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