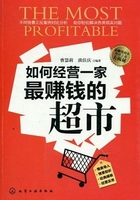文/铁头
1994年
被人叫做阿狗的男孩坐在一棵杨树下,一根鼻涕条从他的左鼻孔里悬垂而下,晃晃悠悠直指裤裆,猛一吸,那根鼻涕条便瞬间不见。有个瘦得仿佛左脸要贴上右脸的老头一只手按着阿狗的脑袋,一只手里举着手动的推子,正在阿狗的后脑勺上推土机似的推头发。在对面红色的墙垛旁,一个被人叫做阿猫的小女孩正蹲在那里,颤着两只羊角辫,抖一件白色连衣裙,双手捧下巴,望着阿狗吃吃笑。
阿狗的头勾着,听见阿猫笑,没法看清她,嘴里只顾喊,爷爷,你不要剪我前面的头发呀,我还要梳中分哪。爷爷说,你才小学二年级,中屁分。阿狗忽然从椅子上跳下去,跑到院子门口哀求他爷爷,求你了爷爷,我还要梳中分呢。爷爷说,你给我回来。阿狗说不。爷爷骂他是小王八羔子,举着梳子追他。阿狗扭头逃窜,光着上半身在巷子里像条小瘦狗崽子那样跑。他听见身后的脚步声一直在哗哗哗,想他爷爷怎么还在追,扭过头去瞧,原来是阿猫在美滋滋地跟着他。
于是他就站住了。
阿狗站在一条围墙的阴影里呼呼地喘气,看见阿猫停在自己跟前,便举起右手的食指点着她的鼻子尖,说谁让你跟着我跑的。阿猫跑得小脸通红,喘着粗气看阿狗嘿嘿笑,然后指他的鼻子说,你的鼻涕过河了。
阿狗生气了,一抽鼻子,伸手推阿猫肩膀,威胁她不准管他的鼻涕条。阿猫的肩膀被阿狗的手给推了几下,她也生气了,想我是班长,你还敢推我,所以她也伸手推了阿狗的肩膀几下。阿狗的肩膀被阿猫给推了,想你是个女生竟然敢推男生,举起双手使劲推了阿猫一把,眼见着阿猫向后踉跄几步,紧接着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阿狗叉腰看她,神气得很。
阿猫伸着两条小细腿坐在地上,看见自己的哥哥方圆从阿狗身后跑来,于是她把嘴一咧,就哭了。
方圆抡起胳膊就勒住了阿狗的脖子,说狗崽子,我弄死你。阿狗的脑袋在方圆的胳膊弯里转来转去,大声威胁对方,你给我松开,背后偷袭算什么本事,你松不松开?我数三个数,你要是还不松开我就出招了。读小学四年级的方圆愤怒地喊,你出招吧,总是欺负我妹妹,这回我把你的脑袋给拧下来。阿狗说好,一,二,三,我跟你拼了。他的右肩膀一沉,右手猛掏向方圆的裤裆,五根手指使劲一捏,就听见方圆嗷嗷的叫了起来。
方圆夹着大腿,扭屁股大喊大叫,你给我松开!跟我用阴招是不是?
阿狗捏着方圆的裤裆厉声质问,你服不服?
方圆嗓门尖利,服你妈!
阿猫看见亲哥哥被阿狗掏了裤裆,夹着腿像公鸡打鸣似的叫唤,心里非常着急。她也不哭了,从地上灵巧地爬起来,跑过去看准阿狗裤裆,一把掏过去并抓在手里。
阿狗尖叫起来,说松了松了。阿猫说你松了我就松了。阿狗怒不可遏,说你不松了你就完蛋了。阿猫说那我使劲了啊,手上加了力气。阿狗的眼泪瞬间就飞了出来,说我松了松了。阿猫松了手,泪还没干却一脸得意。阿狗站在墙角处瞪阿猫,嘴里嘟囔算你狠。
1996年
阿狗贼眉鼠眼地坐在教室里,看见小组负责人开始检查作业。阿猫就站在自己这排前面,慢慢地翻着其他同学的作业本。见她正向自己移动,阿狗赶忙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阿猫伸手推阿狗的肩膀,连推几下,不见阿狗有反应,于是她就扭过头大声冲前面说,牛老师,阿狗又睡觉了。牛老师说,什么,又装睡了吗?她走过来一把揪住阿狗的耳朵,听见阿狗嗷地叫了一声。
你这是空白的啊?阿猫翻着阿狗的作业本说,你没写作业。
阿狗的一对小眼珠子冲阿猫拼命飞眼,还偷偷地伸手拉阿猫的衣襟,说别告诉老师。阿猫说你别碰我,说那怎么行。她向后躲那只蛇一样的手,同时扭过头大声说,牛老师,阿狗又没写作业。
牛老师说,什么,又没写吗?小红花都倒数第一了,下课去我办公室。
从办公室里出来,阿狗觉得忍无可忍,要给阿猫一点颜色瞧瞧。他知道阿猫家养了一只小白狗,并且阿猫非常的喜欢它,总是把它抱在怀里,像温柔的妈妈抱自己的孩子那样悠来悠去。他要偷她的狗。
阿狗的胳肢窝里夹着一个折叠好的麻袋,边走边对大眼说,我偷的时候,你在巷子口给我盯着点儿,她家的人要是回来了你就吹口哨。大眼说,行。阿狗灵巧地翻墙跳进了阿猫家的院子,抖着手里的麻袋,对站在窗台下的小白狗说,奔儿,奔儿,奔儿。那只小白狗扬起嘴巴冲阿狗说,汪。阿狗一手捏着麻袋口,一手伸过去抓狗耳朵。那狗一点儿不含糊,张嘴就在阿狗的手上来了一口。
完了,狂犬病。阿狗扔掉麻袋,捂着手转身向大门口跑。出了院子,望着大眼可怜巴巴地说,我让狗咬了,快背我去打针,要不就得狂犬病了。大眼说,行。大眼搂起阿狗的两条细腿,健步如飞地向诊所的方向跑。
新的一天已经来到。
阿狗笑容可掬地坐在教室里,不耐烦地等待着本小组的负责人检查作业。他看见牛老师埋着头坐在讲桌的后面哗啦啦地翻着什么东西,看见阿猫翻着同学们的作业本正向他逼近。他挺起胸脯,身板笔直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阿猫斜了阿狗一眼,拿起他的作业本在手上狐疑地翻,嘴里说,怎么还是空白的?
阿狗晃着脖子气阿猫,说我愿意。阿猫很惊讶,想他要造反吗?说我给你告诉老师。阿狗说你是个屁。阿猫瞬间气黑了脸,扭过头大声说,牛老师,阿狗又没写作业。牛老师拍案而起,什么,又没写?
阿狗赶忙举起缠着白绷带的手,更大声地说,牛老师,我的让狗咬了,不能写字了。
1998年
小学红色教学楼后面的围墙上,几个少年坐在上面抽烟,炎热盛夏,暑假时间寂静的操场边传来一只蝉的不懈叫声。一个叫祝亮的少年忽然脱光了上衣,像健美先生一样勒起肌肉,向大家展示他满是疙瘩块儿的臂膀,非说自己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阿狗跳下围墙,脱掉上衣,屈臂,绷起自己的肱二头肌,说你跟我比还差得远哪。大眼说看我的,说罢也开始脱衣服。其他几位少年也都脱衣服,纷纷举着胳膊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大家吵吵嚷嚷,说我的大,我的大。都想证明自己的肌肉最发达。
阿狗和祝亮争得面红耳赤,动手打了起来。几个少年乱成一团,都光着膀子,互相拉来扯去的,能听见大眼焦急的喊声:并列第一,你俩并列第一。
后来大家就不打了,都骑上墙头,开始整齐划一地抽起了烟来。
阿狗觉得没意思,把衣服拎在手里从墙上跳下去,晃着膀子朝学校门口走。大家问他干什么去。他不应,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在巷子里面,贴着围墙,踩墙的影子。空荡荡的巷子里只有阿狗脚步的回音。
阿狗踩着几块从别处搬过来的砖头,扒着墙头向院子里张望,看见阿猫正一只手拄着下巴无聊地翻书看。当时阿猫的脑袋后面歪着一条马尾辫,面对大开的窗户坐在书桌前。她一抬头,看见了自己家的墙头上长出了阿狗的脑袋,便举起手里的书,做出假装要扔过去的样子吓唬他,还故意歪着嘴,竖起眉毛,一副很凶恶的模样。
阿狗嘿嘿笑,头一探一探的,然后像条影子一样从大门缝里挤了进去,鬼鬼祟祟,东张西望。小白狗的叫声又把他给吓了一跳。阿狗冲着小白狗瞪眼睛,说不许叫,是我,随即一闪身走进房门。小白狗没拿这小子当回事,站在门槛外面继续汪汪地叫,直到阿猫从窗口里飞出来一只拖鞋,呵斥它不准乱叫。
阿狗心惊胆战,担心阿猫家里有人。阿猫坐到床边捧起一块西瓜啃,说我妈和我哥都不在家。阿狗放下心来,在屋子里随随便便地走起着,抓起一块西瓜边吃边看着阿猫说,你在看英语书吗?真爱学习,都毕业了还看书。阿猫说废话,说我是什么人,我是小学就入了团的人,可不是一般人,将来还得考名牌大学呢。阿狗点头附和说,确实。阿猫说你没事也看几眼书,不能堕落。阿狗皱着眉头摇脑袋,说不行,看见字脑袋瓜子就嗡嗡响呢。
阿狗坐在床上,犹犹豫豫的样子,说阿猫,我想问你个事。
阿猫满嘴西瓜汁,说什么事。
阿狗神神秘秘地凑过去,坐在阿猫身边说,你亲过嘴没有?
阿猫警惕地打量着阿狗,说问这干什么?
阿狗说反正我是没亲过。阿猫说我也没有。阿狗说我能亲你吗。阿猫说不能。阿狗说什么时候我能亲你。阿猫说我还没想好。阿狗说你什么时候能想好。阿猫说我不知道。阿狗有些不耐烦,说要不咱俩现在就亲一下得了。阿猫说不行。阿狗浑身发痒似的坐在床上,一点一点逼近阿猫。阿猫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阿狗说,我给你告诉我哥。阿狗苦着脸,说别别别。阿猫说那你离我远点儿。阿狗还往前凑。阿猫朝窗外望了一眼,说我哥回来了。
阿狗二话不说,踩着阿猫家的床,猛的从后窗口跳了出去。阿猫走向自己的床,发呆地看着白色床单上的那个大脚印,拍了拍床单,嘟囔说,这个大王八。
2000年
我们家快要搬走了,离开这个尘土飞扬的小镇,离开已经放弃学业成天跟我们瞎混的阿猫,离开混乱的中学,离开遍地开花的不良少年。父母说我们家必须搬走,为了你,你不离开那群小流氓,一辈子就毁了。他们说人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你看阿猫,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说快中考了,不能再放任你了。
算为我送行吧。我们哥们几个围坐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小饭店里,窗外的马路上像有滚烫的大水在热烈地奔流,鼻孔里走着烟雾,牙齿里污言秽语。我们都有些喝醉了,交流变得含糊,似乎在各说各的。
大眼忽然说,今天阿猫怎么没来。我摇着头,说不知道,谁知道她哪里疯耍去了。大眼说她怎么变成这样了。其他人也说阿猫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悲哀地说,管她呢,人家早就看不上我了,她现在喜欢的是初三的姚良,姚良是学校里的老大,我能怎么样。邵军鄙视地说,姚良算什么东西,我要为你收拾他。我说算了吧。邵军说不能算。其他人也说不能算。大家都喝了酒,都醉醺醺的。
邵军猛的站起来,冲我说,阿狗你还是不是个男的,阿猫给你戴绿帽子,我早看不顺眼了,我亲眼看见她阿猫坐在姚良的大腿上。我满脸通红,垂着头窝囊地冷笑。邵军的火窜了上来,说是阿狗哥们的都跟我走。其他人都站起身,跟着邵军朝外面走。我也变得热血沸腾,结了帐,跟他们离开。
我们一群人全都面红耳赤地站在老邮局对面的阴影里,大约有七八个人,在等大眼。很快大眼就出现了,他的车后架子上驮着一个深绿色的大帆布兜子,里面装着的是我们以前买的刀具,都是一些没开刃的片刀。我们取出那些刀,由邵军带头,大摇大摆,打算往旱冰场里走。可刚走到旱冰场门口,突然有巨大而混乱的叫喊声从里面传来。
一个满脸是血的人忽然从里面跑出来,出门直接朝左拐,发疯地甩着胳膊奔跑。接紧着,三个持刀的青年追了出来,他们一边大声地叫骂着,一边追赶那个满脸是血的人。我们都被这突然出现的场景给吓了一大跳,拎着刀子站在马路对面,看见那个被砍的和三个砍人的都跑进巷子里消失不见了。
邵军瞪大眼睛看我,说怎么回事。我迷惑地摇着头,说不知道,说怎么看那个被追的人很眼熟呢。邵军说,我看着也眼熟。大眼突然说,那好像是方圆。这时祝亮站在马路对面冲我们喊,你们拎着刀在那儿傻站着干吗?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邵军招呼我们说快跑。我跟着他朝巷子里奔跑的时候,扭头向马路对面的旱冰场门口扫了一眼。在密匝匝的人群里,似乎看见了阿猫那张浓妆艳抹的脸,还有她的眼睛。那是一对不再清澈的大眼睛,那对眼睛里面现在满是惊恐与迷惘。
2002年
三高对面有一个主要面向学生开的小吃部,老板是一个胖女人,每天都叼着根烟站在柜台后面,跟我们这些男生天南海北地闲聊。她的女儿很漂亮,初三年级的样子,为了偶尔能看到她的宝贝女儿,我选择每天中午都到这家小吃部里来吃炒饭。那是个周日午后,我和同学正在小吃部最里面的屋子里喝汽水聊天。一个女孩探头探脑地从外面走进来,问那个胖老板,是不是有一个叫阿狗的人在这里吃饭。女老板告诉她就在里面。
她站在门口喊我的名字阿狗。我闻声扭头看她,见门口的阳光把她的脸给照黑了,虽看不清她的脸,但已从声音里听出来者是谁。是阿猫。我走过去说,你怎么来了?两年没看见你了。
阿猫拘谨地冲我笑,说有一天遇见了大眼,他告诉阿猫说我是在三高的一年三班。她今天直接去了我班教室,但同学告诉她说我可能在这个地方吃饭。
于是她便找来了。
我盯着阿猫的眼睛看,发现她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漂亮,但依然化很浓的妆。闹不清她到底想要掩盖什么,竟然用丑去遮掩美。她眨着大眼睛看我,沉默一小会儿说,你能到外边来一下吗?我想跟你说点儿事。我跟着阿猫走到外面凶猛的阳光里。
阿猫说,我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亲戚给我找了一家理发店,安排我在里面当徒工,阿狗我找你是想跟你借点儿钱,现在我住一个集体宿舍,很不习惯和别人住在一起,想在外面租个房子,但不知道家里是不是同意,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打算先跟你借点儿,我保证会很快还你的。
我问她需要多少。她说要好几百块,最好是四百。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五百。她很着急的样子,说你帮我跟你的同学借一下行不行?我在这里不认识别人,只有找你。我痛快地说行,在这里等着我。
我让阿猫在学校门口的阴影处等我,自己则小跑着走进校门,走进教室,问我们班的那些同学借钱。我向他们保证会很快还上他们的钱,并且我人缘和运气都不错,从我们班四个女生的手里分别拿到一百块钱。
我跑出校门,把这四百块钱交到阿猫的手里。阿猫接过钱,感激地望着我说,阿狗,反正我哥也死了,我认你当我哥好不好?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两年前的场景,在炎热的夏天,满脸是血的方圆在马路边发疯地奔跑。那天他死在了一条巷子里,趴在地上。我同情地望着她,随即高兴地点头说,那真是很好的事情呢。阿猫说她今天真开心,说我会常来看你的。
我把阿猫送上人力车,看见她坐在车上扭过头冲我摆手,看见她渐渐的远去。我忽然意识到心里面是有那么多问题要问她的,问她和姚良的事情,问她死了哥哥以后家里的情况,问她到底是在铜城的哪一家发廊里当学徒,等等。看来这些问题只能等到下一次她来看我的时候了。
一个星期后,阿猫没有出现,我有些着急还那四个女同学的钱。第二个周末下午,大眼倒是又一次来到我们学校看我,他这是第二次来我们学校。我们出了学校向东面走,边走边说话。
大眼说,你被阿猫给骗了,我总能看见她,她还在跟姚良瞎混日子呢。我说不能,她要学理发来着。大眼说我骗你干吗?她在网吧里成天上网,其实她跟你借钱是因为姚良最近打架出事了,需要钱,他们俩正在到处弄钱,能偷就偷,能骗就骗。我大吃一惊,连说几个不能吧。他说怎么不能,现在我们那边的年轻人见到姚良和阿猫都躲着走。
我简直是听傻了,无论如何也没法相信阿猫已经变成了这样。
2004年
回到镇里后遇见的第一个人是邵军,当时我刚下汽车,在储蓄所门口看见一个剔了光头的矮胖子向我招手。仔细辨认,方才喊出他的名字。我跟他开玩笑,说他肥得像猪似的。邵军笑着打量我,说不读书就是老得快,二十多岁的人,你还是一副学生模样。我说我那是幼稚。他问我回来干什么。我告诉他爷爷病重,已经下不了床,高考一结束就赶紧回来看望一下他。
邵军说那你先去看你爷爷吧,晚上我和大眼去找你。我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拍了拍我的胳膊,一边朝公交车上走,一边扭过头冲我笑。
我打算住在爷爷家里,因为晚上还要与大眼和邵军他们见面。
看见躺在床上的爷爷,心里面特别难受。他已经衰老成这副模样,让人不忍心描述。我独自站在院子门口,感慨着时间这东西真是一把利刃。
阿猫是在这时出现的,她家本来就离我爷爷家不远。她从巷子口朝我这边笑眯眯地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和阿猫站在巷子里说话,再次看见她,竟觉得她也老了,脸上和眼睛里已经提前丧失掉青春和活力,目光时而狡黠,时而迟钝。因为我又一次想起了她骗我四百块钱的事,害得我当年省吃俭用了两个月才把那欠债还清,所以在和她说话的时候,我的态度比较冷淡。
阿猫邀我到她家里坐一坐。我拒绝说不想去。但她很热情地拉我,坚持让我去,看着她眼角的早熟和疲惫,心里突然有一些酸,想人总是会长大的,总是会犯错的,总是会变化的。我应该原谅这个与我一起玩到大的美丽女孩。
走在去阿猫家里的路上时,她对我说,我和姚良早就分了,他和他叔叔去了广州,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自己,唉,我怎么那么傻呢,其实我也应该上大学生的,小时候我学习可是好着的呀,你最清楚了,真是命运弄人啊。
想起过去,恍若隔世,我哦应了一声。
又一次来到阿猫的卧室,与曾经相比,似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阿猫的家里没有人,我们两个的对话总是出现尴尬的中断,她在尽力维持着热情的气氛,而我总是显得心不在焉。后来阿猫忽然站了起来,麻利地脱掉上衣,她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眼球里。
阿猫说,我知道我骗过你的钱,但现在我是一个穷鬼,不能还你钱。
我吓了一大跳,连说别别,那钱我没打算让你还的。
阿猫愣愣地看我,又麻利地套上了衣服。而我却再也坐不住了,想立即逃出去。她颓废地坐在对面的椅子里,喃喃地咕哝说,阿狗,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2006年
家里传来爷爷去世的噩耗。
我到导员那里开了各科的请假条,匆匆忙忙踏上回家的汽车,所幸大学离我的家乡并不遥远。在车上时,我感受到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望着窗外缓缓移动的远处建筑,想爷爷遭了两三年的罪,终于是得到了解脱。那股难以言喻的伤感几乎就要揪下我的泪水,因为从小总是呆在爷爷家里,而如今,爷爷已经永远的离开。
世界上不会有永远不破的气泡,活着的过程就是目睹时间的罪恶啊。
这次回去,遇见了很多我少年时代和童年时代的朋友,听他们聊了一些熟人的境况。当然,他们也提到了阿猫。他们说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阿猫了,他们说她低调地嫁给了一个外地的老板,究竟是哪里的有钱人,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只说曾经看见过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
她注定是要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说,其实她很漂亮,应该找个年轻些的。
她每天都愁眉苦脸。大眼说,早等不及要过富裕的生活了。
2008年
大眼结婚。
我是前一天晚上赶回去的,希望能和往昔的朋友们聚一聚,并且,他们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在黄昏时分我们喝酒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融入到他们的谈话之中,为了照顾到我,他们开始讲述我曾经认识的那些人的近况,这几乎成了我和他们见面之后谈话的必然。在交谈的间隙,除了感慨我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情绪。
后来,我们一起醉醺醺地朝小学走,在校门口,遇见了一个抱小孩的女人。我当然能够辨认出她,尽管当时的天色已经黑下来。她就是阿猫的母亲,一个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的女人。她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生活的问题,以及家里的情况。得知我已经大学毕业,正在寻找工作,她开始感慨起自己家庭的不幸。她说她的命苦,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她说她的儿子不学好,早早的被人砍死。她说她的女儿也不学好,丢下一个野种音信全无。
这个小孩是阿猫的儿子?我有些吃惊。
不是儿子,是个女儿。她用另一只手揉了揉眼角的泪水,去年她忽然回到家,带回这个孩子,住了几天就又离开了,现在我已经联系不上她,她的那个手机号已经不用了。
她不是结婚了吗?我迷惑地望着她说,听他们讲,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
她的事情,我怎么说呢,其实现在我这个当妈的都不清楚,我不知道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沉重的黑暗之中,她歪了歪嘴,没有再说话。
我和同伴们像一块糖融化在咖啡里。
现在
下班回来,疲惫不堪地坐在租来的房子里。白天工作时眼花缭乱的身影和支离破碎的对话依然在耳边鸣叫。闭上眼睛,让黑暗将我包裹起来,像一个青春女孩的长发。独自躺倒在床上,想起一个再无音信的失踪女孩,美丽的阿猫,整理一些与她相关的记忆,所幸多数都还非常清晰。也有一些变得模糊不清,比如那些与河流相关的记忆,那就像是别人的。
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站在大河边的河滩上,踩着那些密密麻麻的鹅卵石,他们光着脚丫向河的下游走去。那些鹅卵石像数不清的白色眼睛,有的烫脚,有的滑腻。他们在一丛芦苇的旁边停住脚步,当时有芦苇的气息混合着河水的湿腥钻进鼻孔。几只白鹭站在对岸悠闲散步。一艘铁皮的小船从上游漂流而下,船上有一个叼着烟卷的中年男人,船帮上站着两排东张西望的鸬鹚。
爸爸!阿猫尖声细气地喊。
那个船里的中年男人站在河心,就像一只虫子站立在杨树叶上面。他冲岸边的两个孩子笑呵呵地挥手,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瞎子。他伸出两只手在空中胡乱地摸索,摇摇晃晃,最终跌进了大河。他的头偶尔会浮出水面,像个葫芦一样在湍急的河水里越漂越远,他的嘴巴空洞地张着,像死鱼,仅仅是喊出了几声尖利的怪叫。
阿猫喊,爸爸,爸爸……
阿狗喊,叔叔,叔叔……
声音远了,不见了,喧嚣被塞进瓶子里,成了一粒盐似的原点。所谓少年与少女的故事,还不就是一个个阿猫与一个个阿狗的故事。纯洁的欢笑,终将成为一声绝望的呼喊。喊了也就喊了,世界还在旋转,一切早晚变得不堪回首,正如可爱的事物,一声哈欠,便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垂死的女王,在地心种一束火,谁躲在枯萎的仙女座上雕刻王冠。爱的纤维仿佛巨兽头骨上莲花的纹理,可时间的利器早把涅盘的光芒锯得灰飞烟灭。阿芙洛狄忒,站在我们回不去的地方,美丽得像个毒药。
(选自《荏苒》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