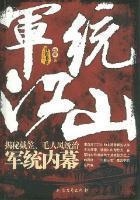我兴高采烈地投入到了工作中,结果,真像伯林汉小姐所说的那样——很费时间。两个半小时的速写——大概每分钟一百字,的确需要很长的时间将它转换成正常的文字。我只能立刻开始工作,否则明天是不能准时交出笔记的。
想到这里,我丝毫不敢耽搁,刚刚踏进诊所不到五分钟,我已经坐在书桌跟前,将那些潦草的简写字改写成工整、可以辨识的正体字了。
假如不是因为有爱,这种事情实在谈不上有趣。当我再次记录那些字句的时候,伯林汉小姐温柔的声音也再度传入我的耳中,顿时让这件苦差事变得有趣起来。而我,仿佛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我跨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有着伯林汉小姐的世界;而那些不时打断我思绪的病患,虽然让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但是我一点也不感谢他们。
一个晚上过去了,奈维尔巷始终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我开始担心起来,难道伯林汉先生始终无法打消他的疑虑吗?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关心遗嘱副本,我只是比较在意伯林汉小姐今晚是否能来。哪怕她只能与我相处片刻,我也会非常满足。
7点30分左右,“砰”的一声诊所大门被打开了,我满怀期待的心立刻打蔫了——进来的是奥蔓小姐,只见她手里拿着蓝色的大信封,满脸严肃地将信递给我,说道:
“这是伯林汉小姐让我转交给你的,信封里还张有纸条。”
“我可以看看吗,奥蔓小姐?”我多少有些失望。
“简直就是个愚蠢的男人!”她大声叫了起来,“我带它来就是要给你的。”
对啊,看来我真的有些糊涂了。于是,感谢她之后,我便拿出里面的纸条看了起来。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同意我将遗嘱副本拿给桑戴克博士。当我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时,发现奥蔓小姐正不以为然地盯着我看。
“看来你得到了某人的欢心了。”她讥讽地说道。
“我一向都很招人喜欢,天生的!”
“才怪!”她不屑地哼了一声。
“难道你觉得我人缘不好吗?”我笑着问道。
“油嘴滑舌!”奥蔓小姐瞥了我一眼,然后看了看桌上的笔记说,“你在忙这些?看来你真的变了不少。”
“是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改变。你一定读过艾萨克博士所写的那首‘如果撒旦能够……’的圣诗吧?”
“你所说的是‘游手好闲’那首吗?”她回答,“看来我得奉劝你一句了,千万不能游手好闲太长时间。我非常怀疑那块夹板的真正作用,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辩论,她已经趁着几名病患进门的空隙离开了。
晚上8点30分左右,诊所就要关门了;时间一到,阿多弗就会关上诊所的大门,今晚也不例外。他做完最后一项工作之后,将煤气灯关小了一些,然后跟我打了一个招呼,便离开了。
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接着传来一阵关门声,这表示他已经离开诊所了。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桌子上躺着那个装着遗嘱副本的信封,我突然想到,应该尽早将这个交给桑戴克博士,并且只能由我亲自送去。
我看了看那些笔记,接近两个小时的抄写,进度已经相当显著了;只不过剩下的部分,还需要继续拼命。我想了一会儿,决定睡觉之前再抄一会儿,剩下的明早再有两个小时就能弄完。于是,我将摊开的笔记本原封不动地挪进了书桌抽屉,然后将其锁上,这才拿起信封,动身赶往桑戴克那里。
当旧财政部敲响9点的钟声时,我正拿着手杖轻轻敲着桑戴克办公室那道厚重的橡木门,里面一直没有回应。这时,我突然想起快要到这里时,看见窗口并没有灯光;我想也许他在楼上的实验室里。就在这时,石阶上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
“你好,拜克里!”桑戴克礼貌地招呼道,“等了很久吗?彼得正在楼上研究他的新发明呢!以后如果你发现办公室没人,就去直接去试验室吧!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在那里。”
“并没有等太久。”我说,“我正准备去打扰他呢,结果你就来了。”
“哈哈,就应该这么做!”桑戴克一边说着,一边将煤气灯开得更亮一些,“有新的进展吗?我似乎看见有只蓝色的信封正跃跃欲试呢!”
“是的,一点也没错。”
“是遗嘱的副本?”
我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我已经得到允许,将副本拿给你看了。”
“看我说得没错吧!”里维斯大声叫道,“只要副本真的存在,他肯定能弄到手!”
“是的,我们承认你有这样预知的能力,但是也不用自夸吧?”桑戴克望着我说,“你仔细看过了吗,拜克里?”
“没有,连信封都没有打开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第一次看了?好的,让我们来确认一下,它与你的描述是否一样。”
说完,他在煤气灯周围摆放了三张椅子。里维斯看着他的举动,笑着说:
“看来桑戴克又找到好玩的东西了。对他而言,又有什么能比内容复杂难解的遗嘱更有趣呢?尤其是它还可能牵扯某种卑鄙的阴谋。”
“我不能确定这份遗嘱是否表达得明确。”我将话题转向正轨,“但是,也许它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要求太过明确了。反正,我将它拿来了。”说着,我将信封递给了桑戴克。
“我想这份副本应该没有问题,”他抽出里面的文件看了看,说道,“是的,没错。这的确是葛德菲尔·伯林汉所持有的副本,不但与原件相同,而且还签了名。里维斯,请你逐字逐句地将它念出来,我会大概地抄写一些内容作为参考。咱们先轻松一下,抽会儿烟斗再看吧!”
他准备好记事本,我们点燃烟斗,坐稳之后,里维斯打开文件,清了清喉咙开始念了起来:
奉天父之名,阿门。本文是由约翰·伯林汉先生于1892年9月21日,在密德塞克斯郡伦敦市伦斯拜瑞区圣乔治教堂教区立下的最终遗嘱。
1.住在密德塞克斯郡伦敦市林肯法学院新广场184号的亚瑟·杰里柯律师,将得到我全部的印玺和圣甲虫宝饰,以及编号为A、B、D柜中的收藏品,外加两千英镑财产,并免缴遗产税。剩余的古董收藏品全部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另外,住在肯特郡艾尔森白杨大道的表弟乔治·赫伯特,将得到五千英镑,并免缴遗产税;我的弟弟葛德菲尔·伯林汉,将得到其他所有的地产、房产,以及私人物品,假如他在我之前死亡,以上所有财产将转赠给他的女儿露丝·伯林汉。
2.将我的遗体与我的祖先们一起葬在圣乔治大教堂教区墓园;假如不能如此,就将我的遗体葬于圣安德鲁大教堂、圣乔治大教堂、布伦斯拜瑞区圣乔治教堂,或者圣吉尔斯教堂所属区内;或者上述教区任何一个教堂、礼拜堂的墓园,以及任何一个允许埋葬死者遗体的合法场所。但是,如果以上条款均不能达成,则——
3.将上述地产、房产改赠给我的表弟乔治·赫伯特所有;另外,在此之前,本人所立的全部遗嘱将自动失效。在此,我指定亚瑟·杰里柯成为这份遗嘱的执行者;主要受益人和剩余遗产受益人为共同执行者。假如所述第二个条款得以实施,那么葛德菲尔·伯林汉为遗嘱的共同执行者;假如第二个条款无法实施,那么乔治·赫伯特为共同执行者。
约翰·伯林汉
最后,此文件由立遗嘱者约翰·伯林汉签署;并由我,以及在场数人共同作证、签署。
菲德列克·威尔顿,执事,伦敦北区梅弗路16号
詹姆斯·巴柏,执事,伦敦西南区新月广场魏伯瑞街32号
里维斯放下了手里的文件,说:“就是这些了。”同时,桑戴克也将记事本最后一页撕了下来,里维斯接着说,“我见过很多愚蠢的遗嘱,但是没有哪个比这个更荒谬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份遗嘱将怎么执行。共同执行者在两个遗嘱中二选一,这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做法,就像无解的数学难题。”
“我倒觉得这并不难办到。”桑戴克若有所思地说。
“我觉得很难,几乎没有办法做到!”里维斯反驳道,“假如在某个地方找到尸体,那么就由A担任执行者;如果没有找到,就由B来担任执行者。可是,目前为止并没有人知道尸体的下落,也没有什么能证明尸体在某个特定的地点,而尸体是不会自己出现的。”
“里维斯,你将问题想得太复杂了。”桑戴克说,“是的,尸体也许就在某个角落,假如不是在那两个教区之内,就是在那以外的地方。假如尸体被弃置于那两个教区之内,那么,只要调查一下失踪者生前最后一次活动,以及那天之后的所有丧葬证明;或者查询两个教区的墓园登记,立刻就清楚了。假如在这两个教区内,都找不到任何有关的土葬记录,那么这件事情可以由法院采证,判定这两个地方没有举行过相关的土葬仪式。所以,尸体肯定是被弃置在了其他地方。因此,乔治·赫伯特就成了遗嘱的共同执行者,以及剩余遗产的受益人。”
“你朋友这下可郁闷了,拜克里。”里维斯说,“有一点可以确定,尸体并没有被埋在这两个教区之内的墓园里。”
“是的,”我沮丧地说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哪个笨蛋会拿自己的臭皮囊大做文章呢?人都已经死了,葬在哪里又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没有礼貌了!”桑戴克看着我们笑着说,“你说这话可有些不公平了,拜克里。专业训练让我们变成了唯物主义者,因此也让我们对于那些怀有单纯信仰和情感的人少了些理解和同情。有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来我们解剖室参观,他曾跟我说,天天面对这些支离破碎的肢体,他很难想象学生们还会对永生或者复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这个人,有着相当厉害的心理分析能力。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解剖室以外,没有哪个地方会比这更加死寂;而静静地面对人体被解剖的过程——就像分解老时钟或者废旧的引擎一样——并不会让人联想到如永生、复活这样的教义。”
“是的,一点都没错。可是坚持必须将自己埋葬于某个特定地点的荒谬心理,与宗教信仰根本毫无关联,这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情感罢了。”
“嗯,我也赞同这是一种情感,”桑戴克说,“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可笑。这种情感不但流传久远而且分布也很广泛,我们必须以敬重的心态去对待它,并将它视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约翰·伯林汉肯定这么想过,古埃及人一生的愿望就是追求长生不老,他们绞尽脑汁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努力。想一想大金字塔或是阿孟霍特普四世金字塔,那里面的迷宫暗道,以及隐藏的墓穴密室;雅各布死后为了与父亲葬在一起,不远万里回到迦南地;还有莎士比亚,为了能够在墓中获得安宁,向后人立下神圣誓约。拜克里,这绝对不是可笑的情感。当然,我跟你一样,并不在乎自己这身臭皮囊会被怎么处置,但是,我能够理解有些人为什么如此执著,如此看重它。”
“可是,”我说,“就算他渴望死后能够埋葬在一个特定的墓地,那么,也应该以合理的方式去达成吧!”
“这个我当然赞同!”桑戴克回答,“这份遗嘱的确很荒唐,它不仅带来了很多难题,而且在立遗嘱的人失踪之后,它也变得离奇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什么意思?”里维斯惊讶地问道。
“现在我们来仔细研究研究这份遗嘱吧!”桑戴克说,“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是,立遗嘱的人有一个资历很深的律师可以咨询。”
“可是杰里柯先生根本不赞同遗嘱的内容,而且他也强烈地建议过约翰·伯林汉草拟一份更合理的遗嘱。”我反对道。
“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一点。”桑戴克的态度很坚决,“对于这份遗嘱的条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应该是这其中极大的不公平性。葛德菲尔·伯林汉的继承权,因遗嘱人遗体的处置变化而受到影响。可是,这种事情又不是葛德菲尔能够控制的,遗嘱人也有可能死于船难、火灾或者意外爆炸,或者死在另外一个国家,并埋葬在某个不知名的墓园中。这种可能实在太多了,更别提要找到尸体了。
“而且,就算找到了尸体,也会存在另外一个难题。遗嘱上提到的那几个教区的墓园,很早以前就已经关闭了。除非可以得到特别的许可,否则根本不可能重新开启使用。而且当局也绝对不会核发这种许可。假如是火葬,问题也许可以简单一些,但是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一点;更何况,葛德菲尔·伯林汉也不能决定这一点。所以,不管怎样只要有一个条件不符要求,他都不会拥有继承权。”
“这太不公平了,真是可恶到了极点!”我气愤地大声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