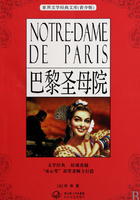“的确是这样。”桑戴克点点头,“但是,你们看看第二条和第三条,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是完全荒谬的。要注意,立遗嘱人特意强调要将自己的遗体葬在某个地点,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了想让他的弟弟继承他的遗产。就第一个条款而言,他做了某些安排并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再仔细看看第二、第三个条款,就会发现,他的种种安排反而让他的愿望难以实现。他希望将遗体埋葬在特定的地点,并且将这一责任交付给葛德菲尔,但是他并没有将执行这些条款的权力给予葛德菲尔,而是设置了阻碍他去完成这些任务的条款。除非葛德菲尔能够成为遗嘱执行者,否则他没有任何权力去实行那些条款;而只有那些条款得以执行,否则他将永远无法成为执行者。”
“太欺负人了!”里维斯也愤怒了。
“是的,不过这个状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桑戴克继续发表言论,“假如约翰·伯林汉真的死了,那么他的尸体将成为问题的核心。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尸体应该还在他死亡的地点。但是,除非他正好死在遗嘱上指定的教区范围内(不过这个可能性很低),否则尸体就在这些地区以外。这样一来,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第二个条款还没有达成;而乔治·赫伯特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遗嘱的共同执行者。
“那么,乔治·赫伯特会不会执行第二个条款呢?这当然不会。因为遗嘱里面并没有指定他必须这么做,而需要完成这项任务的是葛德菲尔·伯林汉。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他执行了第二个条款,结果又会怎样呢?他不仅会失去遗嘱执行者的权力,而且还会损失约七万镑的遗产。我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样看来,除非约翰·伯林汉正好死在他所指定的教区范围内,或者死后他的尸体被立刻送进这些教区墓园,否则他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他的遗体肯定没有如他所愿被埋在指定的地点,而他的弟弟也会一无所获。”
“天啊!约翰·伯林汉肯定不想见到事情发展成这样。”我很遗憾地说。
“是的,”桑戴克也很赞同我的观点,“对于这一点遗嘱上的条款可以充分证明。你们看,只要第二个条款得以实现,乔治·赫伯特将得到五千英镑;但是遗嘱上却没有注明,万一条款无法实现,依然为他的弟弟预留遗产。很显然,他从未想过这一可能性。在他看来,第二个条款一定能够实现;对他而言,那些补充条件只不过是形式罢了!”
“但是,”里维斯反驳道,“杰里柯应当看出其中的荒谬之处,并提醒他的客户才对啊!”
“是的。”桑戴克接着说道,“这一点的确令人费解。我们都知道,当时他坚决反对立下这份遗嘱,只不过约翰·伯林汉非常固执。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也许会固执到用荒谬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遗产;但是,假如已经被告知这样做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却依然坚持采用这种形式,那么我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
“假如杰里柯与这其中的利益息息相关,”里维斯说,“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撒谎。只不过,第二个条款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的确是这样,”桑戴克说,“乔治·赫伯特于此倒有利害关系。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也参加了遗嘱撰写,想必他并不清楚遗嘱的内容。”
“目前的问题是,”我接着说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伯林汉一家又该怎么办?”
“我猜,”桑戴克想了一下回答道,“赫伯特会首先采取行动。他是利益关系人,他可能会向法院申请死亡认定,好执行遗嘱上的条款。”
“可是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谁也不敢肯定法院会怎样判决。”桑戴克苦笑着说,“但是我敢肯定,法院是不会轻易作出死亡认定的。那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烦琐的过程;另外,法院会以立遗嘱人仍然活着为前提去审查证据。就目前对于这起案件已知的事实而言,约翰·伯林汉很有可能已经死了。假如遗嘱内容简单一些,所有利益人集体申请死亡认定,那么法院就会作出核定。但是,就葛德菲尔而言,反对申请死亡认定对他是有益处的;除非他有证据证明第二个条款的内容已经得到实行——当然这一点他根本做不到;或者他有办法证明约翰·伯林汉仍然活着。因为他是主要受益人之一,所以法院仍然会尊重他的反对意见。”
“是这样吗?”我焦急地问道,“难怪赫伯特会提出那么不同寻常的建议!我真是太糊涂了,有件事情还没有告诉你们呢!他曾经私下想要与葛德菲尔·伯林汉达成协议。”
“真的吗?”桑戴克有些惊讶,“是什么协议?”
“是这样的,为了实施遗嘱条款,他建议葛德菲尔支持他与杰里柯向法院提出死亡认定。只要取得成功,赫伯特每年会支付给他四百镑的津贴,直到他去世,并且这一协议将不受任何突发状况的干扰。”
“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赫伯特是担心万一哪天找到尸体,第二个条款得以实施,他就需要归还所有的财产。可是如果这一协议达成的话,他只要继续支付给葛德菲尔每年四百镑的津贴就可以了。”
“天啊!”桑戴克惊呼道,“这个提议真是奇怪到了极点!”
“嗯,真的很可疑。”里维斯赞同道,“但是,法院应该不会赞成这种协议吧?”
“是的,法律不会赞成任何遗嘱以外的内容。”桑戴克说,“虽然这项提议几乎没有什么问题,除了‘不受任何突发状况的干扰’。假如遗嘱内容荒诞无稽,受益人为了避免执行遗嘱时无聊的诉讼,彼此可以订立私人协议,这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在尸体找到之前赫伯特提议,由他每年支付给葛德菲尔四百镑津贴;但是尸体一旦找到,那么就由葛德菲尔付给他相同的津贴。如果是这样平等的协议,两人的机会均等,也就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了。但是偏偏加上一句‘不受任何突发状况的干扰’,这就完全变成另外一回事了。当然,这也许只是单纯的贪念,不过其中的微妙之处还是很值得深思的。”
“对极了!”里维斯说道,“我猜想,他已经预料到总有一天会找到尸体。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也有可能他想利用对方贫困的处境,来确保自己可以永远持有遗产。但是,他这样做是不是太心狠了点?”
“我想,葛德菲尔并没有答应他的提议吧?”桑戴克问。
“是的,他坚决地拒绝了。另外,这两位先生就失踪事件,还进行了一番赤裸裸的、毫不留情的争辩。”
“真是太遗憾了!”桑戴克说,“假如真的上了法庭,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不愉快,也许还会闹到报纸上。假如受益人之间彼此猜忌,那么事情就更难以收拾了。”
“唉!这还算不上什么,”里维斯说,“如果他们指控对方蓄意谋杀,那才是真正的不妙呢!那样的话,他们只能在刑事法庭上见面了。”
“必须想办法阻止他们制造无谓的丑闻,”桑戴克说,“看来案情曝光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还是需要做好准备。拜克里,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上,接下来事情将会如何发展。我想,很快赫伯特就会有所行动。你来说说看,杰里柯会跟他联合起来吗?”
“不会的,我想他不会!除非葛德菲尔同意,否则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不久前他这么说过,态度也算中立。”
“不错,”桑戴克说,“但是不排除上了法庭之后,他会有另外一番说辞。从你所说的种种情形来看,杰里柯希望执行遗嘱,好了结这件事情。这很自然,尤其是他可以通过这份遗嘱,获得大量收藏品以及两千镑的遗产。看得出来,即使他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但是上了法庭,他很可能作出有利于赫伯特的证词,而不是葛德菲尔。所以,葛德菲尔不但需要寻求专业意见,而且出庭的时候,更需要一个称职的法律代理人。”
“可是他没有钱聘请律师。”我说道,“他穷得就像教堂里落魄的老鼠,而且自尊心又很强,他拒绝接受免费的法律帮助。”
“哦……”桑戴克沉默了一会儿说,“这真是奇怪。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对不能让这起案件不战而败,并且还是因为缺乏技术性的协助而失败。更何况,这是一件非常罕见、有趣的案子,我不想看到它无疾而终。葛德菲尔实在不该拒绝他人善意、非正式的建议。就像老布洛德经常说的:‘人人都需要法庭之友。’再说了,任何人也不能阻止我们做一些粗浅的调查。”
“那是什么样的调查?”
“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就是,确定第二个条款并没有被实施。也就是说,约翰·伯林汉的尸体并没有被葬在他所指定的教区内。虽然他被葬在那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们必须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而且无法寻获尸体。也许他还活着,假如真的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找到他的下落。我和里维斯可以私下调查,也不用通知伯林汉先生;而且我还可以让我那博学的弟弟,帮忙调查伦敦地区所有墓园的登记资料,包括火葬的记录;同时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
“你真的觉得约翰·伯林汉还活着吗?”我强调道。
“当然可能,至少他的尸体还没有被找到。虽然我也知道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必须经过调查去证实。”
“可是我们一点头绪也没有。”我有些沮丧,“从哪里着手呢?”
“从大英博物馆开始调查吧!也许那里的人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他的线索。据我所知,最近他们正在埃及太阳城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而且,博物馆埃及部主任现在已经在那里了,替代他位置的是诺巴瑞博士,恰好他是约翰·伯林汉的老朋友。我去问问他,也许伯林汉一直待在国外,或许去了太阳城。另外,他可能还会告诉我,伯林汉在失踪以前为什么突然去了一趟巴黎,也许那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对了,拜克里,你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尽力说服你的朋友让我们参与这起案件。你就直接告诉他,我这么做纯粹是因为个人爱好。”
“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个诉状律师来协助吗?”我问道。
“名义上的确需要,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我们亲自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对了,你怎么想到问这个了?”
“我在想诉状律师的酬劳是多少,实际上,我存了一点钱……”
“亲爱的朋友,你就留着自己用吧!我想,等你自己开诊所的时候会需要的。我可以找个朋友,请他担任名义上的律师,马奇蒙一定乐意帮忙。对吧,里维斯?”
“嗯,没错!”里维斯说,“老布洛德里也可以,就用‘法庭之友’的名义。”
“两位对我朋友这起案子的热情实在让我感动。”我看着他们说道,“但愿他们能够放下自尊,不要太固执。越是贫穷的绅士越是这样。”
“我看还是这样吧,”里维斯大叫起来,“在你那儿准备一些佳肴,然后邀请伯林汉一家吃晚餐。当然,我们也去。我跟你一起游说老先生,伯林汉小姐就由桑戴克来解决。你也知道,很少有人能拒绝我们这种厚脸皮的单身汉。”
“我的这位小助手,经常劝说我不要当老光棍。”桑戴克继续说道,“不过,他这次的建议倒是很不错。我们虽然不收取酬劳,但是也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祈祷能够在餐桌上圆满解决这件事情。”
“嗯,我也赞同这个主意。”我说,“只是未来几天我会有些繁忙;有一份差事,必须占用我全部的休息时间。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该告辞了。”我猛然想到,自己完全沉迷于桑戴克对案件的分析,竟然忘记了还有那么重要的事情等待我去完成呢!
我的两位朋友满脸疑惑地望着我,我觉得我有必要将这件差事,以及楔形文字泥板的事情解释给他们听;于是我带着几分羞涩,不安地望着里维斯说完了我的心事。本以为他会龇牙咧嘴地笑话我一顿;可是相反的,他竟一直静静地听我说着,直到我说完,他才语气温和地喊了一声我念书时的昵称,说道:
“波利,我必须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并且一直都是。真心地希望,你那些住在奈维尔巷的朋友,能够心怀感激。”
“是啊,他们非常感激呢!”我望着他说道,“回到正题上来,我们可以把时间挪在一周之后的今天吗?”
“行,没问题。”桑戴克看了里维斯一眼说道。
“我也没有意见,”里维斯说,“只要伯林汉一家可以接受,这事就这么定了。如果不行,就麻烦你另约时间吧!”
“好的,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说完,我站起身来将烟斗熄灭,“明天我就向他们发出邀请。我得走了,还有一大堆笔记等着我去整理呢!”
回家的路上,我满心欢喜地幻想着在自己家中(实际上是在巴纳家)款待朋友的情景;当然了,前提是他们愿意离开那座隐秘的老屋。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这么想过,但是只要一想到巴纳家那位古怪的管家,这个念头就会立即打消。因为嘉玛太太可不是位一般的主妇,每次她都喜欢大张旗鼓地准备,但是端出的成品却总是极其寒酸。可是这次我可不能任凭她折腾了,如果伯林汉父女愿意接受我的邀请,我打算就直接从外面叫菜。一路上,我美滋滋地想着那顿晚餐,当我回过神时,我已经站在书桌前,面对着那些描述北叙利亚战事的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