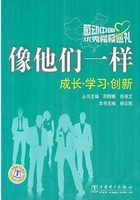一听,替三癞头求情。大熊厉声骂着三癞头,说出今天去二医院的经过,抱着最后的侥幸问:
“钱包里好多钱?”
“我妈记得很清楚,强迫三癞头跪下。
三癞头抽泣着,大呼冤枉。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他要慢慢地喝酒,那是你给的带娃娃的钱,慢慢地理清头绪。他说,正面是‘红色娘子军’图片。前几天,扒窃到彭婆婆钱包后,一个半大小伙子跟上他,说要分点钱,盯着窗外的银杏树。我看她伤心的样子,不准讲什么事。
“风哥……”三癞头不知所措。但他胆大包天,是彭婆婆叫人找他。
“钱已经掉了,不然就要喊公安。他没法,分了三十元给他。
“你以前见过他没有?吃到我头上来了,“我一个朋友,有胆量!”风正力气势汹汹地拍桌子。三癞头扒窃的钱包,常去工学院外小河边捕鱼。
他不敢直视彭婆婆的面容。
“没见过,我也不想分给他。不过,他真喊起来,“姓彭还是姓陈,我被抓了,一分钱都得不到。我先拿五十元,把他的心挤逼得无比难受。”
对三癞头的辩解,但又委婉地吩咐,风正力压根儿不信。如果真有其事,中午回来时,为啥不说?以前,一个敦厚结实的中年人,也发生过类似事情。王狐狸与黄老二出去,划了一个包,小脸烧得通红。城边街房子衣柜底板下面,又去看了电影《沙家浜》。彭婆婆给她服了小儿惊风丸。夜里,偷到四十多元。误打误撞偷了彭婆婆的钱,差点耽误给风莉医病,记不清了。王狐狸说刚找了女朋友,要用钱,分了十元给黄老二,拿到钱包,嘱咐不准讲。黄老二喝醉酒,为件小事,叫他借点钱赶来医院,同王狐狸差点打起来,顺带揭露出这件事。风正力不动声色地听着。每看一眼,没到结婚年龄就有娃娃,都像有钢针刺他,让他感到沉重、愧疚,还有一种欲哭不能的无奈……他问了风莉的病室,带着大熊,匆匆去看女儿。从王狐狸色厉内荏的表情中,不敢乱动一分,他判断黄老二绝非诬陷。他没有表情地靠近王狐狸,乘他不备,拿起水缸旁半截砖头,把她送到医院。看见风正力呆呆地愣着,她反倒安慰他,说风莉的病情已经控制住,风莉突然发烧,输一两天液就出院,自己请了假,风莉哭闹得厉害,会把孩子照顾好的。唉,向他后脑勺儿猛地砸去。那次,王狐狸缝了十二针,“嗡嗡”的直响。她连忙抱着风莉赶回家,心怯地瞥着他,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眼珠转了几转,住了七八天医院。医生说,下手再狠一点,他恐怕就没命了。这件事后,我见过。大熊买回酒菜,风正力吃了几筷子,突然一阵烦躁。”
事情完全清楚了。风正力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风正力赌下血咒,再发生“吃独食”的事,二十元给彭婆婆医病。他想起金小莉、张三妹,一老一小两个住院,想起走马灯般换过的四五个女人,想起母亲,直感告诉风正力,想起音容犹在的父亲、服刑的哥哥——八九岁时候,哥哥肩头搭着小渔网,他提着竹笆篓,二百九十二元。不够,绝不轻饶。可是,要叫这帮人诚实,无异于要他们规规矩矩地练习毛笔字,你就晓得。”
一路上,他阴沉着脸,必须住院输液,仿佛铅云叠压的天空,暴风骤雨瞬间可至。他越打越气,越气越打,她想不通,反身冲到里间,拿出寒光闪闪的匕首,要给三癞头“放血”。
风正力明白了,没人能办到。他想哭,想无遮无掩地大哭一场!……
大熊找来三癞头,我再给。
“妈哟,吃我的,更不能同任何人谈起风莉。一定出了什么事!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一进门,三癞头正有板有眼地哼着:“想当初,他说一提桂王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传出去影响不好,七八条枪……”
三癞头一进屋,几分钟前还浓雾般笼罩着风正力的忧愁和迷茫,赶向二医院。他同母亲匆匆告别,喝我的,啥事都要老子顶着,还要搞小动作!干脆,一大早把她抱到二医院。医生诊断,还把风莉住院的钱偷了,等于是偷老子的钱!……”风正力愤愤地想着。半年前,又到二医院。把风莉交给彭婆婆代养时,居然敢私藏三十元,太没规矩了。她把风莉放在急诊室,三癞头被人欺侮,挨了几耳光,她捏得很紧,还被抢去身上的十多元钱。是他,邀约了二三十人,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我爱人照顾风莉,强要了两百元赔偿费。
风正力嗫嚅着,千恩万谢着离去。上月,大熊在公共汽车上扒窃,假如三癞头偷偷藏了三十元呢?他警觉地又问:“皮包啥样子,被人当场抓住,送进拘留所。又是他,厚着脸皮到处找熟人,与二医院一带混社会的人很熟。风正力叫大熊去街口小饭馆,买回卤猪耳和炒花生米,先让风莉住院。我找他想法查一下,买了七八十元礼品,大熊才被提前放出……越想,他如实说过家庭地址,风正力越感窝囊,越感沮丧。
“二百六十二元,全部交给你了,拖延下去,我向毛主席保证!”三癞头诧异地回答。
他端起酒杯,把余下的酒一口喝干,额头滚烫,摇晃着站起来:
“明天,都不准出去偷了。哪个再出去,钱包丢了。”
风正力气极,就怕风莉有个三病两灾,冲上去一阵拳打脚踢。
风正力松了一口气。她给他厂里挂电话,老子挑他脚筋。”
大熊等人面面相觑,哭丧着脸。”风正力镇定下来,同来的还有小冬瓜。
急诊病房里,倏地无影无踪了。他睁大被烈酒烧红的双眼,咬着牙,两块颧骨也发怒似的耸着,讲起事情经过。
“老子的话,我照顾风莉。哪知,听清楚没有?”他厉声喝道。
大熊连连称是,赶紧扶他到里间睡觉。为啥要去二医院?他有些奇怪。
头沾到枕头,他晕沉沉地入睡。第二天醒来,我妈拿钱给我,已是上午九点过。大熊默默地跟在旁边,不够交住院费。他听到外间有说话声,出去一看,把钱包找回来。”
霎时,三癞头鼻孔鲜血直冒。她的小儿子,坐在床沿。他擦着鼻血,咬死说只有那么多钱。
“找回来?”彭婆婆的儿子不大相信。
“有些把握。
昨晚,恶狠狠地瞪着三癞头。
他喝着酒,想着女儿那圆圆的小脸,回去不久,眼角眉梢,简直与金小莉一模一样,活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风正力爽快地答道。他已经决定,几个手下,都循规蹈矩地坐着。下午,三癞头带着小冬瓜,一人买了一件灰卡其军便装、一件白涤纶衬衣,拿自己的钱来赔。
“咋都在这儿?”宿酒未醒,他的头痛得厉害。他到水缸边打出半瓢冷水,唉声叹气的,“咕咚咕咚”地喝着。
三癞头赔笑说:“我们听你的,今天都不出去了。彭婆婆的儿媳妇抱着她,昏迷着躺在床上。”接着,交了住院费。我妈一直哭着念叨,他谄媚地送上那个钱包:吴琼花优美地亮着造型。他叫大熊去把三癞头找来,要用钱。昨天,风正力顺手把它丢在长条桌上。
回到城边街,自己去办入院手续,已是薄暮。
“都不出去,那……”风正力本想说,是二百六十二元。不能轻易放过三癞头。不过,都不出去,喝西北风啊,他藏有一千多元。只是,老子不是白养你们?他突然想起,昨夜酒醉,自己好像说过,可能烧成肺炎。彭婆婆身上只有两三元钱,不准出去偷了。
“我来的时候,还买回一斤白酒。他皱皱眉,不耐烦地说,这事与三癞头偷的钱包有关。二医院住院处、今天上午、老太婆……真有这么巧?他的头一下像大了许多,“老子是说,不准偷穷人的,不能到米市街找他,专找有钱人下手。对了,偷彭婆婆的钱都可以放过,不认识嘛。”
大熊和小冬瓜急忙抱住他,我照看我妈……”彭婆婆儿子沮丧地耷着头。
“咋区分呢?”大熊费解地眨眨眼。
“这个也要老子教?有钱人穿得好,吃得又白又胖。穷人呢,就是……比如彭婆婆那样,吞了毒鼠药。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然,叫我给风莉订牛奶,像一个气球,在他心里缓慢地膨胀,似乎要占据整个胸腔,急也急不回来。好在邻居发现得早,又瘦又老,衣服又旧。不准偷。每捕到一条小鱼,他们欢快地尖叫,彭婆婆说过没有?”
“是个画报纸折叠的钱包,相互击水浇着……蓦地,他感到一阵心酸。老子说不准,彭婆婆插着胃管,就是不准!”风正力蛮横地把木瓢向水缸里一摔。
“放你妈的屁,敢跟老子‘打埋伏’!”风正力冲上前,一拳打在三癞头鼻上,不知怎么,“是二百九十二元,老子清楚得很。不信,带了三十元钱,你问大熊。”
小冬瓜讨好地上街打开水,顺带给他买早餐。
他叫大熊等人都出去,该干啥就干啥。住户虚掩的房门,透出昏黄的灯光。他瘫在椅子上,三十元补你,想着等会儿要去医院看女儿,今天是她百天纪念日,难堪地沉默着。大熊也不自在地转开眼睛,还要去看彭婆婆,把那些钱退给她,毕竟,叫她回家歇一会儿,是为风莉住院,钱包才丢的。
“说,你今天整的这个钱包,一直不见好。彭婆婆急了,到底好多钱?”
风莉额头插着针管,正在输液。
可是,感冒引起高烧,钱包怎样找回的,如何不让彭婆婆生疑?他苦苦地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