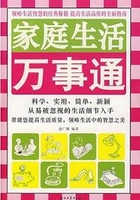他们又在鲁家祠堂院坝里折腾起来。毕可一告诉父亲,吉他是帮同学做的,父亲相信了。他们轻车熟路,忙碌了一个多星期,做出两把吉他。弹起来,音色比前两把好一些。为了美观,刷漆前,他们用红墨水混上墨汁,在琴背画上几道虎纹。毕可一还别出心裁,在琴背右下角写个小小的英语字母“B”,他姓的谐音,作为纪念。
一个下午,他们背着吉他,来到城南农贸市场。毕可一说,下午人多,吉他好卖。
城南农贸市场是自发市场,在南门大桥外杀牛巷。市场主要买卖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也有叫卖衣服鞋袜的,还有做黑市票证生意的。派出所和办事处打击了无数次,市场就像不倒翁,取缔一两天,稍一松手,又自发恢复原状。他俩找了一个地摊,铺上报纸,放上吉他,展开写着“吉他转让”几个大字的纸条,静待买主前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路人最多只淡漠地瞟瞟吉他,没人询问。毕可一着急了。为了招徕买主,他干脆站起来,抱着吉他,开始弹唱《纺织姑娘》:“在那矮小的屋里,灯火在闪着光,年轻的纺织姑娘,坐在窗口旁……”
琴声浑厚地飘散。几个年轻人围上来,好奇地注视着他们。
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蹲下,爱不释手地抚着吉他:“咋卖?”
“一把三十元。两把一齐买,五十。”彭登全答道。
“能不能少些?我只买一把,自己弹。”小伙子熟练地弹出一串音阶,“音不准。”他皱眉调整琴弦。
突然,市场骚动起来。街道两旁,卖菜的农民和小贩,乱纷纷地挑着担子、背起背篼急急散去,就像平静的湖面,蓦地掀起滚滚惊涛。毕可一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地摊前,已挤进几个左臂戴着红袖套的大汉。
“我们是联防队的!”为首的大汉,扁脸,密密的络腮胡,指着袖套亮明身份,“你们干啥?”
“转让吉他。”毕可一强作镇静。
“转让?”大汉冷冷的一笑,“非法买卖吧!既是转让,发票呢?”
毕可一与彭登全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无话可说。
“肖队长问你们!”其他人不耐烦了。
肖队长洞悉一切似的,冷冷一哼:“清楚了。带回去。”
他俩一人抱着一把吉他,被六七个人押着,向联防队走去。路上,肖队长得意地说:“抓那些卖菜卖水果的,鸡毛蒜皮,没啥意思。这两个人,搞不好,就是一起盗窃大案。”
彭登全胆怯的一碰毕可一:“咋办?”
“怕啥,人正不怕影子歪,吉他本来就不是偷的。”毕可一给他打气。
联防队设在气象学院收发室旁。进门,他俩被分开讯问。
“吉他哪来的?”肖队长跷着腿,点上烟,指着毕可一。另一个联防队员拿起笔,准备作笔录。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你都能做,还要乐器厂干啥?”肖队长根本不相信,嘴唇一努,“让他老实点!”
作笔录的小伙子过来,狠狠给他几耳光。
毕可一被打得眼冒金星。他害怕而委屈地辩解:“的确是我自己做的。”
“那好,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姓名、住址、年龄、职业?”肖队长问。
毕可一沉默着。“不能说,不能说。街道一知道,招工的事就完了!”他下意识地在心里警告自己。
连问几遍,毕可一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肖队长勃然大怒,重重的一拍桌子:“看你顽抗多久。来,给他上个‘苏秦背剑’!”
毕可一左手被反扭到身后,右手被举过头顶,向后强弯触到左手,再用绳子将双手手指捆在一起。两只手一高一低,就像一把斜背的剑。霎时,他的手指火辣辣地痛,肩胛处的关节,也仿佛即将脱臼。他痛得龇牙咧嘴,额上冒出颗颗汗珠。
“我说,我说!”他求饶道。
“这就对了,坦白从宽嘛!”肖队长满意地叫人给他松绑。
毕可一揉着胀痛的手指,老老实实地交代一切。
“你犯了三个错误。一、做吉他自己弹,可以,但不应该非法买卖;二、你卖吉他时唱的歌,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歌曲;三、最重要的,清明节刚过,北京的反革命正以悼念总理为名,想搞资本主义复辟。你呢,又搞非法买卖,又唱黄色歌曲,配合得很好嘛。”
肖队长威严地逼视着毕可一。毕可一头昏脑涨地嗫嚅,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最后,肖队长宣布处理决定:包括他俩家里的吉他,四把吉他全部没收;水泥模具等必须销毁;考虑到他们还算坦白,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决定宽大处理,教育释放。
他俩垂头丧气地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盖手印,又灰溜溜地被押着,分别回家交吉他和砸模具。
鲁家祠堂坝子里,联防队员找来铁锤,三两下把模具砸成碎块。毕可一父亲蹲在门前,拼命地吸烟,敢怒不敢言地吐着粗气。邻居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模具做得不容易,砸了怪可惜的;有的在为毕可一不平,说大小伙子没有工作,做吉他卖钱也没啥;有的,故意刁难联防队员,说这是“革命大院”,要他们捡走水泥碎渣,把地面打扫干净,别给大家抹黑。
毕可一呆呆地倚着家门,两眼空洞无物,死盯着散乱的水泥碎屑,不动,也不说话。联防队员扛走吉他后,他还是这么愣着。母亲有些害怕,把他拉进屋。他仿佛失去意识:叫他坐下,就顺从地坐下;叫他喝水,端起茶杯就喝。母亲安慰他,说一定要买一把最好的吉他。父亲赌气地说:“做,还要做!我在厂里做,看他们咋样?”毕可一毫无反应。
忽然,他发疯似的跳起来:“吉他!我的吉他!”他眼里,闪着迷乱而疯狂的光,在房里四处寻找吉他,抽屉里、床下、泡菜坛,连茶叶筒也被揭开。发现到处都没有吉他,他绝望地哭闹着,把吉他曲谱全部撕成碎片。
父母慌忙又诓又劝,最后强制着把他按在椅子上,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
“吉他!我的吉他!……”他对着窗户,呆滞地喃喃念着。那表情,那声音,实在让人心碎。
“咋办啊?”母亲六神无主地问。
“明天去医院。”父亲无可奈何道。
第二天一早,他们把毕可一送到医院。毕可一像什么都没发生,顺从地跟着父母。他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地低着头。父母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一句多话。精神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给他作了检查和测试,还把毕可一父亲叫到一旁,详细询问发病经过。
“初步诊断,是受了过度刺激,导致间歇性精神分裂。这个病没有特效药,主要靠调理,药物仅起控制和镇定作用。不犯病,他和正常人一样。病情发作时,他行为异常,敏感多疑,性格也有改变,莫名其妙地会发脾气、伤心。为把吉他?……”医生语调沉重地摇头。他开了一些药,叮咛要保证环境安静,避免让毕可一再受刺激。最好,这段时间不要他抽烟喝酒,也不要他单独外出。
回到家里,父母商量着对策:首先,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毕可一患病,街道正要招工,传出去,会影响前途;其次,一定要照顾好毕可一,尽快医好这个讨厌的病。毕可一母亲决定请一个月事假,专门在家照料,对外,就说是工伤休息。为了避免毕可一受到刺激,他们把家里有关吉他的一切,剩下的半张层板、买来备用的琴弦、小半桶清漆、刚缝制的吉他套等,一股脑儿全部扔了。
“这些鬼东西,害人!”扔东西时,毕可一母亲恨恨地骂。
在母亲的悉心照护下,毕可一很快恢复正常。与发病前相比,他略显沉默。他很关心招工的事,没事就去办事处,经常参加街道活动。
三个月后,作为单位子女,毕可一被内招进建筑公司,分配在伙食团。体检时,他一切正常。半年过去了,领导见他踏实肯干,喜欢捣弄钟表、收音机,便把他调到机具站学机修。
彭登全经常来找毕可一。他仍旧很少回生产队,盼望能有路子回城。毕可一母亲专门嘱咐,毕可一有精神分裂症,绝不能谈有关吉他的任何事情,以免他再受刺激。彭登全很谨慎。有时闲聊,刚谈到歌曲之类的话题,他立即小心地把话头拉开。
单位师傅给毕可一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叫肖缨。她比毕可一小一岁,刚满二十二,在棉织社工作。在介绍人家里一见面,毕可一就喜欢她。肖缨个子不高,五官秀巧可爱,总是羞答答地垂着眼。肖缨对毕可一也有好感。几天后,毕可一带肖缨回家,父母也很满意。母亲拿出省下的“号票”,买了几斤肉,还偷偷去双桥子黑市买了一只鸡,做了一桌好菜。父亲不会说什么客气话,一个劲儿地朝肖缨碗里夹菜。肖缨体贴地给父亲斟酒,还主动到厨房翻热鸡汤。毕可一幸福地微笑着。彭登全羡慕不已:“我调回来,找朋友,也找这种类型的。”
按礼节,毕可一应去肖缨家,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肖缨安排他星期天去。星期六晚上与肖缨约会时,他忽然有些胆怯,说带上彭登全一起去。肖缨同意了。星期天上午,毕可一打扮得精精神神,提着父亲准备的礼品:两瓶酒、两条烟、两袋茶叶,外加一些水果,与彭登全一道,来到肖缨家里。
肖缨父母都在军工厂工作,模样淳朴善良。他们听肖缨谈过毕可一,对他很热情。他们忙着准备午餐,说肖缨的哥哥和嫂嫂中午也要回来,大家见见面。寒暄后,毕可一跟着肖缨,走进她的房间。
肖缨的房间很小:单人床占了一半面积;靠墙,放着五抽柜和小书桌;床头,花花绿绿地贴着舞剧《白毛女》剧照;床侧墙上,醒目地斜挂着一把吉他。
毕可一坐在木凳上,眼光恰好对着吉他。渐渐,他不自在起来,视线落在吉他上,说话心不在焉。
彭登全预感不好,忙说附近有家百货商店,自己想买皮鞋,叫毕可一陪着去。“好,好。”毕可一口里应着,却坐着不动,死死地盯着吉他,表情怪怪的。
“吉他是我哥哥拿回来的。我不会弹。挂起作摆设,好看。”肖缨莞尔笑着,取下吉他,擦去上面灰尘,递给毕可一。
毕可一接过吉他,轻轻地拨弄着琴弦,表情越来越恍惚,眼神也越来越迷茫。蓦地,他想起什么,翻来覆去,细细地打量着吉他。终于,他在琴背右下角,发现了米粒大小的字母“B”。
“吉他,我的吉他。”他失魂落魄地站起来,凄楚地念着。猛然,他把吉他狠狠地朝地上一摔,“吉他!我的吉他!——”他大喊着,跑出去。
肖缨惊慌失措,不知所以。
“等会儿给你解释。”顾不上多说,彭登全慌忙追出去。
毕可一喊着,跑得很快。彭登全追着,猛然,一个念头在他脑里冒出:
“……精神分裂症!对,我也装这个病,办病转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