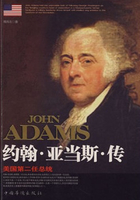(1842—1924)
一
大约在15年以前,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过一次系列讲座。其间借机表达了我对马歇尔这一伟大灵魂的尊重。听众中有人写信给我,以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这样一种意见,大意是说:马歇尔的思想像穆勒或亚当·斯密的思想一样,总要过时的。我将以对这个问题做回答的方式阐明我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已经过时了。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他的方法、他的结论,早已不再为我们所用。我们可能喜爱并崇拜他的强大的理论结构,体现在:尽管受到了一些批判主义理论及新思想的强烈抨击,可它的庄严的轮廓仍然渗透在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背景中。我们可以喜欢和欣赏它,就如同我们喜欢和欣赏皮鲁吉诺皮鲁古诺(1446—1523),意大利画家,擅长画宗教人物,描绘过许多优美的壁画。罗马的西斯听诺礼拜堂的一些壁画就是他画的。——译者注所画的圣母像一样,认识到她完美地体现了她的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可是同时也要认识到它距离我们已经是这样久远。
这当然只是这50年工作的必然结果。若不是我们可以用“古典”这个模糊的词语来界定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那他这些年工作的结果很可能就付诸东流了。这是各个领域里所有古典学派的共同命运。“只要有可能,小人物可以写出大作品。”现代经济学理论同《经济学原理》的关系与现代物理学和19世纪90年代的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没记错的话,亨得利克·安东·洛伦兹荷兰籍物理学家(1853—1928),曾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奖。——译者注在1894年说,理论物理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在现代物理学领域中,这种绝对肯定的说法已经不存在了,那些非常简洁而清晰的结构分界线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我们看到了如战场一般的混乱无序——一堆一堆的不相关联的事实和一件一件的不相关联的技术,看不到任何能将它们整合构成一个完整结构的迹象。在经济学方面也发生了极其相似的事情。我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及与其相关的道德和政治态度的转变。我也无意说马歇尔对实际问题、社会问题及其他类似问题的看法非常过时了,也许他的观点是过时了,但这一点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列。对本文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他的分析工具已经陈旧了,即使并没有任何事情使我们的政治态度改变。即使历史停滞不前,分析对象以外的一切事物均不再向前发展,也改变不了上面的结论。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马歇尔的学说永远不会过时,它的影响将会永远保持下去。这不仅因为这种广泛而强大的学说将成为以后若干世代的遗产,而且也因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能够有效地抵抗腐蚀。马歇尔生活的年代,到处充斥着“进化发展”的口号和呼声,受这种氛围的熏陶,马歇尔是最早认识到经济学是进化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之一(批评他的人不仅忽视了他的思想中这一因素,甚至在一些情况之下,实际上正是由于认为他的经济学忽视进化方面而指责他)。特别地,他认识到所要研究的人性是有可塑性的和变化的,并且具有改变环境的能力。但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他的“进化思想”运用到理论工作中,并且大有要一直持续下去的意思。和穆勒不一样,马歇尔从来不会说某个问题就此解决了,不需要他或其他作者再做进一步的补充解释,正相反,他充分地理解到,他所建筑的基本上是临时的结构。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力不能及的、超过自己范围的领域,这样,一些新问题、新观念、新方法对于其他著者来说,也许像敌人一样陌生、可憎,而对于他来说却像同盟者一样亲切。在他所修筑的庞大而坚固的阵营里,有容纳所有这些“同盟者”的房间——或者说,是提前就为他们准备好的栖身之所。过去和现在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他的理论,但其中绝大多数是比较狭隘的人。有时,这些反对者会发现(或是别人会替他们发现),马歇尔提前实现了他们的目标,这因此使他们的反对毫无意义可言。
二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在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后产生的。当它最初在1890年问世时,立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的问世就像是一出伟大的演出,它披着最吸引人的外衣出镜,完全迎合了那个时代大众言论的趋势,同时也与经济领域的发展现状相契合——事实上这既归功于作者的判断力,也归功于他的天赋。
但是如果想要准确地定位这部著作的性质,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直接指向《经济学原理》所提出的分析工具的核心,则很难做到对它完全公正的评价。因为这个核心的前前后后及周围各个角落,都笼罩在一种以感染力和凝聚力为历史基础的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学的氛围中。实际上,马歇尔虽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但他确实是一位一流的经济史家。而他对史实的掌握及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并没有割裂开,而是形成了紧密的结合,具体而言,就是将活生生的事实归纳总结成原理,再将原理运用到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当然,这一特点在《产业和贸易》中表现得比在《经济学原理》中更为显著。在《经济学原理》中,即使在历史概论的部分,历史事实也被大范围地削减了,以致不论对追随者还是批评者来说,这部分都似乎是一种缺失,然而,不管怎样,它没有消失。同样地,马歇尔对同时代的商业活动孜孜不倦、感同身受的观察结果也一直存在,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像他那样了解这些商业活动。正因为这样的性质,其后来的成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局限性。与马歇尔同时代的中等规模的英国企业的商业实践活动在当时无疑吸引了这位分析家过多的关注,因为他声称自己的主张是可以被普遍应用于实践的。但在这种限度内,他在现实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亚当·斯密——这是唯一可以用做比较的例子。这可能是为什么他在英国没引起制度学派反对的理由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反对曾经在我国出现,并且这是不难理解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个去除历史背景的被简单化了的马歇尔主义盛行于大学的日常教学工作中,这一直持续到当时一些激进的学者对此感到厌烦为止。于是,很自然的:当人们背弃传统化了的马歇尔时,他们会认为是背弃了真正的马歇尔;当人们破除障碍走向经济现实时,他们又会忽视一个事实——在他们这一过程的实现途中,马歇尔主义曾起到路标的作用。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核心在于静态经济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只是当时已经成长或正在经历成长的一个派系中的一员,而且这一派系的其他成员毫无疑问的都是独立于马歇尔学说而自成体系的。而他的工作习惯和发表成果的方式,又使经济思想史家对他的意见不可能给予公正的肯定。希望读者不要对此产生误解。作为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先生在为老师写的传记中,为其主观创造力提供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证言。关于这一问题,马歇尔本人保持了庄严的沉默,而他的感情只表现为:对古典学派,尤其是李嘉图和穆勒采取谨慎而公平的态度;对门格尔、杰文斯及最伟大的理论家瓦尔拉等采取中立的态度。接下来的描述不会与真实情况有多少出入。
从凯恩斯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不是求知的好奇心把马歇尔引向经济学家的阵营,而是一种更强大、更仁慈的动机把他从对伦理道德的思索中引向了这个阵营。这一动机也是他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即减轻他所目睹的英国贫困阶层的苦难。当谈到他要献身于这一领域时,他经常遭到沉浸于当时英国经济思想研究的一位朋友的坚决反对,这是他为什么转向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寻求启发的原因。在马歇尔的作品中,也有其他迹象表明他最初投身经济学是从阅读穆勒的作品开始的。1867年,他又吸收了李嘉图的观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因为当时的情形是一个完全受数学教育的大脑求助于两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创造者:首先,他震惊于两个创造者——尤其是穆勒——对于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和明确的结果显出漫不经心、迷惑不解的样子;其次,他会立即开始动手破除各种限制条件,并归纳总结出核心观点。要把穆勒的结构转化为马歇尔的结构,除了上述两点以外,实际上也不需要更多其他的东西了。
当然,这是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成就。许多理论物理学家能够永垂不朽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的不多的成就。马歇尔本人承认库尔诺和屠能对他的帮助,当然,这两位的深刻影响也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其用于局部均衡或部分均衡分析的供求曲线是库尔诺的曲线(当然也不能忘记弗莱明·詹金),而这个数学天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的边际分析法是屠能的分析法。至于边际效用,杰文斯著有《政治经济学的通用数学理论》,这是1862年他在剑桥召开的英国学会会议上宣读的文章,这篇文章涵盖了“效用系数”这一概念。瓦尔拉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两部分分别发表于1874年和1877年,其中包括的静态模型的理论框架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还要完整。但是考虑到马歇尔的阅读习惯,当时这位经济学家可能不知道这些著作的上述内容。至于其他在技术上占先的一切著者,他们对于马歇尔的贡献或许也只能是零碎的。
这似乎解释了马歇尔想要将所有经济理论改革者要阐明的观点都归于穆勒和李嘉图的倾向。虽然瓦尔拉的热烈推崇者可能有理由因为《经济学原理》中很少提到瓦尔拉而感到不高兴,而马歇尔的热烈推崇者则可能因为马歇尔没有表现得更为宽宏大量而感到遗憾,但对于马歇尔在别人对自己的帮助的认可程度这一点上,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然而,在他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对曾给予他大力帮助、始终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数学表达感激时,反对意见就会出现。
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则不容忽视的是,他的特殊的数学才能对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成就是有益的,正是由于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才产生了这一成就;如果没有其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很难完成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研究方法的转变。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任何一个结果,甚至是对一个经济因素相互依存的体系的总的看法都可以通过非数学的方法来获得,正像我们步行也能走到火车能带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一样。但是即使我们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不以数学为核心是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的,尽管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中不需要出现正式的数学的形式,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另一个事实,即马歇尔式的分析正是以数学手段为先决条件的。马歇尔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对于他这位忠实的友军从来没有给予过充分的肯定,他隐藏了帮助他完成伟大使命的工具。
当然,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愿意把外行人吓跑了,他有着奇怪的野心——“让商人读懂”。他担心会树立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榜样,即让接受数学思想教育的人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仅仅是数学这种工具。这种顾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也有人可能希望,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作品的激励正开始信奉和拥护严谨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们,他能够给予更多的鼓励。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被数学左右”这种危险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只不过在其他领域尚无证据表明其危险性有这么大。任何一种科学,如果没有信奉者,就没有所谓进步。且不说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学科,仅经济学一门学科就永远无法让外行明白。实际上,如果读者完全没有数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是无法完全理解马歇尔本人的著作的,那么企图使他们按照马歇尔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马歇尔能够坚决地支持这一前进的路线——在开辟这一前进路线方面,马歇尔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可能会收到更多的好处。
三
任何一个流派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们无法精确地将马歇尔的学说归入哪个学派中。
第一,理论家们会惊异地发现结构的简洁性是它的一大特点。如果我们把马歇尔的表现方法和瓦尔拉的表现方法进行比较,会发现简洁这个与成功直接相关的特点得以凸显。后者的文章显得冗长乏味,而前者则文笔流畅,语言凝练,其优美的外表很好地掩盖了所有刻意雕琢的迹象。其原理论述精辟,论证简洁——至少是在梗概、附录中。马歇尔的数学修养甚至训练了他的文字叙述,使之更为简练条理,同时也使他的图解简单得令人喜欢。
几何图示的方法以前也有人曾使用于经济理论的论证,库尔诺就是其中之一。但现在,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使用比较容易的平面几何图解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过分地简化。但它们仍然不失为珍贵的处理问题(虽然限于那些基础的问题)的方法,它们成功地澄清了许多论点,为不可数计的课堂带来了方便。实际上,我们应该把那些最有用的图示都归功于马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