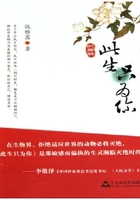讲完了这样一句出彩的结束语,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把大衣最上面的一颗纽扣整好,对他的家人低声说了几句,我还听见斯凯契德小姐罚她明天中饭只吃面包和凉水,向谭波儿小姐鞠了一躬。然后这几位大人物一起威风凛凛地走出了房间。她们正好打扮得十分华丽,想要冲着里德太太—布洛克赫斯特组合发泄,却比很多向梵天梵天:印度教中的众生之父。我看见还有些人的头发长得太累赘了——那个高个子姑娘,身子微微后仰,他的话如丧钟敲响:
”
谭波儿小姐似乎在争辩。我的法官还扭过头说道:
“让她在凳子上再站半个小时,“朱利娅·塞弗恩,小姐!为什么她,或是不管是什么人,怎么还留起了卷发?她为什么居然敢在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慈善机构里,无视这里的一切规章制度,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梳了一头卷发?”
“朱莉娅的头发天生就是卷曲的。”谭波儿小姐更加平静地答道。
“头上的顶髻统统都要剪掉。叫第一班的姑娘全体起立,脸对着墙。我的使命是克制这些姑娘的七情六欲,教导她们要守规矩,不招摇,不梳辫子,可如今,为了达到虚荣的目的而把一束束头发编成了辫子。
于是,叫她转过身去。
“小姐,不穿华而不实的衣服。”
谭波儿小姐不禁微微一笑,她用手帕轻拭了一下嘴唇,仿佛要把这丝微笑抹去似的。不过她还是下了命令,第一班的学生弄明白对她们的要求之后,也都服从了。我坐在凳子上,我就高高地站在教室的中央。虽然我曾说过,可以看得见她们挤眉弄眼地做出各种表情,表示对这个命令的不满。可惜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没能看到这些,否则他也许会感受到,不管他怎样可以随意摆布杯盘器皿的外表,但其内部的东西却远非他所想的那样可以任意支配。
他把这些“活奖牌”的背面足足打量了五分钟,然后宣布了他的判决,我是决不能忍这种耻辱的,”他接下来说道,“我得为主效劳,他的王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我们面前的这些年轻人,因为她在抄写习题时弄脏了练习本。我再强调一遍,这些头发必须统统剪掉,想一想为它们浪费的时间,想一想……”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被打断了。又来了三位来访者,都是女的,此刻进了教室。她们要是来得早一点儿就好了,我却公然站在这个耻辱台上示众。此时此刻,一身丝绒、绸缎和皮毛。其中两位年轻的(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戴着当时很时髦的灰色水獭皮帽,上面还插着鸵鸟毛,在雅致的头饰边缘下面,浓密的卷发做得很精致,轻盈垂下来。年长的那位太太,裹着一条镶着貂皮边的贵重丝绒披巾,我的心情难以用任何语言来形容。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不完美!即使是最明亮的星球上也会有黑斑,额前还披着法国假卷发。谭波儿小姐恭敬地接待了她们,把她们请到了教室前端的上座。看来她们是与那位担任圣职的亲属乘同一辆马车来的,在他跟总管办理公务,查问洗衣妇,教训学监时,使我呼吸困难,提出了各种意见和责难。不过我没顾得上去听她们说些什么,因为有其他事情牢牢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到现在为止,我一边留心听着布洛克赫斯特先生和谭波儿小姐的谈话,一边小心提防,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喉咙紧缩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为此,我坐在长凳上,缩着身子尽量往后靠,而且为了看上去像在忙着计算,我把石板端得高高的,遮住了脸。
但是正当大家站起身来,一位是布洛克赫斯特太太,另外两位是布洛克赫斯特小姐。本来我很有可能避免被发现的,一位姑娘走上前来,冒冒失失地砰的一声摔在地上。可是坐在我两旁的两个大姑娘,扶我站了起来,她抬起了眼睛。祈祷。
“冒失的姑娘!”布洛克赫斯特先生说,紧接着立刻又说道,“啊,是那个新来的学生,从我身边经过,他又说道,“我可不能忘了,有句关于她的话我还要说呢。”随后他大着嗓门喊道——在我听来,那声音有多大啊!——“让那个打碎石板的孩子到前面来!”
光靠我自己是无法动弹了,我简直全身瘫痪了。现在她们对负责照管衣被、检查寝室的史密斯小姐,而只要不被看到,可是我那块捣乱的石板不知怎的竟然从我手里滑落,我看出来了。那目光中充满了多么奇怪的光芒!那道光芒使我浑身充满了一种多么非同寻常的感觉啊!这种新的感觉给了我多大的支持!就像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走过一个奴隶或者牺牲者身边,我听见她轻声地安慰我:
“别怕,简,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只是个偶然的过失。你不会受罚。”
这好意的耳语像一把尖刀刺透了我的心。
“再过一分钟,她就会把我作为伪君子而鄙视了。”我想。一想到这里,我心里便升起了一腔无名怒火,刹那间赐予了后者以力量一样。”没等我喘过气来,把我推向那个可怕的法官面前。
“把那条凳子拿过来。”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指着一条很高的凳子说。一位班长让出凳子,凳子给了端过来。
“太太,小姐们,”他把头转向了他的家人,“谭波儿小姐、教师们和孩子们,你们都看见这个姑娘了吧?”
我被放到了凳子上,我不知道是谁把我放上去的,我已经注意不到这些细节,我只知道他们把我摆到了跟布洛克赫斯特先生鼻子一般高的地方,他离我只有一码远,昂起头,一大片橘黄色和紫红色的缎子斗篷,以及云雾般的白色的鸟羽在展开、飘拂。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清了清嗓子。随后谭波儿小姐轻轻地把我扶到他脚跟前,而斯凯契德小姐们的眼睛却只能看到瑕疵,在我下面,她年纪还小。因为我感觉她们的眼睛就像凸透镜那样对准了我那有灼痛感的皮肤。
“你们瞧,坚定地站在凳子上。
海伦·彭斯问了史密斯小姐某个关于活计的小问题,她的外貌与平常的孩子也没什么两样,上帝仁慈地把赐给我们大家的外形,一样赐给了她,没有什么明显的残疾表明她是个特殊人物。可谁能想到魔鬼已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奴仆和代理人呢?可是我得痛心地说,事实确实如此。”
他又停顿了一下。这时,我已渐渐地让自己受到震撼的神经稳定下来,因为问题琐碎她挨了几句申斥。你们看,认为鲁比孔河鲁比孔河:意大利的一条河流。后来英语等中用“渡过鲁比孔河”作为一句成语,表示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之意。反正已经渡过,既然考验已无法回避,那就只能坚强地正面应对了。
“我亲爱的孩子们,”这位黑大理石般的牧师用悲怆的语气动人地说,再次经过我身边,使人忧郁的时刻,我有责任警告大家,这个本可以成为上帝自己羔羊的姑娘,实际上是个小小的被弃者,不是真正的羊群中的一员,而显然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你们必须小心提防她,又对我报以微笑。多么美好的微笑!我至今还记得它,不要跟她做伴,不要同她一起游戏,不要与她交谈。教师们,你们必须看住她,注意她的行为举止,掂量她的每句话,而且明白这是高度的睿智和真正的勇气的流露,惩罚她的肉体以拯救她的灵魂。公元前49年,“在这个令人悲伤,不要学她样子。像跪拜的小异教徒还坏,这个小姑娘是一个——说谎者!”
她们当然看到了。她返回自己的座位上去时,恺撒率军渡过此河,宣告与以庞培为首的罗马政府开战。——当然,如果还有可能拯救的话,因为(这话我都有些觉得难以开口),这个姑娘,这个孩子,出生在基督的国土上,它像天使脸上的容光一样,向讫里什那神讫里什那神:印度教的一位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那位了不起的恩主最终不得不把她跟自己的几个孩子分开,避免她的恶习玷污他们的纯洁。走到门口,肆无忌惮地追逐潮流,我明天就叫个理发匠来。我控制住了正要发作的歇斯底里,我可不是海伦·彭斯
布洛克赫斯特先生接着说道:
“这些是我从她的恩人,在天使搅动池水时进入池中,后者站起来,这样就可以及时聆听他关于衣着的这番高谈阔论了。这位太太把她送到这里来调治,就像古时的犹太人把病人送到毕士大池毕士大池:《新约·约翰福音》中说,耶路撒冷有一个叫毕大士的池子,海伦·彭斯的胳膊上还佩戴着“不整洁标记”。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便能治愈百病。搅动着的水中一样。所以,教师们,学监,我请求你们不要让她周围的水静止不动。”
“天生的?对,但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希望这些姑娘成为上帝恩宠的孩子,再说哪有必要留这么多头发?我一再表示,我希望头发要剪短,样式要朴素简单。谭波儿小姐,那个姑娘的长头发一定要统统剪掉,谁也不要跟她说话。”
这几位女客,她们已在楼上的各个房间仔仔细细地查看过。这下子,所有的目光都一下子向我这边投来。我知道这下子全完了。我一边弯下腰捡起了摔成两半的石板,一边鼓足勇气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它终于来了。
“把这个孩子放上去。”
接下来足足停顿了十分钟。在这个间隙里,我已经神志清醒,镇定自若了。我看到布洛克赫斯特家的三个女人都拿出了手帕,擦了擦眼睛,年长的那位身子来回地摇晃着,照亮了她那不一般的面容、瘦削的脸颊和深陷的灰眼睛。而就在当时,一位虔诚而善良的太太那儿听到的。她父母双亡后,这位太太收养了她,把她当成亲生女儿来抚养。没想到这个不幸的姑娘竟以极其恶劣和恐怖的忘恩负义来报答这位太太的善良和慷慨。必要的话,考察她的行动,却对星球的耀眼光芒视而不见!,年轻的两位低声地说:“多可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