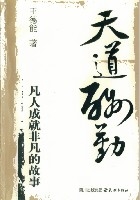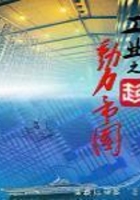七言诗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班固、张衡等人的辞赋中已经开始出现七言的诗歌,曹丕的《燕歌行》就代表了汉魏七言诗的特征。十六国民歌中的《陇上为陈安歌》、《巨鹿公主歌》、《姑臧谣》等,就采用整齐的七言形式。但当时的七言诗歌还被看做民间俚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如傅玄就说其“体小而俗”,汤惠休作七言,颜延之讥之为“委巷中歌谣”。与谢灵运同时的鲍照,借用七言乐府来抒写自己的怀才不遇,风格慷慨悲凉。鲍照打破了原来七言诗句句押韵、节奏单一的缺点,在句式上以七言为主杂以各种句式,在格律上注重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融合着自己的牢骚和愤懑,形成了气势磅礴、奔放流荡的歌行风格,从而完成了乐府诗向歌行体的转化。
梁陈宫体诗的七言体逐渐增多,有的已经非常类似后来的七律,如萧纲的《夜望草飞雁》: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陈后主的《闺怨篇》、萧子显和萧绎等人的《春别》、张正见的《赋得佳期竟不归》、徐陵的《杂曲》、江总的《宛转歌》、《梅花落》等,它们都是情景交融、和谐婉转,已经初具唐诗风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江淹、吴均、何逊与阴铿等几位诗人,他们从不同侧面为近体诗的成熟作了必要的准备。
江淹(444—505)是齐梁时期最善于模拟的诗人,早年才华横溢,诗极精工;晚年官至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诗思减退,被人传为“江郎才尽”。“江郎才尽”的原因,一在于官高而诗作少;二在于其长于古体而短于近体,因而入梁后,诗作难以得到好评,背上了“才尽”的包袱。不过江淹的诗歌对仗精切,诗风清新,尤其是揣摩古人心境惟妙惟肖,开辟了拟古的诗体。
吴均(469—520)出身寒贱,却有才学诗思,诗风清拔,被称为“吴均体”。他的《赠王桂阳》以松自比,刚健清新。《山中杂诗》写道: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烟云、落日、飞鸟、悠云,动态可掬,流露出诗人清幽雅致的情趣。
此外,何逊、阴铿也对唐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在内容上善写行旅、山川,特别重视诗歌的构思和音韵的搭配。如何逊的《咏早梅》、阴铿的《晚出新亭》,构思新奇,色彩和谐,意境辽阔,音韵优美,已有唐人的气魄和风度。杜甫不仅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还说李白的诗歌“往往似阴铿”,可见二人对唐诗影响之大。
四、隋代:在兼容并蓄中自立
秦汉之前,南北文风不同,分别形成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两汉时期,文士有意识地把这两种不同的文风融合在一起,吸收了《诗经》、楚辞以及诸子散文的长处,形成了汉赋。但经过建安三国时期的割据分裂,南北文化有所差异,文学也因此有所不同。随着西晋的统一,南北文风又有所融合。
这种融合是以吴人入洛为契机的。代表人物是陆机、陆云兄弟,此外还有顾荣、纪瞻、戴渊、戴邈、夏靖等,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他们刚入洛时,是为北方士人如潘岳等所看不起的,《世说新语》、《晋书》都记载了北人轻视他们的事。唯独张华、潘尼、冯文罴等少数人欣赏他们。这拨吴人进入洛阳后,把南方的习气带进北方,一方面他们吸收了北方文学的特征,改变了创作风格;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创作和名气对太康文学产生了影响。例如陆机到洛阳之前作的诗都是四言的。从三国时期的文学来看,汉魏时期的五言诗主要在中原一带流行,南方还是四言和骚体。陆机到北方后就开始大量作五言诗,而且他在南方作诗,典故多出自楚辞,到北方后,典故多出自《诗经》。张华、潘岳是北方人,诗作清丽,除了学习曹植、阮籍之外,与南方文风的清绮浸润也不无关系。我们知道《诗经》、楚辞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质朴,后者华美;前者缘事,后者缘情。西晋文学用很美的语言言情,正是南北文风初步交融的一个特征。
这种交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断加强的,到了隋朝才初步完成。南北文学的融合,一要靠文人的交流,南人北上,北人南下;二要靠作品的传播,南北文学互通,在传播中趋同;三要靠文学内部要素的互补,北方的边塞题材到了南方,便有了清丽的边塞诗,南方的宫体诗风到了北朝,便有了质实一些的言情诗。西晋时期的吴人入洛,给魏晋文学注入了一些活力。尤其是北方文人的轻视,刺激了南方文人在学术、辞采以及诗作上的努力,陆机模拟大量的汉魏古诗以及创作辞赋,背后难免有比试的意味。到了东晋,那些看不起南人的北人不得不南下,又给南方文风注入了新的活力,继续推动南北文风的融合。
南北文学的不同,突出体现在南北朝民歌的差异上。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现存南朝民歌大约五百首,保存在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中,其中吴(声)歌326首,西曲(歌)142首,神弦曲十八首,另外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作品。南朝民歌产生于富庶的荆、扬二州,在这些繁华的城市里,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歌谣。由于南朝君臣多好声色女乐,流行于民间的风情小调,常常被他们采集起来,按照自己的趣味加以润色,这些小调不仅在宫廷里演唱,还被赐给功臣。南朝民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起来的。
吴歌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为中心的地区,多在晋宋之间形成。其特点是艳丽柔媚,多表现男女之间缠绵而细腻的情感和交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子夜歌》四十二首,多写相思之情以及哀怨之感,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这些作品语言流丽自然,具有鲜明的情歌特征。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多产生于齐梁之间。这些民歌多写行人思归、思妇怀人,风格直率。如《拔蒲》:“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盈把。”该体清新中多了一丝刚健的气息。《神弦曲》是建业附近民间娱神的祭歌,它和楚辞的《九歌》性质类似,多写人神恋爱。或赞叹男神的美貌,如《白石郎曲》;或写女神的生活,如《青溪小姑》,很有情歌的缠绵多姿。
北朝民歌多载于《乐府诗集》的“鼓角横吹曲”、“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横吹曲》是一种军乐,有鼓有角,故得此名。北朝民歌内容丰富,既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企喻歌》、《慕容垂歌》;也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如《健儿须快马》、《新买五尺刀》;还有反映爱情生活的,如《捉搦歌》等;还有描写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如《敕勒歌》等。其中《木兰诗》写女英雄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它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我国乐府诗的“双璧”。
总体来看,南朝民歌多为情歌,常以女子口吻出之,风格哀怨缠绵。它的形式短小,多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常常用双关语来表达委婉的情感。而北朝民歌内容广泛,形式自由,语言质朴无华,表达爽直,风格豪放刚健。
南北对峙所带来的文风不同,只是问题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南北文风总是在不断交流的。一是书籍的流通。如北魏孝文帝时,曾向南方借书。《隋书·经籍志》记载,“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而在北周宇文泰攻伐江陵时,曾将一批图书随江陵战俘一起押运至长安。二是使者的互通。除了政治、军事使命外,这些使者还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南史·王融传》载永明九年(491),北魏房景高出使南齐,问主客王融说:“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出示之。北方作家温子昇的作品曾由南方使者张皋抄回南方。他的作品受到梁武帝的称赞,云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邢邵的名声传到南方后,被称为“北间第一才子”。三是士人的迁徙。南北攻伐带来无休止的动乱,许多文人改投对方。侯景之乱,颜之推、萧祗等人就奔入东魏。后来江陵陷落,王褒、殷不害等被掳入西魏,这都促进了文风的交流。
南风北浸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庾信,他也是初步完成南北文学交融的大作家。
庾信(513—581)的生平,大致以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出使西魏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庾信聪敏、博学,十五岁就成了昭明太子萧统的伴读。萧统死后,又作了新太子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多奉和应景,写风花雪月,美人宴席,诗风绮丽轻冶。萧纲很赏识他,常委以重任。大同十一年(545),他曾奉命出使东魏,与东魏的文人讨论古辞赋,使他名闻北方。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叛乱的侯景攻到建康城,萧纲派庾信守卫,庾信弃军逃入城中,他的儿子和女儿死于乱军之中。他后来逃奔江陵,辅佐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54)四月,萧绎便派他出使西魏。他到长安不久,西魏派兵攻陷江陵,杀死了萧绎。他从此滞留于北方,先仕西魏,后仕北周,虽然两朝都给了他较高的待遇,以至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但总也不能消除他对故乡的思念,也不能减弱他内心的羞愧,这种情感使他晚年的诗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又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总结了他晚年诗歌的特色。他晚年之作多表现乡关之思,常常把南朝讲究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和北方萧疏开阔的景色、质实刚劲的语言结合起来,形成苍凉悲壮的风格。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及其他的五言小诗,常常能把强烈的思乡之情和苍凉的境界结合起来,形成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如《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诗歌意境浑厚苍茫,风格含蓄蕴藉,充分展现了五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另外,他早期的七言诗中如《乌夜啼》、《秋夜望单飞雁》、《代人伤往二首》等,在声韵、对偶等方面完全可以看做唐代七律、七绝的先驱。所以,我们认为庾信把南朝细腻的艺术技巧和北朝刚健的艺术风格结合了起来,是集南北诗风大成的诗人。
隋统一全国后,就把南北方的许多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曾经仕魏的文人入了隋朝,如李询、阳休之等;仕梁的有颜之推、庾季方等;从陈来的诗人有虞世基、虞世南、陈后主、许善心、王胄等;仕北齐的有卢思道、李德林、薛道衡等;而从北周过来的有杨素、魏澹、辛德源等。隋把全国的文人都笼络到一起了,这就再次促使南北文风得到融合。
隋代诗人常常把咏物诗写得非常清新,如魏澹、辛德源的《咏石榴诗》、《咏芙蓉诗》、《咏橘树》等诗,形象生动。南方的文人像虞世南等入隋后也写了很多诗歌,如写游赏、写歌伎。由于他们与北朝人相互学习,促使其风气也改变了。他们不再把诗写得那么浮艳了,而是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其中。这或许是南朝灭亡增加了他们的沧桑感,诗歌在清丽中隐约增加了一些苍凉气息。
隋代有三个诗人最著名,一是卢思道(535—586),他的歌行写得很悲凉,有惆怅的感觉。他的代表作有《美女篇》,这篇作品是学曹植的,它启发了上官体的婉媚;而《听鸣蝉篇》,则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非常类似,后者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他的《从军行》,写得很悲壮,开唐人边塞诗浑茫诗风。该诗前半写将士们英勇出征,久戍不归,思念家人;后半写思妇遥念亲人,情思缅邈。这首诗在北朝从军出塞的题材中,加入了男女的情爱,不仅具有北朝诗歌刚健雄劲的气质,也带有南朝诗歌清丽流畅的风格。
二是薛道衡(540—609)。与卢思道的悲凉惆怅相比,他的诗写得绮丽。其代表作是《昔昔盐》,同时也是隋代文学的代表作,它是典型的宫体诗。唐初的上官体基本上就是沿着薛道衡的路子发展的。
三是杨素(?—606)。北朝诗人原本擅长的边塞诗,吸收了南方山水诗的细腻后,就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刚健气息就被贯穿在诗歌里。像杨素的《出塞》等,总是有一股英雄之气在里头。
于是山水、宫体、边塞,初唐重要的诗歌题材,在隋代都作了必要的铺垫。所以说,隋朝对南北文风的汇总、吸收和熔铸,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