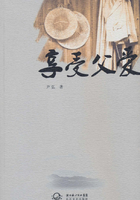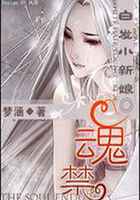第二天,唐子萱病倒了,发着高烧,满嘴说着胡话。程雨农让工地医务室的医生给他挂了吊针,嘱咐他静养几天。
下午,药物在他体内开始发挥作用,热度降下来了,身体舒服多了。他挣扎着要去工地,被程雨农喝止了。
第三天,太阳开始融化地表的积雪。唐子萱的体温还在持续低热,便来到医务室继续治疗。工地医生在他右手腕扎紧止血带,弯腰寻找血管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她踌躇了一会儿,身影遮挡住了室内的光线;旋即她走进屋里。
——茜如!
罗茜如从强烈的阳光下蓦地走进屋,眼前乱溅金星,一时辨不清屋里的人,因而她怯怯地问弯腰的医生:
“请问——”
突然她哽住了。因为她要寻找的人正躺在她面前简陋的病床上接受治疗!
唐子萱在那个熟悉的身影猛地出现在门口的那刻起,心口就狂跳不止。在他潜意识里稳如磐石的思念,一有空隙就从他自我设置的防线钻突出来,增添他的痛苦,诋毁他的意志。——罗茜如最终嫁给了他的同学卢西鸿,成了人家的妻子,这是他最痛苦不堪的。内心受到的煎熬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楚。现在她来了,就站在他面前。
唐子萱猜不透罗茜如怎么到这里来了。即便她回紫溪镇探望她的父母,也没有必要跑二、三十里路到工地上来。况且这里面还有十多里崎岖难走的山路!
他睁大眼睛瞅着风尘仆仆的罗茜如,又把目光移向医生给他扎针的手背,默不吱声。
罗茜如已经适应了棚屋里的光线,认出了唐子萱。她微笑地跨近一步,注视着他:
“你怎么弄成这样子啊!”
唐子萱缓缓抬起眼睛,他一眼看出她瘦多了,依然扎着在乡下的那种泡泡辫儿,脸颊被山里的冷风吹得彤红,嘴里不停地喘着热气。罗茜如穿了一件淡黄花罩衣,蓝长裤,脚上的球鞋沾满了泥巴。女医生这时已经把针头扎进病人手背的静脉里了,疑惑地瞟一眼陌生来客,端起盘子走到一旁去了。
“真想不到你会来这里。”顿了顿,他尴尬地说。
“我只想来当面谢谢你,谢谢你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继而调皮地反问一句。“怎么!不欢迎啊?噢,我不知道你病了,没带东西来看你。”
唐子萱疲惫中有些慌乱,摇摇头:“我只是偶尔感染了一点儿风寒,并没有什么大病。噢!你是随医疗队下乡搞巡回医疗吧?”
罗茜如不自然地笑笑,挪过一只木凳坐下,默看着莫菲氏管晶莹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流进病人的身体,诚恳地说:
“我只想来看看你。真的。”
“谢谢你。”他苦涩地说,“谢谢你还能来看我。”
“我想看一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她轻轻说道。
“你全看到了。”他撇了撇嘴角。“嘲笑我吗?”
“我会吗?”她反问道,热烈地看着他的眼睛。青春重新回到她身上,大量的血液涌流上她的脸颊。
“我的老同学,他还好么?”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故作平淡地问。
“他?!”罗茜如鄙夷地提到她的丈夫,不屑地说:“他如果活得比别人差,那他就不是卢西鸿了。”
“这我知道。”唐子萱吐出一口长气,表示赞同。“能够出人头地,将来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
“我讨厌提到他。”罗茜如蹙紧眉头,厌倦地说。“我们换一个话题吧。虞丹兰,她还好吧?”
“是家里为我订下这门亲的。”他顾左右而言它。“我不想伤父母的心,他们养育我不容易。至于她,”顿了顿,他艰难地说,“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安琪儿,爱我爱的那样深……”
“哦!安琪儿!”她若有所思重复他刚才的话,“安琪儿……”
他不做声,也不敢看她,一动不动半靠在那里。茜如坦露的哀怨让他明显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躁动,内心里对她的突然造访有了某种臆想,嘴里说出来的话却很刻薄:
“你不认为报春花在春天开放太迟了么?当然啦,看了《安娜·卡列尼娜》谁不同情安娜?看了《红与黑》谁不同情德·瑞拉市长夫人!她们都是家庭的叛逆者,追求真正自由的爱情,然而她们最终都被社会扼死……”
她眼里的光泽暗淡下去,他佯装做没看见,继续说:
“其实,我这人不值得别人怜悯。”他瞟一眼棚屋那头假装做事,却竖起耳朵听这边谈话的工地医生。“记得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有一次别人问他,你属于哪一类人?他答复说,如果把人生比做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些人是前来经商,兜售商品的;有些人是前来喝彩,并会晤朋友的;有的人则是前来看热闹的。他自己呢,是属于前来看热闹的一类人。我想,我也算是一个看热闹的吧。因为我在事业上一无所成,总是在社会的边缘晃悠。”
“瞧!你把人生看得这么悲哀。”
“是男人谁不想一显身手?——可是拼搏吧,两袖清风,社会不容。我抽烟最多的一晚上烟头扫了半簸箕,我喝酒,让灵魂淹没在酒精中……转而又想,我有什么理由消沉呢?看看工地上那些下苦力的农民,他们每天只能得到生产队一角钱的劳力补偿,整月整月的吃淡水萝卜煮白菜,干的是又重又累的体力活儿,他们有怨言吗?没有!他们很多人在将来水库修成以后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在他们中间,我有时候真为自己感到羞愧。茜如——”他脱口而出,不由地红了脸,“谢谢你跑几十里山路来看我,我知足了。你回去吧……”
罗茜如盯着他的眼睛,黯然道:“好吧。我知道了。我这就走。”
她从肩上的军用挎包里取出几本书,轻轻撂在唐子萱枕边,低声道:“谢谢你的书。看了那么久,是该归还给它们的主人了。”接着,她轻声补充一句:“其实,在古琴台那次就准备还你的;可惜你没来。”
“《约翰·克利斯朵夫》!”他眼光迅速扫一遍,心底里滚过一丝颤栗。卷首语他记得那么清楚:“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魂灵。”
“各国的……”反复嚼咀着它的全部涵义,他对自己的受苦,奋斗毫不怀疑,但他的灵魂最终能从传统的樊笼挣脱获得自由吗?
罗茜如慢慢走向门口。唐子萱下意识地把手伸进棉袄的胸襟里,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月前他返回管理区办事时,竟鬼使神差地把那串橡子项链揣进了怀里,而且一直带在身边——现在,他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了包裹小木盒的红布,但他没有勇气拿出来。他一直想把它做为礼物送给茜如,又怕太过于寒酸,所以,眼睁睁地看着罗茜如满怀惆怅走向门口而无话可说,倒是心底翻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壮。是的!他已经听出了她的不幸,那又能怎样?——而他,曾经是那样地崇拜她、暗恋她、追求她,把她当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换了以前,他或许会拜倒在她面前喊一声:“高贵、纯洁、美丽的茜如,把爱赐给我吧!”现在,他深感悲凉,悲的是一切都成为事实,一切都成为过去,只剩下悔恨交集。他目送她黯然神伤地离去,在心里不断地呼唤:“你好,祝你如意!你仍回你的闹市,我居我的深山,属于我的什么也没有……”
他紧咬牙齿,胸膛剧烈地起伏,掏橡链的手沉重地垂落在床沿,任凭一腔爱与恨、落寞与惆怅折磨他。
程雨农恰好这时从棚外进屋,跟罗茜如擦肩而过。他扭过头好奇地瞄一眼来访的陌生女人,她已经快步走掉了。
“我路过这里,顺便拐了个弯儿来看你。”他从唐子萱颓唐的神色中觉察出异样,再次扭过头朝罗茜如消失的方向张望了望,然后十分严肃地说:“年轻人哪!不是我批评你。贫下中农的后代,端上革命干部的‘铁饭碗’不容易。在个人问题上可要三思而行,莫栽跟头喔!”
扫一眼刚才罗茜如留在床边的几本书,他改变了几分钟以前要安慰安慰他部下的打算,语重心长地说:
“乌七八糟的书要少看!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的好书也不少,《红岩》、《艳阳天》都是,我以前说过的一些话,并不是要你们年轻人把什么鬼东西都拿来读,结果是越读越糟糕,越读思想越花哨。同志喂!思想问题,栽在那上头可是要哭都不得瘪嘴哟!”
他狠狠地盯一眼神色萎靡的唐子萱,转身“嗵嗵嗵”走掉了。
程雨农走后,唐子萱闷闷不乐地呆靠在床头,直到工地医生走过来帮他换掉一瓶液体。他完全明白程雨农的意思。他把他跟罗茜如之间纯洁的友谊误当做花里唿哨的小资情调,罗曼·罗兰的不朽巨着成了“鬼东西”,这令他难堪之余十分愤怒。程雨农对他发出的警告无疑是开始不信任他的信号,对这一点他深为忧虑,两年来辛辛苦苦付出的劳动、心血,就这么被人家一句话轻轻松松给否定掉了。直到这时他才遽然醒悟,人家讨厌他在工地看书,尤其是外国人写的书!在那些思想正派的干部眼里,外国人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着作,其它的统统值得怀疑。工地上到工程指挥长,下到突击队员,人人都希望听到看到“某某民工今天比别人多挖了几个土石方”、"某某突击队超前一天完成任务”之类的表扬,并不需要太多太深奥的东西。瞧!工地那么多初小文化的通讯员写来的稿件不也照样起了大作用么?!所以,现在他不恨别人了,转而恼恨自己的行为招惹来这么多的麻烦!那天夜里,干嘛要拼命喝酒?——其实他也清楚自己喝的并不多,怎么偏偏就醉了呢?他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那些躲藏在心灵深处驱化不开的情愫在他有限的生命中到底能维系多久?他怔怔地望着头顶单调的苫草,嘴里“嘘嘘”吹起了口哨!——这是他在工地发明的借以发泄内心郁结的好主意;在旁人看来,他倒是十分逍遥自在呢!
唐子萱的重感冒一个星期以后才痊愈。后来的几天里,他都是忙里偷闲地到医务室拿一些药丸,多半时间跟民工一起泡在工地。虞丹兰获知他病倒的消息后匆匆请了假,赶到工地,顺便捎带了一些攒了很久的鸡蛋和托人在县城买到的牛奶粉给未婚夫补身子。
她火急火燎赶到工地时,唐子萱正在指挥部里忙着修改广播稿。看着虞丹兰一副着急的样子,当着唐子萱的面儿,程雨农狡狯地逗她:
“虞会计,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虞丹兰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转口说:
“子萱这回还真亏了您哪!不是您把他从雪地里搀回来,恐怕早冻僵了哦。真的,多谢您程书记。”她瞟一眼无动于衷的未婚夫,微嗔道:
“他呀,也真是的。总是喝得醉熏熏的。”
唐子萱反感地白了她一眼,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冲击之后,他越加郁郁寡欢了。这段时间,他以到各施工点搜集素材为名,推辞掉了许多跟随程雨农四处转悠的机会。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跟他的顶头上司保持一定的距离。
程雨农并不戳穿那天唐子萱在雪地里胡言乱语的可笑表现,接过虞丹兰的话头,诡秘的一笑。
“好哇!男人就是要学会喝酒,喝酒才能图个身心舒坦。”
虞丹兰脸上浮现一层笑容。
“那是您程书记教导有方啊!”她恭维说。心里却冷冷地说:“鬼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瞧他那一副故意喝得醉熏熏的德性,肯定是心里不舒坦,讨嫌这门婚事。反正,他心里还是丢舍不掉那个抛弃了他的贱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