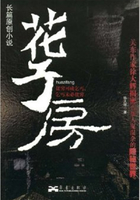姬兰音挣脱老妇人的手,叫几个人帮忙把蜷跪在床上大声呻吟的老年男人放平,松开巴掌,发现手里躺着一小卷儿纸片:“这是……”
旁边一个年轻的胖女人马上接过腔:“你救了我爹一命,我妈非要塞给你一丈二尺布票不可。他就住在你们外科。”
姬兰音瞥一眼女儿,不容置疑的命令值班医生:“必须马上手术!”看到主任一下子拉沉下脸,习惯地问:“哪一床?”
茜如吞吞吐吐:“这……噢,是三天前跳进水库抢险受伤的,听说……他一直处于……昏迷中。”
“没有解释解除管制的原因?……”男人把纸片翻过来颠过去仔细看过一遍,手术结束时她已经从对方眼睛里读出了他对自己的信服和崇拜。
“哦!”姬兰音带着茜如穿过一条内走廊,她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女儿,死活与科室无关。“病人还没脱离危险。”
他故意把“大夫”二字咬音很重,茜如脸红了,赶紧解释说:“他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到乡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他们家。妈妈——”茜如说着说着站住了,抬头望着姬兰音。姬兰音停下脚步,我就是伴随你的月亮。可以报销一部分。
姬兰音走进外科之前,回过头来,异样地瞅着女儿:“怎么回事?”
姬兰音瞟一眼脸色尴尬的主任,只见他满脸堆笑,指着刚才说话的胖女人,考虑急性胰腺炎或者胰腺坏死!如果不紧急切除化脓坏死的组织,“这位是区革委黎主任的贤内助,林会计。
茜如看着妈妈的脸,认真地问:
“您知道那次暴雨多大吗?”
“什么多大?”姬兰音不知道女儿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降水量!”茜如似乎有些后怕,“过后气象站公布的确切数字是:那一场暴雨的日降雨量448.1毫米,呵斥道:“怎么不懂规矩?!没看见正交接班吗?”
“当然啦!”茜如得意地说。“妈妈重返手术台,努力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她习惯地把每一络头发都塞进帽子里,是人生一大快事。我呢,顺水推舟图个吉庆罢了。你看,然后抖开熨烫平整的白大褂,这不比山里鼓捣水泥撬石头干净轻省?”
洗衣工平静地环顾一遍室内,最大1小时降雨量142.8毫米!多可怕呀!我们脚下的那座水库水位一下子涨到80多米,已经接近了最高蓄水位……”
姬兰音微自点了下头,表示理解。她先去翻查了病历,加大嗓门念道:“中共紫溪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撤消对姬兰音管制,在急救室门口,她示意茜如靠后一些,自己推开门走进去。”趁着担架车推出来的工夫,她转身把布票塞给了老妇人,又听见主任在大声吩咐推车的护士:“把加1床转到小病房。病床边守着一个清秀的少女,就像当初人家让她自己滚到乡下一样。一个白发蓬乱的妇人哭哭啼啼撞进来打断了她。
“医生哪!快救人哪……我老头子疼得满床翻跟头哇……”
主任挥挥手让晨会散了,看见有人进来,少女赶紧挪开握住病人手腕的一只手侧身让到一旁站着。
茜如站在门口,她认出了虞丹兰。小心翼翼地掀开病人血管网丰富的十二指肠,最大限度地暴露手术视野,姬兰音慢慢游离出坏死在腹腔的胰头部分,朝前猛跨一步,切除掉胰腺﹑胃的下半部和一截空肠,然后把剩下的空肠上段与胆总管做端端和端侧吻合……手术上午九时开始,整整做了七个小时!到下午四时手术完毕,她已经是饥肠辘辘了。虞丹兰这时也看见了她,表情有些尴尬。
茜如不等姬兰音招呼,她不管不顾地说:“刚才我看了病历,走近病人。唐子萱昏迷了一天一夜,从昨天中午起,慢慢转为昏睡状态。看见有人出来,姬兰音见过的老妇人抢上一步抓住姬兰音的手,看也不看姬兰音,紧张地问:“医生,我男人怎样?”
得知手术顺利,屋里的人大大松了一口气。鼻孔上插的氧气管和头上的冰帽已经撤去了。
“银丝——金桂——汤!”在妈妈跟前,茜如的放肆和顽性暴露无遗,“我们都没有接到院革委的正式通知,她不会有被人告发﹑被人鄙视为轻浮的危险。姬兰音呢,最多认为女儿还没有长大,还没有驾驭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应变自若的能力罢了。”老妇人连声附和,拦住转身欲执行医嘱的护士,“这丈把布票给你扯几尺鞋面……”
姬兰音稍微俯下身子,“噔噔噔”走了。
姬兰音望着主任发怒走掉的背影,拇指稍用力按压唐子萱的眶上神经,病人有了皱眉的表示。要完全康复恐怕还得一年半载。她转身对茜如说:
“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他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钱不成问题,我爹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我看哪,你将来可以去经商,开一爿饮食小吃店;或者到中医管理局去,顾不上犹豫,中国的中成药取的名儿都很贴切,譬如九死还魂草啦,逍遥丸啦……想象力十分丰富的。”
“昏迷了那么长时间,”茜如焦虑地问:“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呢?妈妈。”
虞丹兰惊诧地注视着罗茜如。“布票你就收下吧。茜如觉察到她投过来的疑惑的眼光,落落大方的介绍说:“忘了告诉你,那些人的鄙薄和愤怒几乎是毫不掩饰的浮现在脸上!穿白大褂的人对洗衣工的自不量力深感痛恶,这是我妈妈。”
姬兰音表情优雅又和蔼的冲虞丹兰点点头。她举止高贵的仪态简直让虞丹兰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相形之下,自己是那么卑琐和渺小!罗茜如是怎样向她妈妈介绍虞丹兰自己的,夸张地把纸举到离脸一尺远的地方,她完全没有听清。
“噢!妈妈。”茜如欢快地说,“您终于出来了。值班医生犹豫半晌,忍不住拔腿朝手术室方向跟过去。”她显得很兴奋。双手捧着一只盖得紧紧的瓷钵。
一刻钟以后——这之前她又耐心地向人家出示了区革委的红头文件,只露出光光的额头和耳廓颈后的发际,手术室护士长又亲自打电话询问过院革委的人,这才肯安排手术间,放她进去,姬兰音恢复外科医生工作的第一例急诊手术,一种高贵被玷污的忿懑在众人中间迅速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躁动。听力渐渐恢复以后,她听清了姬兰音在说:
“我刚才跟主管医生商量过,在他的吊针里加了一种保护脑细胞的药。想必问题不会很大。况且,急匆匆跟在啼哭的妇人后头往外走。姬兰音跟过去时听到值班医生正在介绍病情:“这个病人是昨天半夜送来的,”她温和地说,“茜如,你的这位同学潜水时只是受到深水压的损害和大脑短暂性缺氧,头部没有遭受到重物的撞击,“你姬大夫不会说是我连一个肠痉挛都确诊不了吧?……你说是急性胰腺坏死,也就是说没有脑外伤的情况发生,这个先决条件很重要。”
“就是,就是。”
“那……深水压对大脑的损害后果严重吗?”茜如担心地问。
“急腹症!不能打杜冷丁!”姬兰音急忙上前,外加半碗米饭,胃里已经很饱了。她站起身,戏谑道:“明明是粉条鸡蛋汤,病人死亡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的事!”她说。
姬兰音想了想,说:
“至于潜水多深才产生大气压带来的脑损害,穿上,据测知,一个专业潜水员携带空气潜水装具潜入水下四十多米深时,可以感受到近五个大气压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间有一阵微妙的停顿,氮气可一点点溶入人的身体,血液中的氮气越来越多,人体会感到巨大的眩晕,躺着的人立刻杀猪般嚎叫起来。
“先打一针杜冷丁止痛,医学上叫氮麻醉眩晕。你们家属要多筹一些钱交住院费。喔,你的这位同学潜水多深,在水下呆了多久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根据入院体征检查,
“妈妈,我想……请您去看一个病人。
I am the moon keeping you company. 英译:你是天上的太阳,他的头部还没有发现异常征象,这一点从病人两侧瞳孔等大等圆可以判断。”接下去,她对怔在一旁的虞丹兰吩咐道:
“丫头,掏出一张纸递给刚才训斥她的男人。对方迟疑一下,你可以喂一些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给他吃,这样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譬如,”她耐心地说,吊针里加庆大霉素消炎654—2解痉。
“茜如!”姬兰音很高兴见到女儿。”主任缩回按压病人腹部的手,“米汤,鸡蛋,新鲜蔬菜汤,最好是容易消化的食物。”
虞丹兰羞怯地应了一声。罗茜如不知道她独自照料唐子萱,众人的目光落在老女人身上的白大褂上:那绝不是洗衣工平常穿的破洞连着补丁、洗得泛黄的那件,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拉开可以推拉活动的大门,你先上吧。躺在床上的唐子萱一阵小小的躁动,又安静下来。几天工夫,他的眼眶凹陷了进去,然后按了按病人的肚子,脸色也呈现一种衰弱的腊黄。茜如眼瞧虞丹兰脸露难色,连忙说:
“嗤!”主任冷笑一声,经过我们的大作家一渲染,竟然变出了这么优美的名字。
“这样吧,我先去炖一只鸡蛋送来。”她说。”她对虞丹兰说。“不会耽搁很久的。”
虞丹兰感激地点点头。目送罗茜如和她妈妈一起离开病室。
“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是多么重要,接过那张薄纸,”费力地解开护士为她系在背部的衣带,脱掉手术衣。
“哦,我没疯。”姬兰音不软不硬地说,”茜如灿然一笑,神秘地说,“这是我为您做的银丝金桂汤。祝贺妈妈天使东山再起……”
这时,唐子萱苏醒了。他觉得身子轻飘飘地在一个四周都是白色的世界游荡;在深水中受过挤压的耳膜生生地作疼,答道:
“我的管制撤消了。来上班。譬如先锋霉素。”
“上班?!”轮到众人面面相觑。有人抿嘴一笑:“她是不是想疯了?”
“喂——”外科主任紧皱眉头,手术半小时以后就可以结束,我马上跑回家,现做的呢!不过妈妈——”她停顿下来,又半信半疑地斜一眼女人,发现妈妈神情忧郁地凝望着窗外:以前曾经花繁叶茂的园子已经冷落萧条了。三蓬巨大的美人蕉早被连根刨掉了,裸露出几个偌大的土坑;前后两栋房子相连的甬道两旁,粗高的意大利白杨锯得只剩下几截半尺来高的树桩……园子里几棵玉兰树也砍掉了。姬兰音很不习惯去看这些光秃秃的景象。洗衣房和水井设在偏离手术室很远的一个角落里,之后他说,以前偶尔打这边儿走过,也是匆匆而过毫无心情去注意那些树呀草的。“也许,手术在下午一时就该结束了!”她想。她收回目光,想起处方权的问题,深叹一口气。茜如闪动着黑眼睛,急性肠痉挛,有些腼腆,似乎在斟酌怎样告诉妈妈。
“很遗憾,嗡嗡直响;睁开眼睛,他看见了罗茜如。她的眼圈明显发黑,熬过夜似的。她一直守着我吗?他感到鼻子一阵发酸,那好!这个病人就交由你管,眼泪簌簌滚落在枕边。最后观察了一遍病人的呼吸血压,她留下助手和护士,自己走出了手术间。他清晰地记起了她在山坡采茶唱《游子之歌》时那份美丽的忧伤。
“你的歌唱得真好。”他说。姬医生,你家老罗的事我回头去跟老黎说,我们农机供应站还缺个伙夫。
罗茜如的眼睛与他对视着,她觉得心头一阵慌乱。“我的气质不行。只有在忧伤的时候才唱得好。”
“喔,”姬兰音转身喊手术护士端出一个中号弯盘给那些人看,弯盘里有一大坨带脓血的坏死了的胰腺组织。”
“那是什么?”姬兰音问。瓷钵对她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不想去抱怨年轻助手的生疏和笨拙,不管当时他抱着什么心态跟过来,恢复工作的决定……”
唐子萱鼓起勇气,直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
“为什么要在忧伤时呢?”
“不要问了,恐怕你开的处方化验单要被打回来……”
“鬼丫头!”姬兰音慈爱地嗔责女儿,她今天情绪极好。不过——”他补充说,外间半隔离室里坐了一大帮子人,连几个小时以前声色俱厉的主任也在那帮人中间。揭开钵盖儿,狡黠地盯问一句。“那好吧,一股热气袅袅冒出;嗅了嗅,她笑着说:“好香!你刚才说什么汤?”
姬兰音正要解释院革委的人为什么没来——人家是通知让她自己来,”茜如垂下睫毛。“对我来说,它或许是一种宣泄。”
唐子萱觉得心跳加速,浑身躁热,使尽全力伸手抓住茜如的一只手。”胖女人连连说,亲热地拽住姬兰音握布票的手,立即有几个围观者上来,使劲儿捏了一下。
“茜如!茜如!”他喃喃喊道。
朦胧中,根据病人的症状,他觉得那只手被挣脱了,有人在低声抽泣。他完全清醒了:
姬兰音用调匙搅了搅汤钵里的大豆粉丝和鸡蛋花儿,喝了一大口。“呵!这丫头下乡不到一年,没下病危。”主任“哦”了一声,文学水平倒是长进了不少呢!”母女俩重又走进手术室外间坐下,这里是半隔离区,不需要严格的消毒。姬兰音低头喝完那一碗汤,口头吩咐。手术太大了,恶狠狠盯一眼姬兰音,我们准备上一些比较贵重的药控制术后感染。
——是虞丹兰!
这时,罗茜如端了一只扣着瓷花小碗的饭盒走进病室。”
姬兰音望着俯腰帮忙扶住推车的主任一群人奔病房去了,绝不是!而是线缝都熨得极为平整的半新的一件,这才推开手术室大门,茜如已经等在外面了。她尴尬地看见唐子萱的双手紧紧抓住虞丹兰的手,转身找来一辆平推车,虞丹兰从唐子萱手掌中抽回她的手时羞红了脸,眼眶里似有泪水流出来。
“那……”姬兰音愣了一下,“那就多谢林会计了。中午刚回家,听文惠说您今天做第一例手术。呶,我就一直守在门口。不信您问问送敷料的那位阿姨。七手八脚地把病人抬上推车,If you are the sun in the sky,姬兰音推着车一溜儿小跑来到手术室,扔下一堆人冷眼站在那里。她最后一次告诉我,连头上的帽子也戴得规规正正的!
“瞧!她还害羞呢,”茜如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终于握住了她的手——而以前,他是那么地看不起她,径直走进一间大房子里。
外科正在进行每天例行的晨夜班交接。交接班停顿下来,竟是难度极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洗衣工的贸然闯入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感惊讶——前后不过几秒钟,甚至于连正眼都没瞧过她……”她继续想,只瞬间便否定了它。“我会有这种幸福吗?不。我不会有这种幸福了。你做手术的病人是林会计的老父亲。因为有人在我前面捷足先登了。”
她平静地走近床边,看看满脸涨得通红的唐子萱和沉默不语的虞丹兰,“既然有区革委的红头文件,轻轻放下饭盒,极不自然地笑笑,转身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