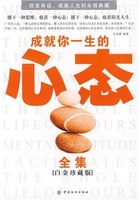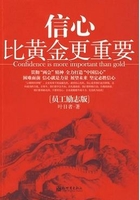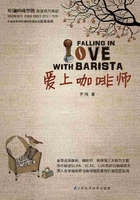霎时,我在黑暗中见到了母亲的脸——她在患病前那张充满慈爱的丰润脸庞,她仍是一头白发,脸上仍旧带着笑容。母亲的影像如此真实鲜明,似乎我伸手便可触及。她的模样一如从前,我甚至闻到她最爱用的香水的味道。她静静地站在我面前,一言不发。我有些纳闷为何我想的是父亲,出现的却是母亲,同时也对许久未想起母亲而感到些许愧疚。我说:“妈,晚年的那场病让您受苦了。”母亲轻轻地将头侧到一边,仿佛表示理解我的心思。她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微笑,然后清楚地说:“不过,爱是我所有的回忆。”说完她便消失无踪了。
房间突然一阵微寒,我不禁打了个冷颤。此时我深深感觉到,最重要的是我们曾对彼此付出关怀,苦痛会消失,惟有真爱永留心间。母亲这句话点醒了我,直到如今,我还忘不了与她相见的那一刻。
虽然我一直没有父亲的讯息,但我深信有一天,他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再说一次:“我今天告诉过你我有多么爱你吗?”
亲情始终温暖,它与生俱来,是人世间最恒久的感情。
奇特的药方
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张药方。让他怎样开药方的,是病人的女儿。
那是一位常见病人,六十多岁,风湿。就在他要开药方时,陪同病人来的女儿让父亲先出去,他的父亲早就盼望着结束检查,只见他边走边拿出打火机将烟点着,看上去瘾大且顽固。
病人出去后,女儿要求他在药方上附加一条:服药期间严禁抽烟。抽烟并不是风湿的病因,怎么可以是药方的内容?他一生严谨行医,怎可贻笑大方。那做女儿的着急起来,她说父亲身体不好,却还是一个劲儿地抽烟,家人怎么劝说也不行。最近一次他偶然听父亲说道:“如果医生说戒烟能治好风湿,我一定不抽了。”“无论与风湿有没有关系,请你一定附上这一条。”女儿求他。
他行医五十多年第一次遇到要求附加药方的,于是破例开了这个不是药方的方子。但是她又说:“能不能再开些可以吃两个月的调理药方,照例在后面附加那一条?”
事后,他想明白了病人的女儿为什么会要求他开那张不是药方的方子——因为药方后面附加着爱。
亲情就体现在生活中点滴的关爱中。
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金牌,为天津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这位十九岁数学奇才成功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下面就是他讲述的自己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袅袅的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
跛着脚的母亲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五个鸡蛋和邻居换来的,她的脚是前天为了给我多筹点儿学费,推着一整车蔬菜往镇里的路上扭伤的。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久久地抚摸着母亲肿得比馒头还高的脚,眼泪一滴滴滚落在地上……
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岱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名叫李艳霞。
我家太穷了。我出生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四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七岁那年,我上学了,学费是妈妈向人借的。我总是把同学扔掉的铅笔头捡回来,用线捆在一根小棍上接着用,或用橡皮把写过字的练习本擦干净,再接着用,妈妈心疼得有时连买铅笔和本子的几分钱也要去向人借。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考第一,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愈学愈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我没上小学就学完了四则运算和小数分数;上小学靠自学弄懂了初中的数理化;上初中也自学完了高中的理科课程。一九九四年五月,天津市举办初中物理竞赛,我是市郊五县学生中唯一考进前三名的农村小孩。那年六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欣喜若狂地跑回家。没想到,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堆满愁云。奶奶去世不到半年,爷爷也生命垂危,家里现在已欠了一万多元的债。
我默默回到房中,流了一整天的泪。
晚上,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头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每天跟妈妈下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
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小毛驴卖了?你疯了,以后整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学期……”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无二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让他念下去。”捧着妈妈卖毛驴得来的六百元,我真想给妈妈下跪、磕头。我太爱念书,然而这一念下去,妈妈又要为我吃多少苦?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似地躺在炕上。妈妈若无其事地告诉我:“没事,重感冒,快好了。”谁知,第二天我拿起药瓶看上面的英文,竟发现这些药是抑制癌细胞的。我把妈妈拉到屋外,哭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妈妈说自从我上一中后,爸便开始便血,一天比一天严重。妈妈借了六千元去天津、北京一遍遍地查,最后确诊为肠息肉,医生要爸爸赶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咱呀?
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没有钱雇人帮忙,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再用平板车拉回家,晚上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穗在大石头上摔打……三亩地的麦子,全靠她一个人,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走路时一瘸一拐的……不等邻居说完,我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妈,妈妈,我不能再读下去了呀……”妈妈最终还是把我赶回了学校。
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六十到八十元,比其他同学的两百至两百四十,实在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妈妈为这一点点钱,从月初就得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出时还得去借个二十、三十。而她和爸爸、弟弟,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儿菜也不用油拌,只舀点儿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去给我批发方便面渣。每个月月底,妈妈总是带着一个鼓鼓的大袋子,千辛万苦地来天津看我。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六里外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给我做计算纸)和一大瓶黄豆辣酱,以及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五元,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青菜也吃不起的学生,只能买两个馒头,回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辣酱和咸菜吃;我也是唯一用不起稿纸的学生,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唯一没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光荣!
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母亲来的时候,我向她说了怕英语跟不上的顾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妈只知道你是最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要让舌头听自已的话,于是我常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拼命背英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英语成绩进入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她的话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个学习障碍。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结果我仅得了二等奖,我一头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者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含辛茹苦的母亲,实在不够啊!回到学校,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的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如果我现在只攻数学,一定能赢。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终于在全国数学竞赛中,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十次测验中夺魁。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费用须自理。交完报名费,我把必备书籍和母亲做的黄豆辣酱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看我依然穿着别人接济的,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打开储藏柜,指着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三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连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你全部的衣服啊?”我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人。母亲总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们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七月二十七日,奥赛正式开始。